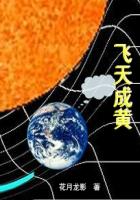前方尽头,仿佛有房屋杂居,村落聚集。吉良庸估计这是小镇,没有城郭隐现,就去那里歇歇脚。
小镇上颇为热闹,吉良庸牵着马,小心翼翼地避让着两侧人来人往,一边观察着两边店铺,终于看到一扇招牌,上面的字对他很有用,“沙河老店,驴肉火烧”,说明这个地方叫沙河。
他看到一间有很宽阔场心的酒家,那里马儿可以被拴在场心上,不用被牵到后面畜栏。
店主应该姓高,招牌上写着高家酒肆,把蕊儿解开放到地上,小娃儿忙不迭地蹦跳了几下,在老爹胸前腿都缩麻了,一父一女手牵手走进店里。小二还在招待别的客桌,他还是老习惯,挑靠窗的位置坐。他选择面对场心,这样他的正脸就不用被其他桌客人打量,蕊儿呢,就对着墙坐,坐他左手边,也是同样道理,一刀一剑,轻轻解下,放在右手条凳上。
随便点了几个菜,另外叫了八个馒头,准备带在路上,时值芒种,天气酷热,含水的食物不易保存,也就馒头可以带个一两日。进来之时已经看过厅内,五六桌客人净是些平常之人,饮酒比较吵闹,两马在场心内树下吃草料,蕊儿双手托腮,呆呆看着父亲。
吉良庸得和小孩说话,这么呆坐着极其反常,他伸手入怀,去摸自己的钱袋,想从里面物件里,找出个什么物件给孩子嘻弄把玩,一不小心,够着了那方包着玉簪的方帕,心中又是一颤。急忙拿出钱袋,从里面找出自己的玉扳指,递给蕊儿,这东西,可以立着,也可以在桌上打转,蕊儿的注意力,就放在这扳指上了。
这一转眼,场心里又有一拨客人,也是骑马而来,等吉良庸去观察他们的时候,有两人正靠近吉良庸的马儿,指指点点呢。吉良庸心内一惊,这些人来路不明,想做什么?
只见这群人在门口你推我辞的客气了一阵,纷纷走了进来,居然也不去楼上雅座,靠着吉良庸这边,也挑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吉良庸扭头与其中几人打了照面,双方都不认识,略微点头示好。
这些人寒暄过后,两人起身去厨房点菜,看起来是这高家店的常客。背对窗靠里坐的那人,正好处在吉良庸看着蕊儿玩的视线里。吉良庸的余光早就看到这人在反复打量自己,奉行言多必失的道理,他默不作声,看着蕊儿将扳指在桌上旋转,像陀螺般炫个不停,蕊儿拍手叫好,这倒好,吸引了那座人的注意了。
还好小二此时正端菜过来,吉良庸连忙摆盘取筷,心下想“不能给这些人搭话的机会。”
可惜麻烦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得掉的。只见这人双手作揖,向吉良庸微笑道
“这位仁兄,场心里那一黄一青两匹马,可是您的坐骑?”
吉良庸放下筷子,抱拳回礼,微笑答来“正是在下的,兄台如何知道?”一边端详此人,这个家伙也是个高个子,身形忻长,头型脸型也是长条一般,眉毛却很稀疏,鼻子高挺,双目略突,说真的,整个长着就是一匹马脸。
“在下姓冯,二马冯,我也是爱马之人,看兄台这两匹马,都是不菲之物,所以多看了几眼”,
马脸汉子说到,好马喜马,又长张马脸,怪不得姓冯;
“冯兄好眼力,果然是好马之人,小弟姓吴”“李代桃僵”吴文静的说词,看来要派用场了。
一边夹菜的蕊儿,抬起头来,纳闷地看了一下吉良庸,吉良庸心里“咯噔”一下,糟了,万一蕊儿喊出自己真名,岂不是要惹事情,只见蕊儿又回头看着那座人,奶声奶气说到
“你们这些大人好烦哪,还让不让人吃饭啦?”
马脸那桌人哄堂大笑,吉良庸心里却暗自惊心,也不知道是蕊儿天性如此,还是临场生变,不像一个六岁小儿的表现啊?
马脸汉子继续聊着“吴兄,我看这青马摔得不轻啊,右边一片毛皮脱落,我看伤口之处虽然已经结痂,但是这炎夏天气,极易长虫生蛆,严重了说不定影响关节,我看着颇为心疼。”
“唉,我也这着急呢,这马的确滑崴了,我正在想吃完饭到哪里找兽医给医治一下。”那就顺着这话题说,
“此去向北约三十里,离丰县不到五里处,就有一家马场,养马之人定会治疗马患,吴兄可去那里看看”
“多谢冯兄指点,小弟感激不尽”,吉良庸连忙站起身,冲小二招招手,“小二,上一坛好酒!”
店小二连忙端着酒坛子过来,吉良庸端起酒杯,走到这桌人前致礼道
“行路之人不便多饮,小弟这里以茶代酒,多谢各位仁兄指点的美意!”
一桌汉子连忙客气寒暄,举杯托碗,答谢吉良庸。
只听又有人无话找话道“这马摔得不轻,但是吴兄看起来倒是毫发无损啊?”
这桌人不简单啊,吉良庸微微一笑,放下酒杯,伸开掌心给众人看了看,一片唏嘘之声,这伤还真的假不了。
“吴兄所带这孩子倒也没伤着啊”说话的还是那马脸二马,这话锋绝对一流,
吉良庸笑了笑,从他们桌走到自己桌前,指了指自己条凳上那一刀一剑,“在下一无用处,只好凭这些家伙吃饭”,摸了摸蕊儿的头,“还好有心,把这孩子绑在胸前呢。”
“哦!”邻桌一片赞叹之声,显然把吉良庸当做了一个武林高手。
“吴兄身怀绝技啊,这脚下骏马胸前负婴,可只有五虎上将赵子龙才做得到啊。”不明真相之人一片夸赞之声。
吃完饭,吉良庸做出一副萍水相逢相见恨晚的神情,和邻座打了招呼,先离席而去。这姓冯的,对他很好奇,他用后脑勺都看得到这家伙对自己的一片胡思乱想。不过,不妨将错就错,虽然与他们熙熙攘攘纠缠了些时间,但是也套出不少消息,尤其是方位。徐州其实在大夏的划分辖境并不大,古徐州包含了现在青州和淮州、扬州的各一部,现在这徐州,只辖十余县而已,徐州城位于各县居中,走过丰县,就能穿过徐州州治,再跨过青州一片,就是冀州境。
解下马缰,吉良庸决定先去这二马指向的马场,这是匹好马,他很喜欢,另外,这马跟他要找的线索肯定有关,他得留着。这二马若对他有想法,也会尾随而来,他不妨将计就计,故作愚蠢。
上了路,看看依旧绑在怀中的蕊儿,突然想起中午那人说的赵子龙的故事,大夏三百年前,正是东汉末期魏蜀吴三国角力之时,镇北将军顺平侯赵云赵子龙,正是冀州常山郡真定县人,当年京师大学求学之际,浑身是胆的常山赵子龙,当然是那群热血儿郎的仰慕对象,虽然吉良庸更为推崇黄忠黄汉升,他跟韩擒虎、阳彦空、桂茂青曾辩过勇武天下第一的人物,吉良庸的观点很犀利,黄忠出仕昭烈帝,已是七十出头,此时已距昭烈帝十八路反董二十年,倒推二十年,黄汉升弓术天下第一,最多五十岁去单挑吕布?谁是飞将还不一定呢?
众人都知道这是吉良庸借以自夸,因为他吉良庸也是走的弓马路子,偏偏还奇准。
收起回忆,吉良庸继续找路,赵子龙胸前绑着后主刘禅,虽然是个废物皇帝,但是也是真命天子坐了江山三十多年。大夏朝开国太祖出身荆州,以恢复两汉一统为己任,所以正本追溯,以蜀汉为尊。
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又看了看怀中蕊儿,蕊儿若是哪天能成为人中龙凤,算了,一个女孩家能有什么大出息,但是他又禁不住联想了,如果蕊儿真的有天命相佐,那柯丽儿岂不是做梦都要笑出来,那他百年以后,是不是也能被追封个帝王至尊啥的?
估计很快就能找到了,他一路问了两拨行人,方向都没错,眼看路口也稀散有几乎人家,其中有一户以布搭棚,摆了个“大碗茶”的招牌。吉良庸下了马,抱着蕊儿走过去,他又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昨日下午茶的感动,依旧历历在目,所以人往往都有这个心理,在哪里有了好处恩惠,就往往把这些身外之物神思刻画,变得有灵有性起来,这大碗茶,现在在吉良庸眼里,也是个绝佳的去处。
把两匹马的水囊都蓄满茶水,在此期间他和摊主,一位中年农妇已经聊了好几句,这是一个勤快也贪财之人,两子已******别处居住,其夫去丰县苕卖瓜果。农妇一文钱两碗茶,吉良庸给了她三钱碎银,该农妇心花怒放侍奉着这财神爷。吉良庸略做了下思考,鼓起勇气做出决定,
“这位大婶,我有一事相托,不知道可否商量?”
财神爷主动开口,农妇乐开了怀。
吉良庸缓缓开口,说出了目的,开出了条件。照看蕊儿最迟到申时,每个时辰一两银子,若是过夜提到五两,蕊儿不得跟他人在一起,她看管需要谨慎。订金先付一两。为怕农妇生疑,他告诉农妇自己要去找屠夫商议,生杀屠宰之地怕惊吓小儿魂魄。村野之人信的就是怪力乱神,这妇人毫不怀疑,喜滋滋地抱着蕊儿,看着吉良庸扬马而去。
吉良庸想赌一下,中午那个二马,他始终觉得不是个善茬,他的确爱马,而且也许比吉良庸更了解这匹马。所以,吉良庸顺水推舟按照他的建议来找这个马场,如果吉良庸赌对了,这二马肯定要出现,但是他出现的结局,可能不会太美满,刑侦捕讯多了,对于反常的气息,有着异常的嗅觉,这二马带给吉良庸的,就是一股威胁的气息。
另外赌一下,吉良庸是把蕊儿的安危,暂时托付给了这个农妇,这个赢面非常大,他没太多担心。
也就四里路的工夫,他就摸到了这个马场,老板是个魁梧大汉,问了吉良庸的来意,出来看了看两匹马,点点头,让伙计带着吉良庸去客厅歇着,自己带了几个人牵着青马去后院,准备放倒马儿,仔细查看,为多赚点生意,他让吉良庸把黄骠马也检验一下,顺便补补马掌,黄骠马蹄铁没有烙印,他们应该看不出啥,于是吉良庸答应了。
一碗茶换到第三遍水,门外传来了一个声音:“有看到一位尖脸高个,一身黑衣,牵匹藏青色马儿来求医的汉子嘛?还带个孩子。”伙计的回答也很干脆“是有个高个子在,但没带孩子呀。”
话音未落,这二马踏进客厅,吉良庸的眼神正候着他呢。
视线一交锋,这家伙一个弯腰鞠躬作揖,“小人冯五杰,问吴大人好。”
吉良庸示意他坐到自己桌左手边,冯五杰乖乖坐过来,吉良庸一边做出打探四周的神情,其实一边在考虑该怎么开口。
“为啥着急着忙追来,不怕走漏风声?!”吉良庸瞬间就拟好了对策,这不是审讯犯人的伎俩,审犯人不可主动出击,而是他在官场上看到的上司诘问下属的惯用手段,那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劈头盖脸把你批评两句,指出你不对的地方,被骂的下属自然会解释的,聪明的上司就靠这招来弥补自己后知后觉的缺陷。
眼神交锋是第一招,那家伙的主动示弱,说明他还不掌握情况,气势先输了一招。
上来就被无头诘问,冯五杰开始紧张了。
“小人左等右等,不见快马信差过来,中午到客栈本想打听一下,看见那匹青马,又见大人模样,寻思着应该是,但是那个孩子让小人左右都摸不清头脑啊。”
“老爷交代的,我怎敢多问,你以为我想啊?”
“是是,大人安排的,必有他的道理。”
“你现在做何打算?”
冯五杰也起了疑心,这吉良庸句句都在打马虎眼套他话啊,“所以我跟随大人至此,就想面侯指示。”
吉良庸伸手入怀,从钱袋里掏出吴文静的名牌,给冯五杰看了一眼,然后又收回怀中。
冯五杰疑心还是不减“吴大人准备做何打算?”
吉良庸伸手又摸起来,摸的时候其实在考虑,所谓虚虚实实,不拿点实际的东西,怎么能套到靠谱的信息?
送至汝南县的海捕公文,推到冯五杰面前,冯五杰连忙拿来,在手里观摩了一番,轻声叹气“这六扇门的死规矩,吴爷到汝南来回的距离信早就到了,咱这等淮州的文书,还是不见来。”
吉良庸轻扣桌面,“你错了,我还没去汝南,”
“啊,那吴爷延时送信,恐怕不好交差啊”
“所以这马的伤势,难道是假的?”
冯五杰眼珠子转了一圈,琢磨着是这个道理,一哈头“那孩子是个文章?”
吉良庸一竖大拇指,“到底是六扇门的,你这思路见识,够水准!”
“吴爷见笑了,小的这里做足了功夫,礼都送了三遍了,这六扇门现无空缺,小的只能以杂役候补呢?”冯五杰摇摇头很不忿,
吉良庸心里暗笑“原来只是个协管”,一边正色安慰到“六扇门不比其他衙门,直通上听,责任重大,门槛高着呢,不止是你,连我在里面耕耘了这么些年,也还不是个起步桩子?末等三月?”
这当然是事实,对六扇门的看重,始于三国时曹魏,本朝太祖情通魏武帝,礼奉蜀汉昭烈帝,各取齐长,六扇门的头头,刑部尚书和两位侍郎,可是随时随地能面圣的,不会管手下的皇帝不是好皇帝。
冯五杰继续说到“小的安排了自己兄弟去淮州来路候着信差了,备好了马匹,好让徐州早点得到通报。”
“这主意好,你看我双马换乘,疲于奔命啊”,吉良庸嘴上夸赞,心里骂着“去你妈的臭协管。”
顺着冯五杰的思路,吉良庸主动说到“徐州地界不大,正式文书收到,冯兄要抓紧行动,争取擒得首功,到时候打点已到位,功劳又有,名列正籍指日可待啊”
冯五杰当然心旷神怡,胡思乱想起来“那还多亏吴大人指示提携啊”
吉良庸抛开笑容,直奔主题而来“但是,你们还是太过疏忽,你早已知道要擒拿重犯,为何不安排人手在道口清点协查?凡有案底,必定做贼心虚,遇到鬼鬼祟祟者,直接拿下,宁可错杀一百,这点道理不懂?”
冯五杰着急得脸色都变了,脖子一伸,探头过来就诉苦“大人冤枉,小的们实在为难,两旬之前就通知我,要我本月上旬准备收淮州海捕文书,擒拿要犯,但是抓的是谁,当时来人根本没说是谁,只让我们提心等待。”
吉良庸微微一愣,记住这个要点,这是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明他去明州采购后,就已开始被人利用陷害。
吉良庸也故意露出惊讶之色,“早知道冯兄如此烦恼,可惜我吴某不通文墨丹青,要是有擅画者,我口述他描绘,留下一些可辨形象,或许可以助冯兄一臂之力!”
这个大胆的假设,恰恰好好钻进了冯五杰渴望得功转正的心里。
不等冯五杰反应,吉良庸又抛出了另外一个包袱,“其实我这里有现成的海捕文书,可惜上面官漆封口,我怕开了就缝合不上,到时候私开封条的罪名,不是闹着玩的。”
看着冯五杰纠结选择的兴奋之情,吉良庸知道下午这场赌局,他又赢了。还是六扇门教会他的,如果要猎物上钩,不妨扔一个让他自己思考,如果他已经开始思考,那就再扔第二个,这样他就不会思考对策,而是开始去做选择。
冯五杰人在桌上,低头向吉良庸重重一点,“吴大人的提携之恩,小的没齿难忘!”
吉良庸微笑着喝茶,对方做好选择了,根据他的选择,吉良庸再做打算。
“只要大人信得过,等下小的带大人进城,小的把大人安置在我城内住处,然后请大人将文书与我,签押房的兄弟,是我牌赌搭子,这小的搞得定,里面有现成的官漆封印,小的只要把字临摹下来,把画记牢了,然后小的即可回来,带大人去城西,那里有一个小的认识的画匠,这样我们俩一起把这画仿成了,城西正好可以通大路,小的再送大人出丰县界去汝南。”
“我勒个去!”这王八羔子低头找蛋这点时间,一整套私拆临摹的路数,居然都策划好了,还一步三算,妙计叠出啊。
“就这么办!”两人双双端起茶盏,相视一笑。
一个伙计奔了进来,“两位大爷,黄骠马的马蹄铁松欠了,要重新打进去,需要再花些功夫,掌柜让我来通知二位爷。”
吉良庸刚想说话,冯五杰已经回答了,“换,磨刀不误砍柴工,动作麻利就好。”
吉良庸想了想,问冯五杰到“你本来想把我骗到这里?查查我身份?”
冯五杰不好意思地笑了,“不瞒吴爷,那匹藏青纯种马,是扶余国走私来的,不止这一匹,整整二十船上千匹扶余良马,其中品种最高的,就是吴爷骑着这种青椎马,这马在扶余也极其高贵,当地人管他叫陆奥追风,还有同样品级的黑色马,叫出羽月黑。”
冯五杰第一次看到吉良庸震撼的神色,控制不住自己的兴奋,继续讲到:“我本来就是好马之人,当初进这批马,就是让我去做的督办,小的这差事办得不错,所以上头赏了老爷这个,”他摸出怀中一个物什,这下更让吉良庸目瞪口呆了。
这是一块粉红色的玉坠子,跟吉良庸给老婆买的玉髓里打磨出来的,色泽几乎一模一样。
今天这二马真的是吉良庸的贵人,他第一次让吉良庸明白,原来很多事情都是前后连贯在一起的,他要检索的线索,比他想象中的更多,现实,也在很沉重地提醒他,他要面对的这个阴谋和背后的势力,简直就是精心策划,刻意栽赃给他。
冯五杰看吉良庸的眼色,又多了些狐疑之情,不做声看看吉良庸反应。吉良庸不声响,往怀里又摸索了一会,找出柯丽儿的方帕,展开,铺在桌上,冯五杰也是吃了一惊,“大人亦对我说过,只有经过考验,值得信任之人,才能佩戴这红玉石。”吉良庸说完,冲冯五杰拱手,“大人麾下,能人辈出,今日遇到冯兄,小弟三生有幸!”
冯五杰彻底放下了疑虑,慌忙还礼“我这厢还未谢过大人呢!”
吉良庸重新把海捕文书拿出来,递给冯五杰,鱼儿必须要彻底上钩,冯五杰兴奋异常,想推脱又怕吉良庸反悔,吉良庸说到“我与冯兄相见恨晚,冯兄也莫见外。此物于冯兄有助,小弟就当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冯五杰忙不迭地收下了。
吉良庸嘿嘿一笑,继续扯到他感兴趣的话题上。“说起来,多亏了那匹青马啊,难怪大人郑重其事地把它交给我呢”。
这下又能打开冯五杰的话匣子,“吴兄有所不知,这种纯种青马少有,那千匹马儿里,只有三十几匹,所以你家大人,一定也是位居高位受重用的。唉,这些马当初我从岸边接过来,费劲老大力气去送到淮州,一路劳顿再加水土不服,死了病了有接近一成,真是可惜啊。”
“怪不得我家大人经常勉励我们要励精图治,要向其他兄弟学习请教,今天幸会冯兄,发现冯兄真是可堪重用之才啊!”千穿万穿,马匹不穿。
冯五杰打开的话匣子彻底关不上了“哪里哪里”,重重叹了一口气,继续缅怀起自己的丰功伟绩,“扶余过海运来,到镇海才上的岸,这一大片海路,不晓得经受多少惊涛骇浪,也难怪,北路关防甚紧,还好我大夏现在海上勘防未有太多动静,也鼓励外埠通商,否则这绕路过来早就被截留了。”
后面的话,吉良庸已经听不进去了,镇海上岸,镇海,镇海。镇海淮阳,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两人继续端茶,这时伙计走了进来,通知二位马匹已经处置好了。二人走出客厅,马掌柜已经牵着两匹马儿,有点恋恋不舍地俯拍着马儿的鬃毛,马通人性,两马亦是温顺地摇尾,纹丝不动,连响鼻也不发一个。吉良庸看看这马掌柜,他很理解这种见猎心喜的心态,跟他自己从前听到有要案要破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追逐梦想的地方。
申时已过,冯五杰带着吉良庸,两人三马,并排而行。两人都在紧张地思索着,冯五杰在考虑等下花多少银子能打通关节,而吉良庸在考虑下手的地方。
眼看前面就要经过那个茶摊,吉良庸心想千万不可被那农妇戳破,略一猫腰,从摊位前疾驰而过。又行了三里地左右,远远已能看到城墙,吉良庸心里不住叫苦,万一直接进城,让这小子直奔巡捕签押房,等他打开文书,发现跟他聊了一下午的知己,就是图上这案犯,这真是作茧自缚啊!
事不宜迟,右边那片小树林虽然狭小,但是现在必须行动了!他侧头跟冯五杰说到“冯兄见谅,下午茶水喝多了”,同时放低马速,转向向那里骑来。“吴兄小心,”冯五杰从后面跟来,神色略微不安地说到,“吴兄,其实我内急也有一阵了,但快进城了,想等进了城再说。”
“莫非那片树林有异?”吉良庸察觉到了冯五杰的不安,不管如何,那里就是上天给冯五杰选好的送命之地!
“吴兄,不瞒你说,这片林子是片凶地,燕王之乱慕容鲜卑侵袭的时候,这丰县曾经有场恶战,后来阵亡敌军尸首都被埋在那里做了冢观,阴气太盛。”
“那更好了”吉良庸心里暗自盘算着,骑到林边跳下栓马,自顾自往林中走去,“做大事岂能惧怕这些阴魂鬼祟?哎呀,下午看冯兄豪情万丈的,原来也是个惧鬼之人”,边走边笑。
走到一棵槐树下,径直松开束缚,释放起来。
然而冯五杰还是保持谨慎,可能的确怕鬼,骑在马上就是不敢下来。
吉良庸一边尿,早已把冯五杰举动看在眼里,心里暗自着急“这贪生怕死的东西”。于是他边整腰带,一边右手朝林内指了指,“冯兄莫怕,人有三分怕鬼……”突然没了声音。
冯五杰正东张西望,扭头一看吉良庸已躺倒在地,吓得魂都散了。他连忙下马,抖抖索索,犹犹豫豫地往吉良庸躺倒的树下跑来,心内极为恐惧,不知不觉抽出了腰刀,战战兢兢地猫腰过来。
吉良庸闭眼听着冯五杰猫过来的举动,冯五杰下马的方位他已经看到了,现在他要盘算最佳的攻击时刻。如果冯五杰也像他昨晚对吴文静那样,拿刀来戳,那吉良庸的西洋镜就要戳穿了。
于是只见吉良庸睁开双眼,咳嗽了几下,摇头晃脑地准备站起来,冯五杰又惊又怕,走到前面问到“吴兄,你怎么了?”
吉良庸摇摇头,没说话,却伸手从腰带内侧,把吴文静昨晚那封密信拿了出来,站起身递给冯五杰。“这是?”冯五杰晕了,“大人的密信。”吉良庸说完,又重重叹了口气。
冯五杰彻底晕了,难道这密信是跟我有关的?双手战战巍巍展开密信,刚看完右边一列“尽速斩草除根”,一阵剧痛传来,眼睁睁地看着一柄剑锋,露出自己胸前,这才意识到已吃了暗算,他想喊,却发现自己只能大口呼气,根本发不出声,一阵天旋地转,像瞬间被抽去了骨架,瘫软成一团。
吉良庸拔出宽刃剑,这剑过宽,所以给冯五杰造成了极大的创口,眼看这冯五杰的身下,已经是血汪汪一片了。拾起地上的密信,慢慢叠好,重新塞回腰带里。他思考着这么处理冯五杰的尸首。然而冯五杰还没有断气,看着吉良庸,目光流出乞求之色。
吉良庸却一点都没有任何悲悯他的意思,走到冯五杰身前,人还没死他就开始搜身,当然,冯五杰的东西,他要的不会太多,他的目标只是那块玉,藏得不深,很快就摸到了。
“冯兄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嘛?”吉良庸讥讽道,他考虑过了一遍自己该说什么,废话不能多,还不到笑的时候。“因为你去过镇海。”
冯五杰眼中露出的已是绝望之色,正中吉良庸下怀,吉良庸转身走开,那封海捕文书他不打算要回来,他带着进城万一被搜出来,不打自招,人家连文书都不用等了。和冯五杰在一起,那封文书会引起六扇门追捕者更多的怀疑,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一切只是拖延。
他其实没有走远,瞄着冯五杰用尽最后力气在身旁地上比划后,他又慢慢踱了回来,冯五杰已经出气多进气少了,看到吉良庸回来,只能看着吉良庸,眼神里没有任何含义。吉良庸翻开他的右手,露出他身旁的字,他举着冯五杰的手指,慢慢地把那个歪歪扭扭的吴字给擦去,另外一个,果然是冯五杰临死前听到的镇海,镇字都未收笔。此时冯五杰的手已毫无力道了,吉良庸伸过去摸了摸他左手的脉搏,放心地放下,把右手重新覆盖在字上。然后,用衣服擦拭剑上的血迹。一切完成,他继续考虑了一会,下了决心,才朝林外走去。
冯五杰其实是个很聪明的人,他能从陷害吉良庸的团伙中出类拔萃,跟他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他也一样在乎每一个细节,留心每一段经历,善于对比,勤于演练,所以,他比别人成功的概率也更高,因为他积累了比别人更多的碎片和细节,而且务实肯干。然而他还是比别人先死一步,死在了自己最惧怕的冢观阴地里,因为贪心而失去了耐心,他只要老老实实地等待官方文书来就好,可惜他选择了走捷径去博重彩,从而一步一步被利用,最后送了性命,如果吉良庸有一天能够扳回战局,那冯五杰在吉良庸的翻身仗里,扮演着一条救命绳索的角色,他的话,把吉良庸理不清的千丝万缕,巧妙地串在了一起,虽然只是冰山一角,真相却已在慢慢出现。
可惜了这冯五杰,只要简简单单的忍耐,他就可以把精心的准备付诸实施,即使在看到海捕文书肖像的时候有受骗上当的羞辱感,也并不妨碍他卷土再来。因为人生,偏偏可以输给受辱受骗无数次都能重来,但也许丧失耐心的那一次,会让你输个彻彻底底,精精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