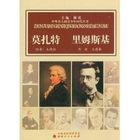她坐在竹凳上吸着旱烟,回想着往事。烟雾不停地从那个小孔里飘出,啪啪啪吸烟的响声环绕在这静静的堂屋里。
她皱着眉头不时地叹气,三杉的学费,家里的开销,手头上的钱,都摆在那儿的现实。空一个子,少一个子。
这喝西北风的日子,让她情不自禁地站起身走到了碗柜旁,在底坐下一摸,十六块光洋静静地趟在那儿,这是她和木匠在一起准备逃难时用的,在任何的困难面前却又从未动用过,它好象有着法宝一样的神奇怎能度过难关,一路走过的日子是平平安安。
九酒掏出一枚,看了又看还是放了回去。她放弃了,哪怕只用一块大洋,都会产生懈怠得不会看到到生活的奔头。它如一颗救命稻草的希望点燃着她心中的踏实。
可这需要钱日子,实在又让她左右为难着,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一个纯粹的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的文盲,此刻陷入在极度的焦虑中。
远方的儿子也让她挂念着,心里是苦得五味杂谈。三十多的一冰结婚也是二年了可还没有孩子的喜讯,是不是生活窘迫,想到这些她那发白的头发更显得苍老。越是苦闷越是担当家中烦事。
九酒这又点了一袋烟,眼前这小小的烟斗暂时能抹去她心中的冰凉!这个辛亥年生小媳妇,几十年的挣扎与木匠并肩而行,如今却要独立的面对生活,感到一切都好空。
她没想到在跌跌撞撞中拉扯大了三个孩子还是这么的孤寂无助。曾经的困惑还有木匠的一双大手可以遮挡,如今独自承担。
一波波涌上心头的记忆勾起着她这一生的回忆,不堪回首却又沥沥在目,眼前浮现起自己曾经还有两个孩子的过去。她偷偷哭泣起来了,或许木匠是去见那两个夭折的孩子了,
烟雾缭绕的堂屋,她数不清抽了几袋烟,迷迷糊糊靠在椅子上无力地睡着了,头疼得让她慢慢地眯着眼晴睡得特别舒服。
一觉醒来,全身都还酸疼着,但觉轻松许多。她翻来覆去地想着自己能做什么,她没有文化,她没有赖以生存的手艺,她没有自力更生的本领。
她有些怕向前走的日子,可在她的心思里从没有那个借钱过日子的念头,也更没有向在远方工作的儿子要一个子的想法。
她否定着这一切,只怪自己没有本事,该怎么办啊!她走进里屋,来到她绣花的竹蓝边,开始寻找一些针线活干。
突然之间,她觉得自己可以绣花和缝补衣服带孩子啊,这女人家能干的活她都会。
倾刻间便来了精神,这是她唯一可以的方向,她不知这能不能养家,但她需要尝试。
她的情绪高了点起身走到桌前,望着镜子里自己是憔悴的脸蛋,有着说不出的哽心。
她穿上了件打着补丁的白衬衣和纯蓝的裤子出门了,看着走在路上的自己,她觉得变了样子的轻松些。那有着六十年代洋气的味道在她身上浑然一体,尽管她的脸在那白发苍苍下没有一丝红润,但她总算愿意踏出屋门。
阳光也是格外灿烂,抬头一望却还耀眼,这是她在家阴霾了多日后,见到的第一道光明。
天不那么灰暗了,阳光把她的脸照得有些光彩,当她路过荣华斋,二毛打工的饮食店她走了进去,平日里她是几乎没来过。
走进了里间看到女儿跟着师傅在和面,二毛手脚麻利的样子,让她心里更多了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苦楚。
二毛这一抬头,看见是妈,脸上有着害羞地说:“妈,你怎么来了。”边上的师傅也立马停下手中的活。
见状,师傅忙道:“常听二毛说起妈妈,今天果真还来了,是不放心二毛吧,她好勤快,不错的。”
“我是路过这儿,不经意间就进来了,早该登门拜谢师傅的好手艺,二毛也才能学会做很多事。”
二毛的师傅看着眼前瘦弱的女子,心生怜悯,道:“二毛妈,你女儿聪明勤快,我教得不累。”说完连忙叫徒弟给她下了碗粉,她推迟不下只能坐下连汤喝了个见底。
她很开心吃下去的东西不那么堵得慌了,这么多天以来,这是她吃得最多最舒服的一次了,她觉得用语言都无法形容这种意想不到的温暖。
真道是:
一碗干面如滴水,善小心慈人开怀
春风拂柳冬远去,花红柳绿艳阳天
她再三感谢着师傅后,又走到女儿跟前,叮嘱着二毛要听师傅的话,才出得饮食店往派出所方向走去。
此时她是去注销木匠的户口,这意味木匠如影相随的身影要慢慢地在她心里消失,从此走上再也无依赖的生活,她要重新开始了。
正想着这事儿,前面一堆人往她这个方向涌来。她定睛一看,一个女的被打得鼻青脸肿,鲜血从口里顺着不停地流。
而有个男的被几个人用力地抓着他的双臂,男的还在大声地吼叫:"你这个臭婆娘,老子今天要打死你,你给我回去不。"
女的只知道哭,一句话也不说,疯了一样往前跑,鞋子都跑掉了,她好心疼这个女人的落魄样子,寻思着这应该是一家人。
突然间那男的猛然挣脱了众人,追上女人放倒在地下,一阵拳打脚踢,看得心里发寒。
她潜意识地想,女人就是犯了天大的错误,他也不该动手在大街上如此地污辱一个女人,这算什么男人,她很恨。她的木匠可是一根手指都舍不得动自己啊!
想到这,忽地不知道有多大的勇气,扯开众人便冲到那失去理智的男人的面前,刷刷刷猛抽了他几记耳光。一下子众人都木了,望着这个柔弱的女子吓了个惊呆。
顿时,旁边一阵掌声叫好,那男的也被震惊了,几个巴掌好像打醒了这个酒醉的男人,他停了手。
众人忙拖着男人以免他去伤及眼前这个无辜的女人,那眼露凶残的男人的目光盯向了她,但没有出手。
而她什么也不怕,还走近前,小心地扶起地上的女人,掏出口袋里的手卷,擦试着女人脸上的血,整理着那乱成一团的头发,女人抱着她是嚎啕大哭。
刚巧,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看到了这一幕,她的淡定让他有着不一样的眼光注视了她一眼。
对于这个凶狠的场面,这位干部也并没有漠视,道:“请你们帮忙,我们只能让他先进派出所说说情况了,这光天化日之下的打女人,不对的。”那动弹不得的男人,就在众人的不平与气愤中向派出所押去。
他并没有跟上,回头却有些激动地握着她的手说:"你不错吗,男人你都敢动手,我们街道上真的就需要象你这么勇敢的女同志,革命工作很复杂,你敢毫无顾忌地站出来,你真是了不起!"
她很奇怪,怎么这是革命工作,她也没多问,只是说:"没想到我今天这么大胆子,也不知怎么就下手了,我只是看到这种行为感到厌恶,我也是女人,知道女人的辛苦,怎么能这样伤害她呢?"她还带着些不平。
说着她就跟这位干部模样的人一起,带着这女人走到街边小诊所,为打伤的女人进行了简单清洗后,只见她真是哭得不停地说谢谢,好似受尽极大的委屈。
回到了家,她才记起,自己要到派出所办事的,给这么一耽搁就忘记了,又经刚刚折腾过,她今天已没心思再出去了。
她自己也不知道刚才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勇气,不计后果的朝前冲,她的胆子是哪里来的。
或许是这么多天以来的压抑情感象火山爆发,或许是骨子里本有的爱恨分明的性格,或许她就是为那妇女半边天的尊严,也或许是她真正走向社会的开始。
这一切连她自己也分不清,但对于刚才的出手她是前所谓有的胆大,相反她觉得今天的心情很轻松,这是不是象前跨出一步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