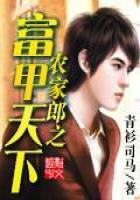十月二十七日,近千被隔离开来在西城门口等着出城的百姓对着十数辆马车小声交谈。那当首的马车宽大,披彩遮幔,两旁绣有鎏金汉字;六马八辕,马儿通体白色,其身披甲,头顶插有五色羽毛。身后八名骑士手执高旗肃立,再往后一辆辆马车虽车身不如当首那辆,却也装饰相同,隐隐可见那马车里露出的一辆张高鼻深眼之人。
城门一开,车队有秩序的出城,直至最后一辆马车消失在众人眼中后。又隔了小半个时辰,城门官兵才招呼着百姓们排队出城。
十月二十八日,金銮大殿之外,有资格上朝的官员们气象百态,有的面带怒容,有的神色忐忑,但更多的是茫然。在停了七日的早朝钟声再次响起时,百官透过徐徐打开的殿门,发现居然已有人等候在里面了!
....
......
杨应彦手里拿着一份户部即将颁发的邸报,脸色有些阴暗。前日的喜悦被邸报上的内容一扫而空。
那日,是他出口替宋安解了围。解释了缘由后,不光罗业,就连候莫宋安自己都是一脸的懵样,看着竟是丝毫不知情。不过也是凭此牵强的缘分,罗业允许他每日可来旁听自己为宋安授课。
小屋前,先生与宋安兄早已开始了授课。见着杨应彦到来,罗业没有停下讲课。只是眼神示意他自己坐下,倒是宋安不知是不是因为知晓了那层关系,很是郑重的起身行礼,关切问道:“应彦兄今日怎么这么晚?”在他心里,已是将杨应彦当做自己同门师兄弟了。
杨应彦向着他回礼。随即便恭敬将手中邸报递到罗业身前,“打扰先生了,还请先生看看应彦手中邸报。”
他还算不得罗业弟子,只能以名自称。罗业却也没怪罪他打扰自己授课,接过那份邸报翻开一扫。初始有些讶色,片刻便恢复正常。他轻飘飘将邸报再递给宋安,平淡吩咐道:“你看看!”
那邸报内容其实不多,很是容易理解。大体便是皇帝陛下感慨民生不举,将于下月初再开由北疆燕宁至西南坝葱沿途九大商阜,全面开通与盎西曼、波拉、西唐三国商事。汉境下,除官命在身者、刑期五年以上者、无籍奴役者。无分天南地北,亦无分士农工商,只要是大汉之民,若有意愿皆可到当地户部备案,行通商之举。一旦得户部认可,但凡行商商阜者,当地税率从明年起,首年皆免,其后减半,为期十年。
宋安这些日虽罗业一起,眼界知识懂得已经不算少了。看到这份可谓之布告的邸报后,心中也是大为惊讶。不过并没有立即出声,而是仔细想了阵后才道:“若能成,大盛之世将临!”
杨应彦是知道罗业真正身份的,要不然也不会苦求拜在门下。听及宋安这么一说,他先是一愣,随即便是愤怒。亏你还是先生弟子,竟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不过他修养极好,与宋安又有了那么层姻亲关系,难得未有失态,而是问道:“宋安兄可曾读的是圣贤书?”
宋安被他问住,想说些什么。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去,无奈看了师傅一眼。倒是罗业在旁咳嗽一声,为他解释道:“应彦啊,在我这里。为天下方为圣,虑万民才为贤。书里的那套圣贤理论,莫要用在此处训诂他人。”
杨应彦不敢置信的看了眼他,语气都变得哆嗦:“先生您.....”
罗业不悦瞟他一眼,道:“你什么你,好好听着!”又转头对宋安道:“说说看。”
“是,师傅。”宋安得了师傅偏帮,自信不少,接着道:“得师傅近些日教导,宋安明白不少。朝堂此举一开,以我汉地地广人博,民生将立增。虽当初圣人将商人贬为下流,但与今世不同。商贾在国力推动中已是不可或缺一环。就如此次新举,商事一开,可带动各道各州各县的粮产、手艺、车行。并可降低不少隐患,如流民、罪患。朝廷亦可从商户中取税,贴补农赋以稳定粮产,补贴工税激励工户。实乃一举多得!”
没等罗业出声,杨应彦已是忍不住了,接着宋安的话道:“宋安兄可曾想过,朝堂此举无异鼓励商道,而商人重利益而轻礼义,大汉每年罪患因商便占七成,不劳而尽享奢华。如此一来,万民羡艳享受,潮涌而至。那何人传道?何人工利?何人务农?江山如何能定,百姓何以存活?”
宋安并未受他话语影响,摇头道:“应彦兄偏激了!”
杨应彦气势更甚:“非仅是圣人,我大汉历代帝王即是看到商贾之害,所以数百年来才会尽力压制。士农工商,商为末等,宋安兄以为呢?”
宋安不答,论儒家学识,他终不是自幼从学杨应彦的对手。他看向罗业,希望师傅帮他把那些他说不出来的意思解释给杨应彦。
罗业饶有兴趣的看着二人争辩,见宋安词穷方才漫不经心说道:“应彦啊,你刚刚说的不劳而尽享奢华。我想了想,似乎你家也应该归于此类吧?”
杨应彦微怔,脸红耳赤争道:“先生岂能将杨家与商贾相比。祖父为国为民呕心沥血,操劳一生....”
“住嘴,住嘴。”罗业没好气的挥手止住了他,“江南道七月大汛,流民近千,你杨家在干什么?”
“祖父身居高位,岂可面面俱到。”
罗业嗤笑道:“可是在我等平民百姓看来,百姓流离失所可不就是包括你们这两位位居高位的祖父不作为而造成的吗?所以啊,应彦,你刚刚说的面面俱到四字可换个立场想一想嘛!”
见着宋安若有所思,杨应彦仍是气鼓鼓。罗业叹息着摇摇头,“你们俩其实说的都没错,但是你们只看片面,不及全概。呃,当然,宋安看的全一点,说的更好一点,不愧师傅多日的培养。”
他洋洋得意先自夸一番,见着杨应彦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对着他道:“万事发展定有得失,这是天道,避不开的。譬如你应彦尿急,又恰逢野外,你总不能担忧失了礼数而将尿溅在裤子上忍住吧。”
宋安想笑,却顾忌杨应彦的感受不敢笑。杨应彦沉着个脸道:“先生低俗了!”
罗业无所谓笑笑:“话糙理不糙嘛。就我看来,大汉此刻恰如一尿急之人,那泡尿就是如今大汉的穷苦。要么被尿憋死,要么就将那泡尿放出来。”
杨应彦摇头正想要继续说下去。忽然间,他似是想到了什么,脸色瞬间有些惊恐,话语也迟缓了许多,“常闻两位先生性情相投。难不成这份邸报的内容....”
见着罗业微笑点头,他下一刻竟似歇斯底里的吼叫出来:“为什么?你们二位天纵奇才,是圣学最优秀的传人,怎么能叛逆儒道!”
宋安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有些慌乱的想要上前安慰一番,却被罗业伸手拦住,“杨应彦,在你看来,儒学是什么?你求学又是为了什么?”
杨应彦仍是没有从刚才想到的挣脱出来,听见罗业问话,下意识回道:“儒学乃是治国安民之理。我等所学自当报国为民!”
罗业点点道:“说的不错!”他微顿,语气重了不少,“不过儒学也仅仅只是道德理念而已!”
杨应彦立即反驳道:“数百年的治下,莫不是依此而来,大汉不也一步步强盛起来了吗?”
罗业笑笑:“大汉承平两百余年,土地大之西唐二十余倍,人口多之十倍,且历代可称贤君者不下五位,可国力民生到如今仍是远逊西唐?以致唐人见我汉人总是蔑视称‘汉乞儿’。连血脉相同的唐人亦不服汉,何来强盛之一说?”
杨应彦哑然。
“当年圣人提出此言时,那是战乱方定,天下凋敝,执权者首重安定。在当时,商人的逐利的天性只会扰乱天下,是以圣人方才会将商道贬为末流。而如今天下承平,大汉却只是依靠亏损国力而强撑其表,这便是传统的国体约束了现今的国力。再不改变,最短不过三十年,国将不国也!”
杨应彦不服道:“先生是否过于危言耸听了?”
罗业一转脸色,严肃道:“大汉锁国,可天下万民并非无途听说。边阜红口,西唐商人处处可比,处处可见。现如今尚可以百年战乱为借口,敌视夷人唐人。但时间一久,百姓必然不从。人天性追富闲穷,你不见每年往返红口商贾何其多也?到时,天下百姓开始议论执权者时。莫说儒学,便是你将佛家那套转世理论拿出。也是定不了天下人之心的!”
杨应彦天性聪慧,加之眼界不凡。这些事如何不能望见?内心略有晃动,但十数年所学仍让他难以接受。不觉再问道:“为何偏走商道?先前应彦所担忧的,朝廷又改如何掌控?而且,最重要的,一旦商事大开,商人必然得势,而一旦商人得势,即会破坏大汉现有的阶层,必然要求与传统仕子争夺大汉的统治权。先生请教应彦,如何能避免大汉不会像盎西曼那样让国家沦为商人手中得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