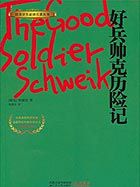回到固城时,已是中午。
街道两侧还是东倒西歪的泥瓦房,父母曾几次写信说家里的老房子都拆了,修起高高大大的砖瓦房。”可我怎么也看不到新房子。下街王家的女人,我走的时候就站在门口,两手叉腰,骂二哥如何如何地不要她的女儿,害她女儿年过三十还找不到婆家,我走了这么多年,她还在如数家珍般地骂二哥。村庄的门都朝太阳打开,供销社的台阶上,几只黑母鸡琢吃上面的虫子,时不时地朝街口传来的骂人声望一眼,瓦房顶细长的黄蒿倾斜身子,好像它们都是王家女人的呼应者。
我家还是两扇粗糙的白桦柴门,小时候写上去的两行字还在上面,炕上叠放红绸被,是二哥结婚时,大姐送的,母亲特意用它给我缝的棉被,看上去还是我自己叠的,整整齐齐,棱角分明。炕头挂一盏煤油灯,那年考初中整夜背课文,小学课本放在枕边,一截写秃的铅笔夹在课本中间。炕角堆放洋芋,是二哥从水泉湾背回来的,这么多年,洋芋一点没见少,家里人都吃些什么?
听得见大柳树上的蝉鸣,看得见院子里遗落的麦穗,正是碾麦的季节,心想他们可能在碾麦场,便将行李放在门口,朝碾麦场走去。心想,刚才路过碾麦场时怎么没有看见他们。
走到戏楼前,一股水从堰渠梁斜冲下来,径直流进下面的洋芋窖,洋芋窖塌陷,窖里积满了水,洋芋乱堆在窖边。水渠边长稀疏黄蒿,站在渠上的老水磨披身暖烘烘的太阳,磨门大开,磨炕上的火盆边有燃残的柴头,被柴火点燃留下小洞的炕席还是热的,磨房飘浮面粉,磨轮呕当呕当转,是谁磨完面刚走。估摸他没走多远,跑到高家园子边,大柳树下似有人影闪过,待我赶过去时,人已到上河坝的白杨林里,斑驳疏离的树影下,卧着耕地耕乏的两头黄牛。
回到河边,踩过摇摆的河石,听见牛拉碌碡碾场的辘辘声。从场门进去,木锨扫帚都站在仓库墙角,房中央放只大火盆,几粒火星明明灭灭,一罐薄茶咕嘟嘟地煮,火盆旁放顶草帽,帽壳压陷进去的坐痕还在,人肯定都在场院里。掉头出来,场院异常安静,什么时候村里人加大了碾麦场,宽宽泛泛地冒着湿气,像刚挖过的洋芋地。转眼工夫,碾麦场中站起两座麦垛样的坟墓,土瞬间板结,坟头蒿草摇曳。记得那里一直是两只碌碡的地方,靠东的一只长得像蟾蜍,四周长芽麦,身子底下是太岁的家,碾麦场的人马总绕着它跑,谁又搬走了它们呢?母亲坐在坟前,我走过去,叫声妈,我回来了。母亲没有抬头掰着竹齊般细嫩的手指头,好像没有听见,我摇晃母亲毛蓝布包裹的双肩问:“妈,我回来了,我昨晚给小军打电话说今天要回来,他没给你说吗?”母亲猛然抬起头问:“小军和二娃三年服都脱了,他俩的坟都长这么高了,你咋打电话哩?”我说:“我昨晚明明给小军打电话,他今天咋就死了呢?”母亲站起来指着河对岸的水泉湾说我们家的洋芋地被他俩取土取了十几年,修起几院高大的房子,给后辈儿孙的房都修起了,我说把地掏空要出人命,你二哥耕地时牛不敢进地,太阳一出来,地皮薄得像张纸,一眼就能看到地底去,年年的洋芋长不大。你顺哥到化绿山背麦时,看见他俩在地底下取土,地皮弓着腰,就要塌了,他俩咋劝都不听。没办法,你二哥就到大弯梁一天砍一背刺,背了几年才罩住地边,原以为罩了地,他俩就不会偷我们地里的土,可有一天,地皮塌了,把他俩压进地底,挖了几天才挖出来。母亲说完,看我一眼狐疑,坐回坟前,扯掉坟头的一张纸,对我说:“你看看,他俩是咋掏空一块地的?”我看见纸页上,两个人一趟一趟地背土,修起一院一院的房子。母亲伸手揭过这张纸,眼前便什么都没有了。我问母亲:“二哥啥时回来”?她说:“几年没有回家了,小军和二娃修房那年走的。”看着母亲平静的表情问我:“这趟回家三两天,能不能见他一面?”母亲说他走时说他剁够罩地的刺才能回来。你二哥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一辈子的活就想一天干完。我看着母亲坚决地说:“我要到大湾梁去找。不管他从哪里走,我都要找到他。”母亲抬起头,看着眼前远远近近的山峦说只怕你越走越离他剁刺的地方越远。”
我奇怪,昨晚给小军打电话,他的声音犹在耳边,今天他已死去三年,一个人从生到死究竟有多长时间?
站在空荡荡的场院喊二哥……我的声音落地的瞬间,一股风从远处呼啦啦飘来,又一股风从城墙上面滚下,抓起场院里的两座老坟,在空中翻了个跟斗,云朵般从村庄上空飞过。当我睁开被狂风刮闭的眼,场院依旧是原来的场院,码着麦垛,镰伽打,簸箕扬,牛拉碌碡碾麦场。人群当中,扎着小辫的红梅儿啥时从海边回来了,我跑过去问她,她却一脸糊涂,说她从未去过海边。一转身,小军肩搭麻绳从场门走进来,我问他:“你咋又活了?”他生气地说:“你从城里回来咒我做啥?”
四处寻找,场院里再也看不到母亲的身影,赶紧跑回家,母亲正蹲在炉前烧镆馍,看见我高兴地迎上来说,小军一大早就说你今天要回来,我都给你烧熟了几个苦豆漠慎。
我越发纳闷,村庄怎么一下子变得颠三倒四,一些人和一些事是很多年以前的,另一些是很多年以后才要发生的,却怎么赶在同一天到达,像要庆祝一个落后或提前的节日。
正在这样想时,二哥吆着骡马从后门回来,他笑呵呵地对我说:“水泉湾的洋芋都驮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