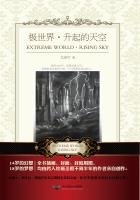收完秋天的最后一茬胡麻、洋芋和老梨树上的化心梨。月明星稀的夜晚,在无量殿镂空的四季花窗格前,点亮两盏葫芦状的清油马灯,孩童们欢声雀跃地喊:“挂灯唱戏喽,挂灯唱戏喽!”
吃过夜饭的村民,抬上笨重的长条板凳,女人怀揣刚从铁锅里炒熟的小豌豆,三五粒丢进嘴巴,咬得咯嘣咯嘣响,斜披夹袄的男人们一锅一锅地吸旱烟,东一句西一句说闲,头顶罩一层从他们嘴里吐出的蓝色烟雾。
戏总是在台下的一片抱怨声中开场。这晚唱的《铡美案》。顺哥扮演包拯。包拯身穿黑色蟒袍,黑脸红腮,额上半轮断狱明决的镰形月亮,两手轻按玉带,缓步走上台来。戏台左右放两张小方桌,正中一前一后铺两块木板,前边系白色帷布,上搁虎头铡刀。陈世美一身白衣,一袭黑发缠绕脖颈,由王朝、马汉押至台前,躬身低头。台下,蛾儿看到扮演陈世美的爸爸即将被铡,挣脱母亲的怀抱,在戏台口大哭起来,她太小了,爬不到戏台上去,便在地上滚作一团,女人们哄她抱她,她还是哭闹不止。直到脱掉戏衣,来不及卸妆的中红子从前台跳下来,抱起她说:“爸爸没死,爸爸活着哩。”她才止住哭,爬在爸爸的肩膀上哭着要回家,中红子只好抱她回家去了。
这是童年,唱大戏时台下最有趣的一段戏外戏。
1970年,无量殿里改唱《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村民们唱得不伦不类。不久,除“四旧”把无量殿拆了,村里再也没有唱过戏。而自乐班的演员没有散,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谈论唱戏的事。他们时而在山梁上喊一曲山歌,时而咒几句天爷,骂几声爹娘。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的春风缓慢飘到偏远的固城村,吹暖了自乐班封冻已久的心,自乐班的十几号人悄悄召集村民,要在无量殿原址重修戏楼。短短半年时间,钢筋水泥的新式戏楼落成,二哥当选为自乐班会长。
老会长张阿爸和二哥去天水市看了看,竟然产生了更大的想法,请来老班子人员,研究自乐班要为家乡造福,边唱戏边扯集市。
那些天,人们面带笑容,吆喝毛驴驮上小麦、包谷,到杨家寺、甘谷、武山、永坪去粜。二哥怀揣村民募捐的6000元钱去西安咸阳买来各色龙衣蟒袍,各色袄衣、女衣、裙子、裤子和战袍,包巾、虎背旗、会旗、小红旗、腰带、大帐子、凤帽、软帽、生靴、女鞋、扇子、镜子以及头盔、大锣、顶锣、小斗谬、大鼓、小鼓、战鼓、干鼓、抱鼓、铜号、挂灯、对板、单桌、二胡、板胡、笏板等唱戏道具。
大年将至,阴阳爷爷早早拟好对联,张贴在戏台两侧,上联为“文化园地,百花争艳”。下联为“忠孝礼义,古为今用”。横联为“发家致富”。正月初八晚,家家门前挂起红灯笼,悬挂在戏台上的500瓦的大灯泡照得戏台灯火通明,三层大幕重重挽起,台口两边端放两只铮亮的铜火盆,盆里盛放干柏叶、香和喜鹊窝。自乐班商量,国家允许唱老戏了,这是我们的福气,打台戏就唱《天官赐福》,老会长扮演天官,老艺人顺哥扮演灵官,从新疆赶回固城唱戏的田阿爸扮演寿星。
戏唱了十天十夜,戏台两边不断张贴宣传广告,要村民们在每月逢三、逢六、逢九做些小生意,摆些小地摊,尽快扯起集市,搞活农村经济。封闭几十年的传统老戏,在村庄里唱开后,村民们冒着严寒和大雪,站在淹过脚面的泥水中看戏,戏不毕人不散场。
然而,偏僻落后的村庄里,扯集闹市谈何容易。来年春天,自乐班全体人员商量后,再次宣传唱戏扯集,动员群众向外地亲朋好友捎话带信。以前戏是唱给山神爷的,现在是给自己唱,各家的媳妇、姑娘也破天荒地登上无量殿,用农家女儿的一腔柔情演绎一幕幕千古悲欢离合,给粗犷的秦腔增添了不少婉转悠扬。1982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春台会,固城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四乡八里的人都来了,街面有卖熟食的,卖小百货的,卖土特产的,走亲访友的。二哥把家里的农活全部抛在脑后,一门心思唱戏,既要摆放戏台道具,又要关照演员背台词、化妆,十天戏唱下来,老会长一病不起,二哥更是连眼皮也睁不开了。
四月初九,摆小摊的,由于生意不好,都渐渐离去,街面上只有两家卖面皮的,一家卖洋芋包谷的,还有一个修鞋的。二哥是个很倔的人,他召集自乐班人员及每户村民家长,在戏台开会,商议请礼县剧团来固城唱戏。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由于老人们的大力支持,这事就定了下来。
演员的饭派到各家各户,乡亲们拿出最好的东西给演员们吃,腾出最宽的炕给演员们睡。轰轰烈烈唱了十天戏,固城人真真实实的见了一回世面。然而,人走茶凉,集市仍然没有扯起来。二哥还是不死心,在全家人的谩骂声中,他再次决定请戏扯集。同年九月份,老会长请来西安咸阳市青年秦剧团。自乐班其他人员,分头去县城、天水、甘谷张贴宣传广告。每家每户都利用自己的店面,姑娘们把自己绣的花鞋垫都摆在地摊上卖。
那是我印象中固城人最多的日子,礼县城卖熟食的生意人,跟着戏箱子云集固城,杨家寺、小天水的生意人,用拖拉机拉着布匹、成衣、百货,在戏楼周围搭起布篷,甘谷、武山人翻过分水岭吆喝骡马驮着辣椒、蔬菜在街头摆摊设点,从弯弯的泥土街道到戏楼周围,人山人海,应有尽有。集市终于扯起来,自乐班几个人病倒了,老会长旧病复发,于同年底去世,老会长是带着微笑走的,他没留下一句话,但乡亲们心里明白他最后离开自乐班时想的是什么。
二哥因为唱戏耽误了农活,让父母和二嫂非常辛苦,趁二哥回家吃饭的工夫,全家人都劝他:“今年干下来,明年不干了!”二哥总是点头表示同意。到了第二年,二嫂抹眼泪,踏着缝纫机仍在轧唱戏用的护领、玉带。父母也东家出、西家进的请演员。总是好的角色争着唱、丑角丑旦没人上,遇上挑剩的丑角,二哥为了救场,脸上抹上油彩,不会唱也要唱,年年唱下来,二哥的丑角,在固城远近出了名,连她七岁的小女儿也穿上戏衣绣花鞋,手拿云帚站在台上当丫环。
春台戏、会戏、年戏唱完后,自乐班人员坐一起,在街面每人吃一碗面皮算是聚餐,然后心满意足地散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