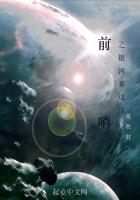晏战困惑地眨眨眼睛,抬头看看天,那里的确什么也没有,不过几片云,还有刺眼的阳光。他歪着小脑袋想了想,又撒开了小腿跟在那女子身后。
女子加快了脚步,晏战干脆抡起了小胳膊连跑带跳,一路气喘吁吁。还好他本来生得壮健,在林子里撒野惯了,这样的奔跑对他来说并不费力。但女子的步伐快得令人困惑。她讨厌他么?象巫医那样烦他么?也许她根本就嫌他是个累赘。他这样想时,不觉嘴一撇,停了脚步站在原地喊,“妈妈,妈妈……”这一喊不要紧,陡然令他对母亲添了一份思念,只片刻,便潮水汹涌地吞噬了他全部的委屈。
母亲的音容笑貌,母亲身上的气息,部落离别时,父亲有力的臂膀,巫医临走时挥动着干枯的胳膊……竟于一刻排山倒海般地向他撵来,“妈妈,爸爸,你们在哪儿?”他咧开了小嘴,凭白又多了一份对父亲的思念,一时涕泪纵横。没有人回答他,那女子的身影也由于眼前模糊看不分明了。他越哭越伤心。
“巫医……”又多了一个,“小宝,胖胖……”此时,部落里每一个人,都被他想起,都被他记起。他大哭着,喊着他们的名字,转身走向刚才走出的方向,“你们在哪儿?呜呜呜……你们在哪儿?呜呜呜……”
……
“妈妈,爸爸……”
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竟是越去越远?在前昂首阔步的身影忽然一愣,转身,却看见那孩子哭喊着朝他们走出的百合山谷行进。她一时困惑,撵了上去,却看见那孩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根本不看她,只是执著地朝他们刚刚走出的山谷前行。
她不觉出声,“你要去哪儿?”
那孩子抽泣着不语,撅了小嘴,一意前行。
“你到底要去哪儿?”她不禁狂喊。
那孩子被吓了一跳,猛然一怔,又咧开小嘴哭喊起来,“我要妈妈,我要妈妈,爸爸……”
她一时手足无措,那孩子不管,扯开了喉咙狂哭,“我要妈妈,我要爸爸……我要巫医……”
也不知多久,有一只兔子忽然受惊似地蹿了出来,浑身雪白,犹疑惊恐地翕动着它的唇鼻。那孩子猛然止了哭声,张圆了小口看着它,她伸手捉住,递到孩子面前。孩子将兔子抱在怀中,撅着小嘴看了半天,忽然抬头,“姐姐,我饿。”
女子一愣,哭笑不得,于是伸手去取他怀中的小兔,那孩子抱着兔子一躲,愣怔怔地看着她也不言语。她忽然明白,不禁苦笑,重重叹了口气道:“好吧,我去抓别的。”那孩子看了她半晌,竟咧嘴笑了。
她一时懊恼,在离孩子不远处搜索了半天终于抓到了几尾草蛇,便生了火堆,烤熟了给他吃。那孩子狼吞虎咽地吞下,心满意足地抹抹小嘴,便抱着小兔蜷在火堆边睡着了。女子长叹一声,也折腾累了,阂了双眼躺下。只睡到半夜,这才苏醒,高空繁星闪烁,一弯新月盎然挂在天边,那孩子睡得极香,梦里还咂呲着小嘴,迷迷糊糊喊着妈妈。她不觉微笑,细细盯着他的小脸,思绪便在一瞬间缥缈入了高空,繁辰之外。
她一生都不会有孩子,可因为百合山谷一行,上天瞬间给她带来两位天使。她不觉又摸摸自己腰间的竹筒,有一种别样的幸福悄悄弥漫心间。
她伸了手抚摸那孩子的面颊,温温的,细滑如脂。原来,生命可以如此鲜活,如此触动人心……指尖一时微微颤栗,她忽然有了想哭的感觉,鼻子一酸,带了些刺痛的苦涩,一珠泪无声滑落……
晏战永远也不知道,有那么一瞬,她几乎改变了主意。
第二日,天,大晴。
女子终于和这孩童达成了默契。晏战乖乖的,抱着小兔亦步亦趋,非常老实地跟在她的身后。
母亲没了,他心里很清楚这一点,眼前的姐姐或许能带着他找到父亲,他只有跟着她。他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怀中的兔子身上。有意无意间,他豁达开朗的天性保护了他。可每每念及母亲和死去的亲人时,他都会鼻子一酸,呜呜掉下几滴眼泪。可是,他明白,不管他怎么哭怎么喊,他们都不会回来。但他的童年还没有结束。姐姐坐在河边梳洗,他也伸了小脸对着水里的倒影用手抹脸。姐姐弯腰在地上拾掇野菜,他也会学着她的模样,在地上抓一把草。姐姐很爱笑,矜持地,低声地笑,可很少和他说话。他不觉得那有什么不对,重要的是每次吃东西时,姐姐总是拣最好的,最美味的给他吃。
二人就这样一路行来,倒也相安无事。
这一日,林子渐渐稀疏了,林中纵横交错竟有许多人类走过的痕迹。甚至有的已经清晰成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上面并排走上五六个人也绰绰有余。
“我们到虬城了吗?”晏战抱着小兔问。
女子一愣,“你怎的知道虬城?”
“妈妈说的,妈妈说爸爸就在虬城附近,那里有好多人,好多房子,可我一个都没看见。”
女子一笑,“怎见得,我就一定会带你去虬城?”
晏战挠挠后脑勺,“可……可是只有虬城才有很多的人。”
“可我们一路上没有看见一个人呀?”女子忽然起了童心。
晏战指指地上交错的道路,“你看,这都是人走出来的。妈妈说,虬城很大的,只有虬城才有这么多人,才能走出这么宽的路。”
女子笑了,忽然明白在这孩子小小脑袋里只要人多的地方一定是虬城。“是,你真聪明,我们是要到虬城了。”她赞赏地说。
“那我就可以看见爸爸了?”
女子一愣,她压根就没想过要将这孩子送回到他父亲的身边。虽然这一路上,她断断续续从这孩子口中打听到了他的身世,和他所经历的一些片断。但就这样白白送回他亲人身边,她还不太舍得。寂寞久了,她的身边多是静寂,忽然有个孩子又哭又闹,又笑又跳,她才有些感觉到活着的快乐。
童真于一瞬熨贴了她内心深处渐起的褶皱,缓缓消融于岁月无情的斑驳。相较于这种奇妙的体验,虽然经历岁月的沧桑,她的脸没有丝毫的改变,但那不是她想要的幸福。
有急促的马蹄向她迫来,她还一时未从自己的思绪中抽离,一只稚嫩的小手便伸入了她的掌心之中。她浑身一颤,微弱的温度于一刹奇妙传递,触及肌肤,顺手臂蜿蜒而上,直达肺腑,竟使她有了一种莫名的颤栗。
“姐姐,我怕!”
她看着孩子,那孩子眼里的惊恐竟使她心生怜惜。抬眼,一队骑马士卒牢牢将他们围在中央,为首的座下一匹黑缎似的战马,身后一袭大氅如飞瀑流泻,瞬间遮了她的视线。
“原来是虬族圣姑——司孺,”那骑马的武士说,语气中缺乏最起码的礼貌。“您老人家怎的到了此处?”女子不答。晏战心中微微有些惶惑,这姐姐看起来那么年轻,何以那位武士要称她为“老人家”,在他的印象中能配得上这种称呼的,应该是和营地内那些婆婆大爷一样的年纪才对。
那人微微一笑,侧头,左颊醒目的“将奴”刺青铜浇铁铸般烙上了他一生挥之不去的耻辱。“速速告于英将军,有贵客来访。”身后一骑听令,掉转了马头绝尘而去。
晏战一吓,他认得他们左颊的标志,那是屠戮他族人的凶手,他永生都难以忘记。他本能地握紧了女子的手,躲在她身后。司孺的手陡然一沉,这一路行来,恍恍惚惚,竟未曾发现这附近有将奴埋伏。
半晌,有悉瑟的衣袂之声,将奴铁蹄缓缓散开,一人昂首挺胸,徒步走来。马上众武士右手抚胸,弯腰行礼,显得极为恭敬。那人身形颀长,秀眉星目,面如冠玉,年纪二十五六岁,也许略大些,身着猩红大氅,黑甲战袍,腰间系了一把长剑,却是一个风度翩翩不失英武的青年。
司孺一见他,鼻子里放出一声冷哼,显是极为不屑。那人也不生气,恭恭敬敬地行礼,“英正参见圣姑。”
他的身后募地旋出一位冰肤雪颜的女子,晏战一吓,急急后退,只见那女子行至姐姐身前盈盈一拜,道:“慈牙见过圣姑,多谢圣姑救命之恩。”
晏战这才看清,这女子虽然和他在百合山谷所见的女子一样的肤色,但眉眼柔和,显然不是同一个人。
司孺昂然,冷冷道:“你用不着谢我,谢你的英正吧,他以毁我旧宗庙要挟,我才不得不救你。”
英正微微一笑,抱拳行礼,“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过圣姑。”说着示意慈牙,慈牙再次行礼。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