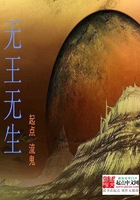形势转变太快,众人还未回过神来,南宫齐婴已经拉了容玉匍匐于地、叩首谢恩。祁王面色铁青,如此响亮的一个耳光,却怎奈是天子甩过来的,再如何不服也只得忍气吞下。
本想着今日朝堂还会有一番艰难的容玉此刻面上露出几分疑惑来。目光流转间不禁意对上一双如星辰闪烁的黑眸,纵然隔了轻纱却仍然挡不住几乎能将人吸进那深不可测的瞳眸之中的灼灼之气。容玉深深吸了一口气,收回了视线。却又瞥见另一道愤怒中夹杂着不甘的目光,容玉嘴角轻弯,几不可闻地冷哼了一声……
祁王世子的目光似要穿透那薄薄的轻纱,眼神中的狠厉似乎要生生将轻纱下的女子灼伤。她宁愿拼却名誉和终生,也不愿入祁王府,自己都这般在君前恳求,她却丝毫不为所动……想自己堂堂世子,天之骄子,也算是玉树临风,琼玉之姿,京城王侯勋贵之家的姑娘谁不是卯足了劲儿地想要嫁给自己,偏生这个容玉竟然如此不识抬举!越想越不是滋味,正要上前去问个明白,却被身边的祁王一把拉住:“还嫌丢人丢得不够?”顿了一顿又故意压低了声音低低叹了一句:“今日之事已成定局,容家那丫头,怕是不简单,我倒是小瞧了她!”
散朝之后,南宫齐婴看也不看容玉一眼,自顾自地向外走。容玉无奈地耸耸肩,嘴角一撇,随即像个敬畏父亲的大家闺秀一般亦步亦趋地跟在南宫齐婴身后出了未央宫大殿。
看着那个娇小的身影随南宫齐婴迈步出了大殿,姬蕴又转头看了一眼此时空空如也的御座,想起皇帝临走前在大殿中扫过的那一眼,尤其是落在容玉身上的那一眼,眉头不禁一皱。
殿外的台阶上,南宫齐婴放慢了脚步,一侧头便看见那个小小的身影,到了嘴边的话突然就这么哽在喉咙里,半晌才终是故意放冷了声音道了一句:“四年也没长了身量,容家就是这样宠你的?”
容玉脚步一顿,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南宫齐婴话里的意思,敢情是说自己长得慢,如此想着不由自顾自地将自己从上到下看了一遍,嘴角一抽,这还叫长得慢?在同龄人中自己算是身量高挑的了,虽算不得丰腴圆润,好歹也是莹莹如玉,莫不是父亲还希望自己被养成个大胖子不成?
心下这般想着,脑袋一歪,调皮地眨巴了几下眼睛,嘴上也这么说了出来:“难道父亲希望女儿似郭重那般?”郭重是春秋时期鲁哀公身边的一个极其肥胖的属下,因哀公为讽刺孟武伯惯于说话不算数而说郭重的一句“食言多也,能无肥乎!”而闻名。
刚刚走近的姬蕴正好听到容玉这一句,忍不住轻笑出声。南宫齐婴父女闻声回头,便看见姬蕴一只手轻握成拳,置于嘴边,状似缓解尴尬地咳了两声,才上前朝南宫齐婴拱手一礼:“南宫将军!“
南宫齐婴微微眯了眯眼,对于这个南越左相,说不上好感,却也不排斥,素来与之无甚交集,不过今日大殿上他那一番话倒是让南宫齐婴意外,于是回礼道:“今日圣前多谢姬相仗义执言!老夫感佩于心!虽朝堂之事所能尽之力绵薄,但若是姬相日后有其他需南宫府周全之处,老夫定全力以赴!”
南宫齐婴一席话说的有礼有节,姬蕴是何等心思,焉能听不出其中深意。南宫世家百年根基,势力盘根错节,在朝堂之上有多少派系想要拉拢,怎奈南宫齐婴为人爽直,历来不参与党派之争。如今这话明面上是感激姬相的仗义执言,实则却也是告诉姬蕴,若是存了拉拢之意恐怕要让对方失望了。另则,言语中只提南宫府却只字不说南宫世家,这明摆着是说我南宫齐婴承你的情,可这与并不等于南宫世家要为此记你的恩。
姬蕴似乎并不以为意,只是若有所思地勾起了嘴角,薄唇开合间,低沉的声音像是浸过了陈年的佳酿:“南宫将军多虑了,本相不过是受人之托罢了!”
南宫齐婴和容玉闻言均是一怔,但看姬蕴一副不愿多谈的样子,南宫齐婴也并未深究他是受了何人之托。容玉突然想起哥哥在她进宫前说的一番话,顿时了然。
南宫齐婴与姬蕴又聊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场面话,然后各自告辞。
临走之际,姬蕴将目光落在一直乖矩不语的容玉身上一瞬,说了一句:“翁主聪慧过人,假以时日,定成大才!”说着不等南宫齐婴说话,便转身离去。只是在转身的一瞬间,似乎听到一声若有似无的抱怨之声,如果没有听错的话,那软糯稚嫩的声音说的是“顽劣之人多作怪!”
姬蕴脚步一顿,薄唇一抿,胸中隐有笑意溢出,心道:真是个记仇的小丫头,竟然还在为大殿之上自己说的那句“顽劣之罪”耿耿于怀。思忖间,嘴角的笑意越发深了,连着脚下的步子也轻快了许多,看得迎上来的侍从眼皮直跳。
宫门口,容云鹤见容玉跟着南宫齐婴出来,面色一凝,随即迎上前去:“誉见过父亲大人!”
“哼!”南宫齐婴冷哼一声:“老夫可当不得容大公子这一声父亲!”
容云鹤似乎早就料到了南宫齐婴会有此反应,面色如常地拱手行了一礼:“生育之恩,血脉之情,不敢忘!今日朝堂,多谢父亲大人相护,玉儿才能有惊无险。祖父大人已经在来京城的途中,抵京之日定亲往南宫府拜谢!”
南宫齐婴一听容云鹤此话,面色更为难看:“老夫护自己的女儿,何须他人拜谢?容大公子莫不是忘了,九儿的宗籍尚在南宫山!”南宫齐婴话里话外只称容玉为九儿,明显还在为当年容玉入容家改名一事耿耿于怀。
容云鹤面色一沉,正待说话,却见容玉蹦到自己身前,亲昵地挽住自己的胳膊,撒娇道:“哥哥不是说母亲也会随外祖一道回京么?”
果然,容玉话音未落,南宫齐婴只觉浑身一僵,不过很快便恢复如常。容玉称呼容老太爷那声“外祖”似是取悦了他,看了容玉兄妹一眼,嘴角泛起一丝极轻微的笑意,转身就走向自己的马车。刚走了几步似乎想起什么似的,又回头冲容玉说了一句:“你祖父下山了!”说着再无半分停留地离去。
容玉这才发出一声惊呼:“爷爷从南宫山下来了?”一思量便觉恍然,看来若非爷爷下山,父亲又怎会对自己这般和颜悦色,虽然南宫齐婴至始自终都未曾真正和颜悦色过,不过了解他脾性的容玉却是知道他如今这般对自己已经算是不易了。
容云鹤不以为意地笑笑,一边拉着容玉的手朝容家的马车走去,一边随手拿下容玉头上的帷帽朝一路小跑过来的奴儿一扔,然后修长的手指在容玉双丫髻后一阵梳理,容玉垂于身后及腰的长发本来就很柔顺,被容云鹤的手指拨弄过后更显得服帖。
容云鹤目光宠溺地看着眼前娇俏的妹妹,这才满意地点点头:“倒是顺眼了些!这才是我的小玉儿!”
容玉眉眼弯弯,长长的睫毛像蝴蝶的翅膀似的忽闪了几下,细腻的眼窝处立时便有阴影闪烁,如瓷玉娃娃般精致的脸上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迎着阳光的少女的笑靥几近透明,还泛着莹莹如玉的光泽,一对灵动的双凤眼顾盼间竟羞得连阳光也黯淡了几分,那样纯净得不染纤尘,明丽得不似人间的笑容一时间竟使得一旁拿着帷帽的奴儿晃花了眼,怔愣在了原地。
而晃花了眼的又何止那奴儿一人,远远地迎着阳光走出宫门的祁王世子刘夜刚一抬眼看见的便是这样一幅美得可以入画场景。“砰“的一声,心中某个地方不受控制地猛跳了一下,有什么似乎要冲破胸膛喷薄而出,眸中颜色瞬间变幻莫测,不过须臾,眼神便随着那被容云鹤扶上马车的纤纤背影消失在落下的车帘内而黯了下去:原来……她就是容玉!容玉,容玉,容颜如玉,人若其名!原来那就是自己原本的妻!
当那个“妻“字浮上脑海的那一刹那,刘夜只觉心尖上好像突然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生生的疼!猛然间伴随着莫名的怒气,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前去,不顾形象地拦住了正要离开的容家马车。
一只修长的大手自马车内伸了出来,车帘的一角被掀起,露出容云鹤眉头紧皱的俊颜:“祁王世子可是有事?”
刘夜透过车帘被掀起的一角朝车内望去,却被容云鹤不着痕迹地挡住:“若是无事,还请世子移步!”
“我有话要问容玉,请大公子应允!“刘夜虽说心中愤愤,却也知这位容大公子不好惹。
“舍妹今日大殿之上受了惊吓,恐怕此刻不能见世子!“容云鹤冷冷回绝道:”世子与舍妹婚约已解,若是再这般直呼舍妹闺名,似是不妥!”
“我只问容……女公子一句话!”刘夜强压住心中的不满,固执的目光似乎要穿透容云鹤的身体直直看清车内之人。
见容云鹤似是在思考,刘夜趁其不备一把掀开车帘子,容云鹤面色一沉,终究是未再阻拦。
容玉正懒懒地倚在马车内的一张紫貂皮垫子上,身子斜斜地靠着绘有繁复花纹的金丝锦绣圆墩靠垫儿,白衣胜雪,容颜倾城,虽然稚气尚未完全脱去,却仍是自有一番艳艳独立的风姿。现下这么随意地倚着,身子仿若无骨,说不出的慵懒,说不出的动人。淡淡地瞟了一眼还保持着掀帘姿势的刘夜,容玉身形微动,目光却是骤然一冷:“世子这是何意?”
刘夜深吸一口气,目光灼灼地落在面前的女子脸上,道:“那日,我在稻黍稷遇见的并非容二公子,是你?!”虽是问话,语气却是十足十的肯定。
容玉嘴角轻轻一勾:“世子难道不曾听说容玉与二兄本为双生子?”
刘夜面色一顿,心中却是在揣摩她这句话的真假,良久才又道:“你是不是从未想过要嫁于我?就算母妃没有上门,就算你未曾遭劫,就算我从未与那修成君府有婚约,你……也不会嫁于我?”
容玉面上一凛,不曾想他竟问的是这个!思忖间秀眉不觉轻轻蹙起,而一旁的容云鹤却是不禁多看了两眼刘夜,如果没有看错的话,这位眼高于顶的世子方才跟自家妹妹说话时眼神中明显透着紧张和忐忑。
“世子要问的如果之事,乃未发生之事,既是未发生之事,恕容玉无法预知!”良久才听见容玉轻轻浅浅的声音飘过。
刘夜却是不依不饶,固执地盯着容玉,颇有不得到答案就不罢休之势:“你只回答是与不是!”
容玉似是未曾料到这祁王世子这般难缠,不禁再次抬眼看向他。四目相对,一个灼灼不让,一个清冷浅淡,一个神色复杂,一个面露疑惑……似乎对峙了很久,久到刘夜以为她不会再回答他的问题时,只见容玉璨然一笑,如满树繁花盛开,樱唇开合间轻轻流泻出一个利落的“是!”
刘夜捏着马车帘的手一紧,眼中似有波涛汹涌,半晌才见他眸色深沉,复杂地看了容玉一眼,骨节分明的大手一扬一甩间,车帘落下,隔绝了两人的身影,也隔绝了本应该交集的两个人生……
容玉只觉车内蓦地一暗,紧接着便听见容云鹤冷冽中带着一丝警告的声音响起,话是对刘夜说的:“多谢世子承让!今日之事到此止,世子与舍妹缘分已尽,他日再见,权当陌路,否则再有谣言传来,就算未来世子夫人不计较,难保舍妹日后的夫家为难!望世子成全!”
车轮缓缓滚过的声音传来,车内容玉看不见外面的情形,却能感觉到一股冰冻三尺之气,可是良久也未曾听到任何声音,许是那祁王世子不再纠缠了,容玉心头长长舒了一口气,耳边只有车轱辘与地面摩擦发出的亘古不变的“哐啷哐啷”之声……
与此同时宫门口的另一辆纯黑色马车上,姬蕴望着那辆容家标志的马车渐行渐远,嘴角微微扬起,视线不经意间与祁王世子转头的目光在半路相汇,两人皆是一顿,良久还是姬蕴微微朝祁王世子一颔首,大手轻轻一甩,墨黑的车窗帘落下,不带一丝犹豫的低沉之音响起:“回府!”车轱辘一动,那亘古不变的“哐啷哐啷”声再次响起在宫门前……
突然听得外面有“得得得”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传来,越来越近,却是朝宫门方向而来,马蹄声急促,很快便清晰地响在耳边。姬蕴正在思忖间,只觉一阵劲风逼近,马车窗帘都被带起了一角,透过那一角,姬蕴看见一位银甲少年骑着一匹全身不染半点杂色的白马掠过,一路狂奔,直入宫门。宫门前的侍卫只是一顿,随即恭敬地散开,立于两边,让开道路,丝毫不曾阻拦。那少年一人一马很快便入了宫门,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里。能如此张狂,打马入未央宫的还能有谁?似乎是为了印证姬蕴心中的猜测,马车外的侍从放低了声音禀告道:“君侯,是霍小爷回京了!”
姬蕴唇角一勾,霍去病回来了,那么卫青也该回长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