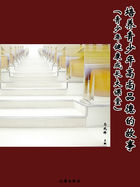怀远坊的一处民宅埙声彻夜回旋婉转,埙声虽及其低沉浑浊,犹如孤魂清唱着,声声引起认得战栗,缠绵着悠悠天地,闻者哀婉而涕下,街坊四邻听出这声音是来至承德王妃旧宅发出的,自从数月之前那里隐约的冒出血腥味,倒也安静了一段时间,只是不知昨夜是人是鬼在那吹曲子,于是众人心里留着疑问相互之间小传小道着。
“小乞儿你昨晚嚎了一夜?”榕城习惯性的摸索着下巴盯着易水涧破掉的嘴唇,“可够深情的,如果那个丫头跟我一样有眼光也就不会出这么多事!”
“嘶”闷声苦笑的动作太大扯到伤口,古一看着对面有些狼狈的人,严重的睡眠不足导致脸色青灰,浓重的黑眼圈以及通红的双眼,倒有些符合小乞儿的外号,好在今天随手带了一个外伤的药膏,“这个你拿去敷伤口。”
易水涧打开盒子边敷边说道:“昨夜你们去了千岁府,说说你们的计划?”
榕城背手在身后边走边说道:“那从暗杀已经打草惊蛇了,秦中宗必然会派更多人的看管牢房,以防有心人得逞,所以我们想着硬闯是不行的只能靠智取,我们打算戍时扮成他们的人先混进去,然后下药迷魂大理寺的看守和犯人,再来一个偷梁换柱趁换班的时候出来,前提是距离换班之前的半个时辰开始行动,时间拖的越长越容易被发现。”
易水涧皱着眉头问道:“那之后呢?出了大理寺怎么出城?”
“九千岁的马车可以自由的出入城门!”
古一瞧的出易水涧对计划的不赞同,“你有什么想法?”易水涧抬头看了对方一眼说道:“倒不是计划不好,其实我已经派人打一条从大理寺到皇宫后山的一条地道…”
“什么?”古一和榕城异口同声的惊讶道,榕城赶紧收起下巴问道:“我知道花楹转移到大理寺也就一个晚上的时间你是怎么做到的?”
“有钱能使鬼推磨没什么是钱办不到的!”易水涧紧握着手里的盒子,“不过还得多亏那个要暗杀花楹的蠢材,如果不是他我还是真没办法,薛叔以前跟我说过当初他们宫变逃出来的地下隧道就发现有一条极其狭窄的路是通向后山的,只是那个路就允许六岁小儿通过,所以之后封路时,那条路也被人忽视了,所以我就照着那条地道通向大理寺。”
古一身子稍微往前一倾问道:“所以你打算怎么做?“
“计划照样进行只是人却是往隧道走,一旦他们何时发现怀疑的对象也只有九千岁的那辆马车,而不会想到其实从一开始我们逃走的方向却是另一个,我们到时就在博山山下碰面,我会在那里备好马车。“
榕城右手放在易水涧的肩膀上重重的捏了一下,“好小子,这招故布疑阵的使得好,事成之后除了我们三人九千岁也不会知道花楹的去处,以防九千岁倒戈到东秦皇帝那!”
“那就这样吧。”计划敲定古一站起身,榕城在易水涧耳边说道:“下午好好养精蓄锐,你这个死样子去见人,小心那丫头又取笑你!”然后哼哼笑着去追古一的身影去了。
易水涧躺在床上根本就睡不着,薛叔死时的样子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听话的指挥着乞丐闹事,站在人群之中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薛叔不让他轻举妄动他只能控制着自己的蠢蠢欲动的双腿,直到看到慕容如愿拿着弓箭出现在他视野里,他明知结果可还是忍不住痛苦的呻吟。
他迅速地抱头蹲下来嘴巴咬在膝盖上,死死的吞咽自己的声音,他此刻的样子没有人怀疑,因为他就像是受到惊吓的普通百姓一样。直到花楹绝望的尖叫和嘶哑的质问,他才从满眼的红色转到那一副摇摇欲坠的人儿上。
他不能去因为他还不能出现,好在九千岁果然守约的护着她,直到看到她上了马车,他撑着膝盖让自己站起身,摇摇晃晃的跟着人流离开,他还有许多事要做,接下来事态的发展让他应接不暇,他根本就睡不着,现在闲下来也是一样。
煎熬的时间何止是今日,只是今日的特别难熬,数日没有女主人的南苑已经冷清的可以寒鸦筑巢了,何况是整个承德王府。男主人双腿复原的消息也冲不破女主人身份给王府带来的阴云,府中上下都愁云满面的担心着锁在南苑一直不出门的人。
容婶在偏厅嘤嘤哭泣,“你个婆娘别再哭了,光哭有用吗!”容叔烦躁地在她面前走来走去,“我哭我的,你走你的,你说小主子日子过得怎么那么苦,难得有几日开心的甚至都要当…”
“闭嘴!”容叔呵斥道,容婶自知自己多嘴气弱哼了一声不说话,只见阴医丞脚步虚晃的走着,低着头像是很认真的看路就差没有把路看穿了,容叔急不可耐的跑出门,拉着人的手正要开口问,阴医丞举起手侧过头有气无力的说道:“你问了我也不能说,你们也别去找王爷,让他一个人静静。”容婶听到此话只好把停下脚步,红着眼睛与容叔对视一眼,除了担心他们能做的再也不多。
“王爷已经允许我出府归家,我告知你们一声。”阴医丞做了揖转身离开。
“医丞你这是...”
“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可还是想着去试试,毕竟…”毕竟什么阴医丞没有接下去说,而是动着嘴巴碎碎念着,原先缓慢的动作机械的加快一些,他此时的样子落在容氏夫妇的眼里,已经引起他们内心的波澜,肯定是要发生什么。
南苑的厨房传出了柴火味,一个高大的身影在里面忙碌着,这道甜点他很小的时候就会了,可惜十来年都不在亲自动手难免有些笨拙,但这不影响他的认真和专注,在这些材料旁边有一个方形的小木盒被随意的放置一边,在这个厨房中显得非常格格不入。
将做成的汤圆下到已经煮沸的热水中,没多久将煮熟的勺到莲花瓷盅,最后撒上一把桂花,热气蒸腾着挂花香扑鼻而来,满意的盖上盖子放在锅里保温着,当他转过身,只见容婶还来不及躲起来的身影,“容婶,帮我备一些碳炉放在食盒里,汤圆凉了就不好吃了。”
容婶楞了一下然后猛得点点头,因为惊喜于连日来自己这个小主子对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爷,这是打算去哪?”明知能够让爷亲自动手的人现下想来也只有身陷囹圄的王妃,可是他一脸平静的样子,这样的话就像是家常一般,自己从小带大的孩子怎么会不了解,越是一副常人的模样越是压制着内心的暗潮汹涌。
“去见你家夫人,说不准今晚她就可以回来了。”
“真…”容婶将惊喜的反问收回嘴里,如果是真的主子不会是这样的语调,她没有再问只是遵命的去拿碳,“爷,老奴这就是拿碳,需要准备轿子吗?”
“马车吧,快一些!”
“是,老奴这就去办。”
容婶提着食盒站在大门内恭敬的等候,听到拐杖在石阶上的嘚嘚声,眼见扫去一身颓废的王爷就算有个碍眼的拐杖却抵不住贵气逼人,就像是离别前的整装待发,多悲伤的词汇,她抖了抖心神,把食盒递过去对方接了过去,“容婶你有空把南苑重新整理一下,或者选一处清幽的郊区别院,整理干净些就好顺便遣散那些下人。”
“爷,这到底是…”容婶不得不问,他要她现在做的这些是何寓意,“你照做就好!”慕容如愿低沉着语调无风无波,容叔暗叹一口气,放下矮凳托着人上马车,在放下车帘前说了平安。
平安对于一般人来说就是个奢望,也只有位于至高无上的人,才能手握权柄掌控别人的生死,所以,对于那个位置的渴望从没有想今天这么强烈,这样他才能护的了他在乎的人,他决不允许再有第二次将自己推入绝境。
蓝花楹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高床软枕之上,甚至桌面上已经摆好吃食,对于生理的需求她下了床走到桌上,端着一盘糕点一边吃着一边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打开房门,一人从天而降,刚睡醒在她没任何防备下,还真的吓得她差点噎到自己,穿着禁卫军服饰的人抱拳道:“皇上有令不准王妃踏出房门一步!”
“咳咳,这是哪?皇上为什么不把我关在大理寺?”这个皇帝怎么突然将她关在类似冷宫一样的地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王妃,这里是无忧宫,其它属下一概不知!”咻的一下人就使轻功上了屋顶。
无忧宫,皇帝打得是什么算盘?难道是为了确保行刑之前的安全还是又突然念及旧恩斩首改为幽禁终身。
呵,现在现在有谁知道她在哪?不管在哪还是自救要紧,依照目前的情况她应该还是没有生命安全的,否者皇帝何必大费周折的换地方。
悠悠半日,蓝花楹在屋子里东摸摸西碰碰、其实不难发现无忧宫中还存在着卓长君的痕迹,梳妆台上的发饰,衣柜中的绢帕,书中夹杂的书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书笺伸向窗外,任由风吹动着它,“唯有以命相之,一世梦魇困兮”堂堂一国之后,竟然用如此极端的手法来换得心上人的痛苦悼念。
卓长君就像黑百合一样,嫉妒是单纯黑化的养料,蒙蔽了她的双眼,什么是爱,怎么去追求爱,从一开始就不平衡的地位就注定着她享受不了一生一世一双人。
痴情人是最情痴,同样是了解自己的生命不顾一切,一个是得偿所愿的上天入地追随所爱,另一个却是不留余地的撕毁假象制造梦魇。
“孩子,就算就我们母子两个,娘一定会陪着你长大,看着你结婚生子或者披上嫁衣嫁于良人。”指尖的书笺在空中旋转着落在雪地上,无忧宫的大门打开,一身紫裘的人影出现在她视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