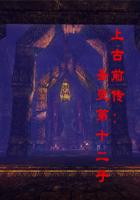一向空阔的花园此时却有了几丝门庭若市。
成千上百宛如黑客帝国般的黑色人影,蝗虫似得从各个角落涌出,这有几分站在教学楼顶上看到的全校跑操的味道。他们的动作谈不上整齐,却胜在数量,这种阵仗纵使国家元首站在这里也会生出几分畏惧,而此时所有人倾巢而出的目的只有一个,逮住那只胆大妄为敢只身闯入野牛群的独狼。
虽然大部分野牛都觉得,不需要对着毫无斗志的独狼太过认真,若是一只狼连撕咬的能力都失去了,又谈何凶残?他只是不断的在防御,躲避,将自己的安全区域越拖越小,没有半分用手枪示威的意思,也不知是不愿伤人,亦或者从开始徐煜就没有半分硬碰硬的想法。
可是男人不这么觉得,那女人教出来的孩子,让他难以轻易忽略,鬼知道他会不会突然发起疯来?自己或许能凭着亲情嚣张跋扈,可面对这群路人甲,就连他也不敢轻易下结论。他很怕,不知究竟是惧怕徐煜,还是他背后那分明已经熄灭但任然留有余温的残烛。
独狼屹然临与众野牛之间,胸腔毫无规律的起伏昭示着他现在早已疲惫不堪,这种连续练习躲避球般,不能反击的情况真是憋屈的要死。
徐煜大口喘息着, 全身重力不住的往下压,双膝弯曲着,这样更加便于下一波的躲避;若是给他一个帮手拖拖时间,他又怎么会这般狼狈。他拍了拍脑袋,早知如此就应该在法陨晨那儿抓两个苦力来的,现在可好,骑虎难下了。
他承认,自己很混账,他能对摔倒的老人不闻不问,也能毫无绅士风度的嘲笑醉倒在路边的小女生,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好人,几乎做遍了世间所有的坏事。但面对这个男人,这个身为自己父亲的男人时,他却无能为力,因为他是父亲啊,是他一生要供奉的人啊。
供奉?为什么会用这个词语呢,习惯?或者,本能?
一个拳头迎面砸来,他躲闪不及,无法克制的后退几步,有点像不自量力挑战拳王的死宅,刚刚上场就被轰得体无完肤。可事实是他已经在这种一波接一波的车轮战中坚持了好几个小时,他其实可以将犬牙交还给父亲,自己老老实实的听从父安排,这样起码可以少受点皮肉之苦。现在这样做有些放肆,他也觉得有些放肆;可他不愿意就这样屈服,于是将内心那顺从的本能生生压下。
他无法承认这被迫的本能,如果他原本就是条听话的狗,那他也要强行的使自己变成狼。如果狼注定要六亲不认,那么他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违抗父亲的命令,那怕这种行为着实荒谬。
很不喜欢,他很不喜欢这些男人的装着,清一色的黑色有着一种送葬的既视感。
连退几步,他又被逼回了包围圈之内,看来这些家伙是要把自己困死在这里啊,自己被捉无所谓,重点是法陨晨好像还没吃饭吧。
他笑笑,真搞不清楚为什么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还能有照顾别人的闲心。
“我的儿啊,乖乖听为父的话不就好了,就像以前一样。”男人终于是率先开口了,在这场心理的拉锯战之中落了下风,可他的语气依旧是硬到不行,他也怕啊,万一打坏了呢?
徐煜的身体微不可察的轻微晃动着,可他仍在笑,他笑他赢了,从这个男人的手里获得了主动权。在这场令人绝望的困兽之斗中,对方越是沉不住气,他的胜算就越大。
不是从这里逃出去的胜算,在男人使用皮卡丘召唤卡呼叫出送葬小伙伴时,他就注定逃不出去了;他说的是,在父子之间的等级上,起码是在徐煜自己的心里,他赢过了自己的父亲,从今往后不再是一个呼之即来唤之即去的傀儡,哪怕他明知道这只是自己安慰自己的借口,却宁愿相信这个粗糙的借口,这样起码在他被抓时不会太难受。
一股前所未有的疲惫感笼罩全身,徐煜无力地蹲在了地上,算了,这种已成定局的事情,不管努力尝试多少次都是徒劳,只是可惜了,没有把母亲从他的身边带走。
要是让法陨晨知道了,一定会气得跳脚吧,好好的一头肥羊就这么跑了,白白损失掉大几百万。想到这里他不由笑了起来,这么说来倒还真想看到他愤怒的样子,只怕是没机会了。
送葬小伙伴们趁着这一会的功夫,迅速的围拢上来,终于把这家伙的体力给磨完了,这可是好几个小时啊,手下的弟兄都不知道换班休息了几趟,这次的车轮战算是他们打得最艰难的一次。他们甚至都有些怀疑,徐煜到底是不是人。
罗铭身着漆黑的西装,发亮的皮鞋落满灰尘,他和其他人一样,都在费力的喘着粗气,他眯起眼睛仔细打量着徐煜。
因为聚众斗殴,警校还没毕业就被开除,还在局子里蹲了两年的他,无可奈何的接受了男人的保镖工作,上任之后才发现,男人要的其实根本不是保镖而是数量惊人的打手,他想过辞职,从小立志保卫人民的梦想竟然屈居于小小的打手,这让他不能忍受,但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这辞职信却一直没有上交。他相信凭借自己能力,哪怕是重考警校,不出三年也能升为真正的人民警察,毕竟他全校的散打记录至今还无人超越。
可如今看到徐煜,让他的自信受到了不小的打击,纵使是他也无法夸下海口说自己能在数百人手下坚持好几个小时。光是这一点,他也对徐煜肃然起敬,同时怀疑起男人的品行。你说对儿子都能下这样狠手的父亲,对待员工又会怎样?
就在这一愣神的功夫,身后的几人便冲在了他前面奔着功劳而去。罗铭也没有再继续的意思,索辛就站在后排。
“你这是静静的看着他们撕逼啊,厌倦了吗?”戏谑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练家子的本能使他顺速的回转头,摆出可攻可防的格斗姿势,但待他看清来人时,一张清秀的脸刷一下红了。黑色的低领毛衣衬得他更加苍白,隐约有一种病态的美感,但这种美感在充满肌肉野牛的地方却显得格格不入,相比之下,他们这些与他穿同色的五大三粗显得格外乡下。
那人笑着,带着几分邪气。
此时他们正处于人群的最后一排,面前拥挤的人潮是密集恐惧症患者的克星。法陨晨拍了拍罗铭的肩膀:“那个啥,帮个忙呗,亲~”
扬声器刺耳的调音响彻全场,十一二岁的男孩坐于广场中心的假山之上,一手高举着高音喇叭,另一只手单手拆卸着子弹,那模样好不惬意。没人看到他是怎样上去的,假山虽然不高,但两三米的高度依然会让一米六的小孩够呛。
“看过来,看过来,我跟你们说哦,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虽然只有三个人。”叶残星漫不经心的说着,像是在与菜场的大妈唠嗑。只是那把明晃晃的左轮手枪格外晃眼。
搞什么啊,恐怖袭击?消防演习?麻烦敌军正规点吧,你那小身板端的起枪吗?
一时间除了徐煜外,所有的人心中都充满的轻蔑与戏谑,‘小孩’在‘大人’面前是翻不起风浪的,这是公理。
叶残星才不管别人的心理活动,朗声道:“很好,就这样继续保持安静,下面有请主持人上场。”
一道道目光游离着,试图寻找所谓主持人的身影,这是观众的自然反应。
“那,那个。”罗铭结结巴巴的发出了几个音节,声音通过广场的扬声器传出。顿时数百道目光齐聚到他的身上,他此时只穿着一件白色衬衫,这在纯黑的野牛群里分外的突兀,将所有人的视线全部聚集到了他一人身上,而忽视了另一道纤细的身影。罗铭讪笑几声,不知应该如何动作,活像个忘词的小丑。
法陨晨压低帽檐,遁入人群之中,如同隐藏杀气的杀手,悄无声息。他在人群中灵活的穿行,却没有一个人能注意到他,就宛如他从来不曾出现过一样。
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幅样子啊,鹤立鸡群的罗铭心里在暗暗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