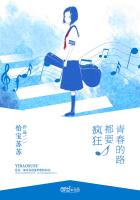可以想象,只要它脑袋轻轻一摇,再厉害的动物也会闻风丧胆。鼻孔像两只粗大的鼓风机,呼哧呼哧地喘息着,强大的气流把朽木上的余火吹得一明一暗。“哎哟我的妈呀!这大家伙,简直就是一辆坦克车!真要扑过来,就咱这破房子……”拖拉机手索二宝打了个寒战。四驴子急忙喊道:“快!快!快把崽子给它送出去!只要它们别过来!”在猪王的两边还有几只特大号的野猪,像犀牛一样。这是一个家族,是生活在小兴安岭密林深处特殊的野猪家族。它们一色的小耳朵,红眼睛,叫声似猪又像牛,低沉,粗犷,凄切而苍凉。
时至今日,我每每闭上眼睛,那头猪王的影子,就与嘉荫县出土的恐龙化石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一群罕见、珍贵的野生动物。是浓烟和烈火阻止了它们前进的脚步,没有老泰山,没有这个老顾问,昨天夜里,后果是真不堪想象啊!此刻,老泰山手拎快枪,像战壕中的一位指挥员,仍然向远外观察着望着……他眼睛红了,仅仅一夜,满头的灰发已经变白了。玉珍还跪在铺上一动不动,我感觉到了内心的疼痛,像撕裂般的疼痛。
太阳的笑脸终于从地平线上升了起来,老泰山回头扫了全体突击队员一眼,然后用洪亮的声音吼道:“都出去,屋里一个人不留,都跟我一块出去……四驴子,你把那个竹筐搬上,把孩子交给它们的妈妈!”说着,一脚把门踢开,率先冲了出去。我把爱妻扶了起来,她的手脚竟是冰凉冰凉的,脑袋依偎在我的胸前,憔悴的面容仍不见血色。玉珍啊玉珍,你的精神负担太重了。别的家庭都是一个人在此,而我们呢?一旦有个闪失,就是全家覆灭了。以烟雾为屏障,以溪流为疆界,全体队员在房子前面一字排开,手拿斧头镰刀,目视着烟雾那边的八戒弟子。待我挽玉珍出来一看,门口所有地皮统统都给野猪翻了一遍。黑土上飘散着猪毛,空气中弥漫着刺鼻子的膻臊味。
四驴子算是有胆量的,手捧竹筐,把小猪崽轻轻地倒在了地上。没等回头,那头老母猪就呼的一声冲了过来,舔舔这只闻闻那只,那份亲密那份疼爱,连高智商的人类都深感自愧不如。母猪用嘴把崽子一只只叼走。没出去十步,就扑通一声躺在那儿,四腿长伸,让孩子们吃起奶来。无忌无虑,幸福安详。老母猪在喂奶,猪王及子孙们仍然是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似乎在耐心地等待着烟火的熄灭,好一声令下,冲上前来。此刻,我的岳父崔永焕出马了,他气宇昂然,一身正气,一手握枪,跨前了两步,对着阵中的猪王,言辞恳切、感情深沉地大声说道:“老人家,请你不要误会,我们来是从事生产,搞成林解放,不是来争夺地盘称雄决斗的。您看明白了吧?昨天的事,是孩子们出于好奇,跟你的晚辈开了个玩笑。既无伤亡也没流血,您大驾光临,亲自出征,到底是为了啥呀?是记前仇,冤冤相报?还是看看我的枪法,跟昔日有没有逊色?我崔永焕不愿意伤你,可也得让你看个清楚,免得后悔而折了你的寿命!”说着,右臂猛地一甩,枪口冲天,“砰”的一声,一只松鸡一头从空中栽了下来,不远不近,不左不右,恰恰栽在了猪王的面前。
“好!太棒了!崔师傅宝刀不老,风采不减当年啊!”“哎哟!不愧是崔炮手!当年剿匪,刘山东子,在半里地之外,就被他从马上打了下来!”人们情绪激昂议论纷纷。我心里猛地一颤。作为全军的特等射手,与岳父相比,功夫技艺真是天壤之别,自愧不如了。我为岳父自豪,也为自己的虚伪而内疚。我舒了一口长气,再看对面,猪王对死鸟置若罔闻,倒是身后几只大猪崽子冲了过来,你抢我夺,松鸡被其中的一只衔住,脑袋一扬就吞了下去。猪王站起来了,四腿迈动,我清楚地看到,它不是雄性的,而是一头雌性的老母猪。松弛的奶子蹭地,步履蹒跚,俨然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太太啦!这是一个母系社会,在兴安岭的大山深处,繁衍栖息着她庞大的野猪家族。早在七世纪初,渤海王国的民族就有象形文字记载,雌性野猪是群体生活,而雄性的则是孤猪。
它们活动范围很广,从外兴安岭的庙屯、库页岛,到黑龙江流域的开库康、十八站,一直到长白山北段的老爷岭,都曾看到过这种野猪的影子。这是一种高智商的动物,其大脑的发育程度跟海豚、猴子、猩猩、大象差不多。伪满时期的《卜奎日报》曾介绍过这种野猪的生活习性:阴险狡猾、刀枪不入、喜袭击外国人,尤其北满林区的日本关东军。当年驻在那一带的北安联队本田肆郎大佐就曾恶狠狠地骂道:“赵尚志的、冯仲云的、野猪的一样、死了死了的!”不知何故,也许像其他珍稀野生动物一样吧,这种野猪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到“文革”后期,仅能在烟筒山、老白山、金顶山、汉冲沟山、摩天岭附近才能看到了。这些山头都在鹤北林业局的管辖之内,而鹤北局,则是共和国最年轻的一家森工企业。大面积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不仅仅野猪,而且也是棕熊黑熊东北虎金钱豹的存身之处和生活乐园。九十年代初期,中央电视台的《人与自然》节目组专门来了一趟,也曾到柳毛河林场做了专访。遗憾的是,别说整个野猪家族的庞大群体,连一只红眼睛小耳朵的野猪都没有见到。
八十年代中期,在野猪岭下,这个家族的集体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是最为壮观完美的一次了吧!果真如此的话,当时的目击人应该是最大的幸运者。这一次我们也成了幸运者,岳父鸣枪击鸟以后,猪王缓缓而动,而前后左右的保驾护航者,都是清一色的雄性野猪。猪王在观察着我们,危险并没有消除,刚才岳父讲了:“我们不是来争夺地盘的……”我心里倏地一亮,命令索二宝:“发动机车,马上返回!”再不返回,就只能是错上加错了。离开石头庙子,猪群自然就会散去。在机车旁边,二宝子忽然失声喊道:“王场长!你快来呀!”我闻声赶去,低头一看,是四驴子拧的那些野猪套子,均被野猪衔到这儿了,然后用牙齿一节节地咬断了。长如筷子,短似火柴,想想昨天晚上嘎吧嘎吧的响声,再看看这些筷子粗细的铁丝线,望着对面的猪群,我再次地感到头皮发奓,后背发凉,根根汗毛都直竖了起来……人都说虎牙尖,狼牙快,豹子牙齿没得赛,而野猪牙……想着,我催促二宝:“发动车,快走!快走!这帮家伙,简直就是一群魔鬼。”拖拉机发动了,启机的声音尖锐高昂响亮,在大山的底谷,像一头猛兽的号叫声在回荡着,猪群毛了,乱窜乱叫,猪王昂起头来,用惊恐的目光望望我们再看看机车。这个怪物,可能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个场面吧!它晃动着脑袋,倒戗着鬃毛,嘴巴子杵地,“哞”的一声吼叫,像拉满了弓的一支快箭,随时随地都能射来。我不由一阵紧张,随手抓起了一把六磅大锤,握在手上,摆好了决战的架式。队员们拉开了距离,老泰山把准星定在了野猪王的眼睛上……金京子“妈呀”一声惊叫,机车的柴油机开始了正常运转。我对三位女性大声喊道:“玉珍、京子、春霞,快进机车里面去!”她们迅速地钻了进去。
拉上铁门,我舒了一口长气。二宝子来了脾气,也许是为了转移野猪们的进攻目标,减轻我们的精神压力,把油门一按到底,挂上了五挡,咬紧牙关掌握着操纵杆,拖拉机突突突地吼叫着。势如破竹横冲直撞,履带扬起了木灰,像一头发疯了的猛兽,奔猪王就扑了过去。
人们乐了,高声喊道:“二宝子!往死里轧,轧死它们!”“对,轧死这些家伙吃肉。看它们再凶!”岳父却竭力劝阻:“二宝子!二宝子!不能伤害它们啊!它们是无辜的哪!又没伤害咱们!”我也帮着岳父喊道:“二宝子,别轧!别轧!”可是已经晚了。猪窝像炸了营,东窜西跳,哞哞地叫着。山林下面像突然被捅了的马蜂窝。猪王别看平时动作迟缓,步履蹒跚,关键时刻还是非常机灵而又敏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