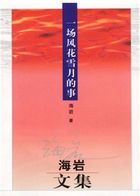他拎着锯老远就喊道:“俺就知道什么事儿没有嘛!在北大荒这么多年,它什么阵势没有遇到过啊!受狼崽子欺负,那还能叫龙驹,大侄子你说对不对啊?”听得出来他喜形于色。“黑龙驹,我的黑龙驹哟!我就知道你没有事嘛!哈哈!哈哈!”他大喊大叫着直奔他的黑马。
刘传海在后面更是赞不绝口:“三国英雄唯有战将吕布,历史上的宝马惟有胯下赤兔。王师傅的黑马实乃是威风!绝无仅有,绝无仅……”第二个“有”字还没吐出口,他就张着大嘴愣住了。在场的人们同时看到,尽管大黑马遍体鳞伤惨不忍睹,可是它依然身姿矫健,鬃毛招展,蓝天白云衬托着它的英姿,两只眼睛黑亮而又精神。
车老板扔掉了刀锯,踉跄着扑上去抱住它的脖子,感慨万千地哭喊道:“心肝宝贝哟!没见你影子可把我给急坏啦!老伙计啊!你真不愧是……”话没有说完,立着的大黑马便轰然倒下了,像大厦倾倒,旋起一股巨大的阴风……大黑马死了,停止了呼吸,但它仍然还站着,它是被狼群给咬死的,也是在激烈的搏斗中累死的。
也许其灵魂就等着它的主人,车老板抚摸时它才轰然倒下。毫无疑问,它就是在等待,等着与主人最后一次告别,等着与主人再见上最后一面。我的全身依然是冰凉,眼前一次次地模糊,阵阵眩晕……巨大的悲痛笼罩着荒野,笼罩着野狼沟这片苍凉的土地。当我们终于克制住了情绪再次注意车老板时,发现他躺在地上早就昏了过去。
“王师傅!王师傅!你醒醒呀!你醒醒呀!”“王师傅,你坚强些,坚强些啊!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是刘传海!刘传海啊!”“快!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毕竟刘传海岁数最大,他跪地把王师傅搀扶起来,轻轻地捶背,车老板的眼睛才一点点睁开,满脸灰土,目光混浊,脸颊深陷。车老板的眼睛忽然间睁大,怒火在目光中骤然燃烧,没等大伙儿反应过来,他就直蹦了起来,踉跄着站住,歇斯底里地指着远处的石砬子骂道:“你们……你们给老子等着……我用炸药把你们全部送上西天!”他的面孔是那么狰狞,脸上的伤疤是那样丑陋。他猛一转身又差点儿栽倒,是刘传海扶着他才勉强站稳。
他的脸色苍白,大口喘气,英雄气概荡然无存,眨眼间就变得那么苍老,那么颓废,似乎一阵大风就能把他刮倒。他喘了几口粗气扭头就走,抓着他的刀锯,两腿打绊趔趄而又踉跄……我突然萌生了能给他惊喜或者一丝安慰的想法,嘴上不禁喊道:“秦、秦、秦世海!”他没有回头,也没有停住脚步,无疑此刻他根本没有听到,其他人也没有察觉,也许以为我喊错他的名字了。
拦不住也不敢拦,刘传海忙问大伙儿:“谁会骑马?得陪着他回去,半路上千万别再出事啊!”出沟就有散养的野马,逮住了就骑,但没有鞍子也没有笼头,没有两下子谁也不敢较量。孙刚把铁铳往二苗子手上一塞:“还是我去吧!”大伙儿默许,我也没再声张。
等着他回来我们再相认,让车老板知道他是我寻找了近20年的父亲。于是我大声地对孙刚喊道:“孙大哥!拜托啦!拜托啦!我李玉珂以后一定重重地谢您!”其他人都感到莫名其妙,只有我自己心里头最清楚,孙刚是代我去护送我的父亲。一切似乎暂时平静了,于是我们剩下的五个人全神贯注地工作,争取早点把勘测任务完成。
经历了血战野狼的那一夜,什么样的恐怖也不再感到害怕,况且我们早做好了各种准备,也摸清了狼群的活动规律。它们白天轻易不会活动,夜晚我们则轮流睡觉,执勤者的任务就是别让篝火灭了,篝火不灭,狼群就不敢肆意前来骚扰。可是我们都牵挂着孙刚与车老板:“该回来啦!百余里地,早该回来了。”“找人难呗!领取炸药得领导批准,边防吃紧,领导也不会轻易地就批啊!睡觉,睡觉,别想那么多啦!你扛着设备一个劲儿傻跑,明天说啥得把直角对上。其余的工作咱们回场部再弄,眼下关键是别留下缺口,再回来返工那可就惨啦!”我没有心情和他们聊天、议论,我在思索,狼群是不是真的认输了?
虽然我们用篝火来防范,但这儿毕竟是野狼的窝啊!记得出发前场长就说过,北大荒各农场连年开发,狼群被迫往沟内集中,这儿是野狼最后的一道防线,是它们的根据地,是大本营。大本营、根据地,围攻了半宿就做出了让步,尤其是那四五只白色老狼的目光、神态,没有丁点儿认输的迹象。老奸巨滑的它们肯定还会反扑,可是为什么就再没踪影了呢?难道依然在调兵遣将?还是在酝酿更残酷的阴谋?第二天很快就过去了,还是没见人影,我们大伙儿都沉不住气了:“不对劲呀!早该回来了!别说是领炸药,就是回去制造也造出来啦!不行,明天一早咱们得出去看看,我总觉着这里面有事。”刘传海的疑惑代表了大家。
第三天一大早我们就往沟口奔去,拐了两个山包,离沟口不远,眼前一幕又让我们大吃一惊:四堆骨头白花花的,很容易辨别,两个大堆儿是马的骨头,两小堆儿显然是孙刚和车老板的。大伙儿目瞪口呆,突然间都傻了,也都懵了,大张着嘴巴欲哭无泪,全身发僵,很长时间才哭出声来。我觉着全身冻僵般的寒冷,一根根的头发全立了起来:“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刘传海第一个喃喃地说道。“啊!明白啦!明白啦!”二苗子蹲下又站了起来,指着沾满了露水的蜘蛛网:“肯定是前天的傍晚时分,狼群在这儿埋伏重兵,它们也学会了围城打援,狡猾的狼群!”我察看了地形,也认为这里突然袭击最容易得手,离大道很近,人们的警惕性不高,略一麻痹狼群就能得逞。而且也确实布下了重兵,从四堆骨头上就可以判断,人没有反击,马匹没有逃窜,狼群应该像泰山压顶般突袭,眨眼间就解决了战斗。
人的骨头大部分嚼碎,马骨头上的肉丝还有不少剩余。很快我们发现了炸药,离骨头很远,被灌木丛托着,肯定是车老板经验丰富,坐在马背上,见事不好就把炸药包给抛了,否则不可能甩出那么远。我们也找到了车老板的刀锯,木质的锯把被啃得精光,锯板上也留下了很杂乱的牙印,看出来狼群是多么痛恨,如果能吞咽可能早被它们吃了。即便在这极度痛苦、悲愤的情绪中,我脑海中仍闪现出作为父亲应该有的那枚勋章,可是周围除了他们俩衣物的碎片,没有他物。我的心情矛盾之余早已被仇恨拧得生疼。
我们拿着炸药,在山顶上找到了那条直通老巢——烟筒山石砬子的小路,石砬子是周边最高的山峰,怪石嶙峋,气势磅礴,岩石缝内有数不清的穴洞,悬崖下面有一处深潭,据说是梧桐河的源头,据说这深潭与天池相连……蜿蜒的小路在林荫下穿过,树干、树枝、野玫瑰、榛柴及桦树条子上面,到处都沾满灰褐色的狼毛,还有一堆堆风干后的狼粪,野猪骨头,马鹿骨头和家畜骨头等等,看出来这儿是它们的据点,它们经常在这儿作案。看着刀锯,看着那包炸药,想想可能是父亲的残缺肢体,我的喉咙有点儿堵,眼睛也一次次被泪水模糊……仇恨和悲痛在内心汇聚,满腔怒火再也无法忍受。
眼下,炸毁狼窝,炸死狼群,就是我们的最高使命,我们要为车老板报仇,为孙刚报仇,为马匹报仇,为眼前的累累白骨报仇。我们俨然就是刽子手,用我们手中的炸药去行刑,不需要审判,不,是在我们的心中已经审判千万次,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马上执行。点燃了导火索,我们仍在咬牙!“轰隆”,震耳欲聋,地动山摇。
碎石和小树飞上了天,随后就是无尽的惨叫声。“妈的,看你们还能在这儿待多久!不行明天再来一包大的,把整座石砬子都给炸平。奶奶的,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上午我们引爆了炸药,可是直到傍晚,夕阳下我们才看到,沿着那条起伏的山脊,狼群终于开始撤退了,足足有上千只野狼,单列长队,动作缓慢,不停地哀叫,不断地回头,看出来它们是那么留恋。霞光四射,大地被染红,目睹灰狼,我还有些疑惑。撤离的队伍中怎么没有那几只白狼呢?难道它们被炸药给炸死了?还是已经提前逃走?正有点茫然,突然就听孙磕巴喊道:“你们快、快、快看哪!白狼出、出来啦!”沿着他的手指我清楚地看到,金光刺眼的霞光下面,六只白狼齐刷刷地站着,是那样高贵,高贵得简直有点儿神圣。
六只白狼面冲着我们,表情和目光是那样的悲哀和忧虑。它们在作揖,在嗥叫,叫声婉转而不是刺耳,我们愕然,可没等反应过来,六只白狼就跃入了深潭。刘传海号啕,其他人也哭了。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人狼大战早已深深埋进我的思绪深处,我不愿提及,我不想争论谁是最后的胜利者。
可是,当年的北大荒在大批知识青年挥洒汗水、奉献青春下,早已旧貌换新颜,成为祖国的大粮仓;当年的烟筒山石砬子也因其险峻、景色秀丽,被政府开发为旅游景区,每年都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大批游客来此观光、探险。当然,我的寻父之路也从未间断过,先后找到过很多组织部门和当年的老兵了解情况,有的说父亲回国后时间不长,就因伤情恶化,离开了我们,要是能早点接受系统治疗,保住性命应该没什么问题;有的说父亲伤好后,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想母亲为自己伤心,于是请求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一个边远的连队工作,在一次与狼群的遭遇中为保护战友的生命安全,引开狼群,可是后来战友们再去寻找,却并没有发现父亲的踪迹,只是找到一枚被狼群咬过的严重变形的银质的类似勋章一类的东西;有的说……不管怎么说,我坚信父亲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我坚信他还活着,他也一直在苦苦地寻找着母亲和我,也一定无数次梦回新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