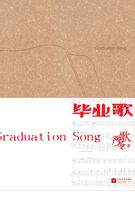我想着心事,再加上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不敢有一点疏忽,努力睁着疲乏的双眼。自从进狼窝的路上那三鞭子响过,一个不愿意承认的父亲形象便若隐若现地清晰起来了。此刻我的母亲又在脑海里出现,还有母亲讲了多少遍的故事,这些故事曾经让她自豪,其中就有父亲驯马的故事,三鞭子就降住了三匹烈马,当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在不断地回忆母亲的讲述,父亲的形象越来越让我渴望,可车老板除了那三鞭子,怎么也看不出当年能让母亲动情的风采来。我辗转反侧,脑袋发胀,眼珠生涩,就是没有睡意,隐约听到狼嗥声由远及近,像千万个婴儿同时在啼哭,听上去让人凄切而又绝望。
我赶忙起身推车老板:“快!快!都快起来!你们听听,这么多狼啊!这么多……”我全身颤抖,汗毛直竖,四肢仿佛是失去了知觉,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动静。尽管我思想上早有准备,但事到临头,除了大脑一片空白,手脚也冰凉冰凉。外面的马匹也惊恐得乱叫,蹄子刨地,扑通扑通山响……狼嗥马嘶,地动山摇,夜色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凄厉的嗥声像洪水般地扑来。野狼的利齿要把世界嚼碎,我们的木屋已变成了孤岛。
“都准备好了,王八蛋,不怕死你们就来吧!”孙刚在黑暗中切齿地叫骂,他有铁铳,慌乱之中当然就他胆大。其他队员也准备了武器,斧头、镰刀、切菜刀及铁棍。我用的是铁矛,铁矛把近两米长,用涩木制成,这种材质出自完达山的阴坡,像铁棍般坠手,却有一定的弹性,既能当棍子横扫狼腿,矛头锋利又能刺它们咽喉,黑暗中充斥着紧张和混乱。越是恐惧,孙磕巴的舌头越是不闲着:“剁、剁、剁爪子!砍、砍、砍脑袋!妈、妈的,豁、豁出来、来啦!今儿个不、不是鱼死,就是网、网、网破啦!”他提着斧头,是伐木场上用的开山板斧,只见他“咔嚓”就是一斧子,狼爪子不知道剁着了没有,房顶上的灰尘却全落了下来。于明新拿着撬石头用的钢钎,不声不响一个劲儿狠捅。他也是我们队上的元老,但身体瘦弱,说话声像蚊子,个头儿倒不矮,外号叫螳螂。
此刻二苗子正在对他大吼:“去!别在这儿碍事,就你这身板儿,凑什么热闹!”黑暗中刘传海也紧张地说道:“大、大敌当头,精诚团结,可不能内讧呀!我说二苗子。我的妈呀,听见了没有,上房顶啦!上房顶啦!”他握着把菜刀,但不敢出手,只是在地上转圈儿喊叫。车老板没动,仍在炕上坐着,像没事儿一样,黑暗中不清楚他到底在想啥。狼群从进攻就没有遇到阻力,看出来它们也特别谨慎。只是嗥叫,好像在恐吓,似乎想用恐吓的方式把我们给吓退!正在我揣摩狼群的动机和车老板的想法时,孙刚的铁铳咕咚就响了,火光非常刺眼,震耳的轰鸣声还没有彻底消失,正前方就传来哭泣般的哀叫:“哇欧……哇欧……哇欧……”与其他的叫声不同,毫无疑问,有野狼被击中:“打中啦!打中啦!”二苗子手舞足蹈。孙刚在黑暗中洋洋得意:“王八蛋,不怕死的,你们就来吧!老子带了一兜子弹药呢!”没等他说完,车老板忽地站在了地上,亮着嗓门气愤地骂道:“谁让你开枪的!啊!你找死啊!小兔崽子!”听口气,车老板已经火冒三丈了,简直要吃人,“你把大伙儿都给毁啦!这儿是狼窝!你怎么瞎整呢!哎!把那块破铁快给我扔了!显摆什么啊!进沟你就瞎摆弄,别人没见过枪啊!”毕竟都是成年人,车老板的怒骂很难让人接受,尽管眼下是特殊的环境,但就是骂儿女也得讲点儿方式啊!况且两人相识才仅仅半天。
也许车老板意识到了什么,他口气缓和,似乎有点抱歉,用责备的口气继续说道:“你不懂!这一枪可就惹下大祸喽,场部为啥不给咱们发枪?仅仅是大鼻子要闹事吗?不对!枪械库的破枪有的是,为什么不给?是人家场长比你们懂,你们不傻就不会想想,是咱们进来占人家的地盘,狼窝狼窝,这是狼的家啊!人家能心甘情愿吗?当然会反抗,兔子急了张嘴还咬人呢!总得让人家闹哄几天吧!闹哄几天自然就走啦!老老少少的,搬家也不易啊!这也是故上,故土难离啊!唉!这一枪打的,就结下仇喽!不信你们用电棒照照,打死的老狼肯定被它们同伙给吃啦!紧接着就是复仇了。你啊!你啊!你开枪的时候咋就不考虑考虑呢?也多少考虑考虑后果,我死了不要紧,土埋脖子啦!可是你们呢?你们六个人呢?你们……”没等车老板说完,二苗子就触电般地惊呼:“爪子进来啦!爪子进来啦!”喊着叫着用砍柴的大镰刀就是一阵子猛剁,随着一股刺鼻的腥味,一只老狼惨叫着逃走。
偷袭的狼群也逃走了。霎那间,室内又恢复了宁静。我仿佛听见了自己的心跳,此刻大伙儿都屏住了呼吸,忐忑不安,听着外面的动静,夜幕下马儿们也没有了声音。又一阵紧张袭上了心头,那几匹马怎么样了?尤其是那匹黑色的大辕马,真被狼吃掉该是多么痛心啊?我用手电筒从窗户的缝隙中向外面照射,刚一照就心惊肉跳,不由得冷汗又涌了出来,屏住呼吸照亮了再看,孙刚和孙磕巴也凑了过来,我们三人同时看到,绿幽幽的眼睛到处都在晃动,漫山遍野,简直像鬼火在草丛中跳跃。
近处有七八只硕大的灰狼,正在啃嚼着同类的尸体,狼毛飞舞,污血遍地。见到电光它们也一愣,但没有一只惊慌失措,更没有逃跑或躲藏的迹象。而是大义凛然仇视地盯着,那阴森恐怖又狰狞的目光,让人不寒而栗!又听孙刚喊道:“快看,白桦树下面。”经他提醒我才注意到了远处,一棵粗大又茂盛的白桦树下面,四五只白狼正注视着这里。夜色漆黑,杂草还是绿的,尽管树叶有点儿泛黄,但白色的老狼是那么醒目,白得刺眼,也更让人恐怖。毫无疑问,它们是狼群的首领,是今天的主谋,是现场指挥,庞大的狼群均服从其调遣。此刻它们仿佛正在研究,所以周围也就出奇地安静……我想起来了,想起了挠力河西岸,白狼劫子逼走垦荒连队的故事,更想起了它们的智慧,它们的容忍和克制,今天我亲眼目睹了白狼,面对这么强大的对手,也真真切切感到冷风刺骨。
事实正如同车老板所讲,围攻是想把我们逼走,可是孙刚突然打死一条灰狼,战场上的性质可就彻底变了。这几只白狼正在咬耳朵研究,看来残忍的报复马上就要开始了。手电筒刚灭,随着一声嗥叫,狼群就如同决了堤的洪水,夹风裹雨,扑面涌来。野狼群的第二次进攻,可以说来势凶猛,嗥叫声震耳欲聋,我们龟缩在室内,也趁机仔细打量木屋是否有易被攻破的隐患。靠地面的圆木已经腐烂,木头缝里的黄泥也早已经脱落,如果常住,别说是猛兽,就是夜晚的蚊子也够人受的。门板窗户也在风雨中腐朽,难以抵挡野狼不间断的啃咬。这次它们是扇形地扑来,爪子挠、牙齿啃,屋顶上的狼群想把房顶揭开。四面受敌,我们也只好各自分工,各坚守岗位,相互协作,拼了命自卫。
我使用的铁矛得心应手,木头的缝隙刚好发挥作用。黑暗之中我猛地刺去,一只老狼被刺个正着,“哇”的一声就逃之夭夭。但圆木太粗,野狼个儿又太矮,刺在腿上往往不起作用。正当我第三次又命中了目标,可刺出去的矛头却怎么也拽不回来,被老狼给衔住,而且很可能还不止一只,我拧了两圈竟然没有拽动。狼的牙齿嘎巴嘎巴作响,但我的矛头就是拽不回来。双方像拔河,匆忙中我大叫:“毁啦!毁啦!我的扎枪被咬住了,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我有些绝望,但还不敢松手。野狼们的力气非常大,也可能是数只一齐跟我较劲。
其他的伙伴早已顾不上我了。镰刀、斧头、大菜刀,奶奶的,整个室内混乱成了一团。有人狂呼,有人怒骂,木屋摇晃,灰尘落地。外面的嗥叫声有增无减,刺鼻的血腥味在黑暗中弥漫。不少野狼被伙伴们击中,或爪子被剁,或脑袋被击伤,“哇哇”哀号着躲到了一边,逃向了远处,但其他的灰狼迅速又补充上来。攻势不减,而且更为疯狂,百分之百的亡命之徒,死亡早被它们置之度外。
狡猾的狼群在凶猛地冲撞,几只或十几只,用它们的肉体,使腐朽的槽木吱吱作响。刀斧根本就发挥不了作用,眼瞅着堡垒就要被它们攻破。就在我们惊慌失措的紧急关头,车老板突然连打了几声口哨,伴随着刺耳的口哨声响起,马匹也挣断了缰绳,“扑通扑通”往远处跑去,马匹突然间远去,围攻的狼群也忽然间松懈。我乘机把铁矛硬拽了回来,思想上也忽闪出个念头:狼群为什么没有进攻马匹?难道残忍的野狼对黑马也打怵?车老板是想让马匹把野狼吸引走?但时间不长,狼群仿佛意识到了什么,调头反扑,继续决战。它们似乎探到了我们的实底,不再有疑惑,想要把我们吞掉。
孙刚哭了,也许是悔恨自己过失导致了这场灭顶灾难,也许是被恐怖的态势吓得无力再自卫,扔下武器听天由命了。男子汉的哭声感染力很大,听他哭泣我心里也有点酸酸的。从朝鲜来到中国的狼窝里送死,母亲白养活我一场……意志软弱、临阵哭号无疑是战场上的大忌。车老板急了,黑暗中骂道:“哭丧啥?日你祖宗的!”一嗓子吼完,孙刚的呜呜声戛然而止。接着车老板愤怒地喊道:“点上蜡烛,都给我听着,谁当孬种,我他妈的对他不客气!”我丢下长矛抖着手去点蜡烛,划一根火灭了,再划一根又灭了,费了好大劲才把蜡烛点着。随着火光一次次地闪动,外面的进攻也略微有点儿收敛,狼嗥声也突然消失了。我心头一喜,感情它们都这么怕火啊!“早不点灯。”二苗子说道,“早点上蜡烛……”看着车老板,他的话没有说完,就惶恐不安地硬憋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