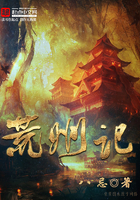而蜜蜂呢,昼夜不停地辛勤奔忙,从蜜源到蜂场的路上,嗡嗡飞着,“叭叽”一声,从空中栽了下来,特别是箱子跟前,一夜之间,就有千万只蜜蜂累死在那儿,黄糊糊的一片。看后,是令人非常悲壮而又痛心的。老叔就难过中多次感叹着说道:“唉!咱们养蜂人哪!不管到任何时候,都得跟蜜蜂一样,在这个社会上,勤恳、诚实、厚道,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对国家、对民族都得忠贞不渝,要不,就不配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就不配跟蜜蜂们在一起……斌子哪,老叔我说得对不对啊?”老叔在正规学校没念过几天书,但他记性特好,人又勤奋,一旦填饱肚子,空余下来,除了钻研养蜂学,并自费订了一份《蜜蜂》杂志,还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名著,像岳飞,杨家将、呼家将,信口就能随便给我讲上一段,而且还不影响干活。自古以来的“忠孝”二宇,始终是牢牢地扎根于他的精神世界。所以,蜂场黑黑的木屋中,各种奖状和荣誉证书,在粗糙的墙壁上,也早就贴得满满的。清凉爽口甜甜的椴树蜂蜜,不仅男女老少都喜爱,蜜林中的野生动物也是一有机会就来划拉一把,狐狸、黄鼠狼子、野白鼠尤其是死皮赖脸的狗熊,敢冒风险还贪吃不要命。
尽管三只猎犬恪尽职守或戒备森严,每年夏天、搅蜜期间,蜂场都要遭受它们的袭击和蹂躏。特别是石砬子背后的那只大棕熊,明目张胆,仗势欺人,大巴掌抡开,压根就不把三条猎犬当回事,连吃带糟蹋,直恨得我和老叔牙根儿生疼。
一天傍晚时分,三只猎犬突然一齐狂叫:“汪汪汪!汪汪汪!……”“老叔!又是那只黑瞎子吧?”我紧张而又恐惧地问道;老叔没有吱声,铁青着脸,目光死死地盯着窗外,不宜出去,也不敢出去。窗外林涛疯狂般的怒吼着,猎犬声响成了一个蛋。听声音,冲上去又退了下来,退下来又冲了上去。愤怒、狂暴、忍无可忍,地动山摇般……老叔气愤地全身抖动抓在手上的猎枪,犹豫再三,又轻轻地放了下来。“给它一枪呗!”焦急中我轻轻地说道。“不行!”老叔抑制着怒火缓缓地说道,“你不懂啊!”顿了顿,老叔又说道:“这家伙,全身都是厚厚的松树油子,又沾了一层沙土,子弹根本就钻不进去。反而引起了它的愤怒。
蜂箱也全都毁啦!”“那就没办法了?”我感到寒冷、恐惧、悲哀、绝望。在强暴面前,人类是那么无能渺小、儒弱和无可奈何。“有!”黑暗中,老叔肯定地说道,“狗熊和孤猪一样,只有咽喉和它们的腹部,才是它们的致命之处。盲目出击,效果不大,反而后患无穷啊!”突然,门外传来了大黑的惨叫声:“哎哟!哎哟!”夹杂着蜂箱被摔碎了的劈叭声。想到蜂子的死亡和蜂场的损失,我心里头像揪着一样,既疼痛难忍,又怒不可遏。“杂种,你等着!”我全身颤抖,咬牙切齿地骂道。吃饱也斩腾够了,狗熊才扬长而去。
我用电棒一照,光束中,那家伙是那么盛气凌人而大摇大摆,并漫不经心、得意洋洋地,傲慢而又狂妄地回过头来,用绿荧荧的小眼睛、嘲讽般地望了我们一眼再看大黑,膀子上被挨了一巴掌,败下阵来而毒气没出,目光红红的,像两块燃烧着炭火,羞耻和污辱,使它全身上下都在剧烈地哆嗦着。长毛和小六子,一声不响,目无表情而又怅然若失,紧紧地夹着尾巴,除了哀嚎再无别的能耐。我知道,大黑的报复心特强,今天受了欺负,以后,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场破釜沉舟的恶战,也许,很快就会爆发出来。
对大黑的性格,我是再熟悉不过了。像疆场上的烈士,残杀中只有站着去死,而绝对不会躺下去生。否则,也就不是它大黑了。蜂子死了一地,蜂箱破碎,蜂坯被扔抛得漫山遍野,粘粘的蜂蜜也在草地上流淌着。老叔气得脸色煞白,胡子抖动,但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冷静中咬着牙根说道:“斌子呀!你看家,我到山上转转!这家伙赖得很哩,不给它点厉害瞧瞧,过两天,犯了瘾,它是肯定还要来的。”老叔说完,挂上了子弹袋和饭包,一手拎枪一手拎着刀子,没走多远,大黑就跟了上去,前腿还有点儿一瘸一拐的。我急忙喊道,“大黑,回来!带伤参战,不是干吃亏吗!”大黑回头望了我一眼,摇摇尾巴又固执地跟了上去。“让它去吧!”老叔理解地说道,“毒气没出,它在家中也待不消停!”老叔领大黑奔到了大砬子背后,也是鹤岗与嘉荫县的接壤地带。
可恶的狗熊,是应该把它处死了,否则,对蜂场,永远都是个可怕的隐患……天,很快就黑了下来,老叔还不回来,大黑又不在家,蜂场死气沉沉,只有周围的松涛一个劲儿响着。我心中烦躁,就出来走走,围着蜂箱。一天没有搅蜜,蜜蜂们也仍然在工作着。原来,没有进山之前,印象中,蜂蜜是靠蜜蜂酿出来的,但事实并不是那么回事,而是各种植物的开花期,花蕊中自然就有甜蜜流了出来,像椴树、苕条、槐树、油菜、枣树等等。是工蜂直接去把蜜采来,吐在了坯子上,预备越冬食用。坯子搅了,巢穴空了,蜜蜂就得继续再来。蜜蜂没有思想,若不把蜜及时搅出,巢穴已满,它们也就趴在那儿,懒得再出去动弹了。
蜂巢内也是一个美妙而又严肃的社会,分工不同,各负其责。蜂王甩籽,雄蜂交配,工蜂群内除了极少部份负责警戒,伺候王子,打扫卫生,绝大部份都得外出采蜜的。我仔细观察过:它们的惩罚制度很严,若有个别工蜂偷懒懈怠,蜂王就会毫不客气地把它来置于死地,咬死以后,由其它工蜂把尸体清出箱。
天色黑透,星星眨着眼睛,群山像一只只庞大的猛兽,蹲卧在那儿,黑黝黝的,看上去令人觉着毛骨悚然,一阵阵地焦虑不安。出去整整一天,老叔也该回来了呀!万一……我不敢再想下去了。与野牲口打交道,枪杆儿再直,也有失手的啊!我烦躁,又不能呼喊,点上油灯,借着窗子射出来的亮光,我躺在外面灯影的暗处:左手捏着电棒,右手握着棒子,耳朵紧张地竖了起来,仔细地观察着周围,心里略微感到一些失落。老叔再不回来,没枪没狗,死活我是不敢进屋睡觉的。
老虎、金钱豹、野猪、狗熊、豺狼、在暗念中,像走马灯似的,不停地晃动了起来……这大山深处,四十里地周围,仅仅就这一个木屋,我真若被豹子咬死,老鹰和乌鸦把皮肉啄光,成群的豺狼,会把我的骨头也嚼得丁点儿不剩。突然,一个毛茸茸的动物猛地出现在我面前。“妈呀”一声,我险些晕了过去。
揿亮电棒一晃,原来是大黑返了回来。“哎呀!你,可把我吓死了!”我嗔怪地说道,“咋不吱个声哪!死玩意,老叔呢?”大黑无语,晃动着尾巴,亲昵地在我身上吻舔着。一个阴影,蓦然笼罩了我的心头:一个不祥的念头,老叔出事了,大黑回来送信儿;再看大黑,尽管急切,目光中却没有悲哀和凄凉,反而有点儿惊喜和兴奋,我悬起来的心,又悄悄按了下去。站起身,随狗朝石垃子方向摸去,没出多远,就迎上了老叔,老叔大汗淋漓,呼哧带喘,让我更感到吃惊的是,他背回一个人来,而且还是个女人。“哎呀!老叔!可把我急死了,咋回事呢?”“进屋再说!进屋再说!”疲倦中老叔得意地说道。长毛和小六子也一齐跟了回来。进屋撂在炕上,借着昏暗的灯光,我清楚地看到:女人有三十多岁,身材苗条,面容清秀,披头散发,一身工装沾染着点点的血渍。她呼吸正常,眼睛微闭,尽管没有发现伤痕,但苍白的脸色却告诉我:她受了创伤和惊吓,目前仍处于昏迷状态之中。
看衣着打扮和面容肤色,她肯定也是山里人,但绝对不是那种经常跑山的劳动妇女,像科室人员或学校老师,又似乎是生活比较滋润的那种家庭主妇。“老叔,她是谁?咋的了?”我疑惑地问道。老叔饿极了,嚼着馒头,仍然气喘吁吁地说道:“她是谁?我怎么知道?咋的?被那只棕熊扑倒后吓的呗。就差一步,再晚去一步,哼!这事,今天,还得说多亏大黑呢!”原来,中午时分,在石砬子那边,犬们嘶咬。而且声音极不寻常,老叔提枪冲了过去,透过枝叶,他恍惚看到,又是那头棕熊。正在追赶一位捡山的妇女,妇女拼命地喊着:“救命啊!救命啊!”情况相当危急,老叔毫不迟疑,抬手就开了一枪:“咚——”枪声在山谷中回荡,奋不顾身的大黑,随着也就扑了上去。狗熊一愣,显然是没有击中要害,扔下女人,挣脱大黑的纠缠,就直奔老叔扑了过来。老叔有多年的狩猎经验,迅速跳到了一棵大桦树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