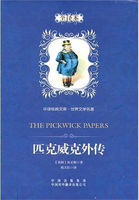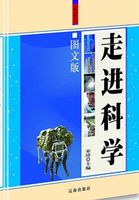老叔是养蜂专业户,在小兴安岭的夹皮沟林场,提到我的老叔——夏大禹,自然就想到他的“雪花牌”蜂蜜。作为小兴安岭的拳头产品,它早在十五年以前,就漂洋过海,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在为国家换来大把大把外汇的同时,老叔也一度走红,广播、电视、报纸,一个照片接着一个照片,一个镜头连着一个镜头,那天晚上看电视,黑龙江台,当老叔一脸憨笑又在镜头上出现时,妻子突发奇想不无揶揄地对我说道:“哎!夏斌,你那些叔叔姑姑,一个个都长得球球蛋蛋的,唯独你老叔,人高马大,还是一脸络腮胡子,你奶奶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不正经呀?”“放屁,你奶奶才不正经呢!”拿租宗开涮,我一听就炸了肺管子:“什么东西,作为晚辈,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妻子也不示弱:“哎,你急啥呀!看看哪!那不是你七叔,也在电视上嘣哒呢!猴子和狗熊在一起,他们能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芝麻杆上挑个大茄子,不串种,谁信呀?”妻子理直气壮,我“啪”的一声关闭了电视,把没抽完的烟头,狠狠地扔在了地板上,用脚一拧。
在平时,妻早炸了,不骂我个狗血喷头,让我跪在那儿用舌头舔起来是绝对不算完的。今天,大概是看出了苗头,兔子急了也咬人,好汉不吃眼前亏,眼珠子瞪得比鸡蛋还大,最终却知趣地连一个扁屁也没放出来。她拽了一把儿子:“冬冬!睡觉去。有本事你把房子点了火,人模狗样的,德性!”门一摔,自己进卧室去了。
妻子离开了。15岁中学生儿子尽管闻到了火药味,但仍然是天真的问道:“爸,妈妈不问,我也有点儿怀疑,我八爷爷,真的是我老奶奶生的吗?达尔文的进化论我都读完了,我五爷、六爷、七爷和你差不多,都是小矮个小白脸,唯独我八爷……就是进化,也不能进化得那么快呀?”我本来想呵斥他一顿,小孩子,你懂个啥?但转念一想,不行,儿子毕竟是中学生了,再说,他也有这个权力,作为父亲,必须正确对待,严肃回答。否则,儿子同样也不买我账的。于是,我郑重其事地答道:“冬冬,你看过杨家将那本书了吗?”不等儿子回答,我又继续说道:“杨家将中的杨八郎也不是佘太君的儿子,而是义子,当初你老奶奶呀,也是为了图个吉利,才从河东平度地,给你抱回了这个八爷。你八爷爷真正的母亲是谁,父亲又在哪儿?爸爸当然是不清楚了!你八爷爷虽然也是姓夏,却不是一个血统,这回,你明白了吧!”“噢!是老奶奶的干儿子呀?”冬冬更加天真地说道,“佘太君跟大宋皇帝平起平坐,这么说,我老奶奶也时常地进出皇宫了?”“得得得!你的想象力倒是不错,睡觉去吧!睡觉去吧!你们母子呀,纯粹都是精神病!”冬冬扮了个鬼脸,一脸迷茫地噘着嘴出去了。
不久,我就收到了老叔的一封信,是别人代笔,字写得老大,还伸胳膊踢腿的,几十个字,就划拉满了一大张稿纸,内容更是叫人既骇然又疑惑。“夏斌侄儿,见信速来,我重病在身,阎王爷把路费钱都给我寄来了!蜂场咋办?别人,我相信不着,这件事情,就只能依靠你了!”老叔和我,尽管是在一个林业局,但两个林场的方向不同,从庆丰到夹皮沟,区区百十里地,中途换车,还得住上一宿,那个别扭劲,真比出国还要麻烦。关键是通讯设备滞后,早先用五十年代的摇把子电话,自从各林场统一配备了对讲机以后,一百多里长的电话线,就被下岗职工一节骨一节骨地掐断,做了狍子套。
大事小情,彼此之间就靠对讲机来沟通联系,一家有事,全局知道。于沟河林场是全局新鲜事最多的一个单位,防火大队长与瞭望台的防火员对讲,通过电波,都清清楚楚,一个字不少传到了副市长兼防火总指挥的耳朵里:“狗剩子他爸!你快下来呀!”“咋啦!啥事呢?”“还啥事呢,人命关天,你老婆喝耗子药了!扯鸡巴蛋,没事闲的,搞破鞋玩,都搞出人命来了,你还在金顶山上拿稳的呢?”“她跟谁?”市长气哼哼地听着。“还有谁?你们家邻居五大巴掌呗!当王八有酒喝,你在山顶上是不是喝晕过去了!……”市长大发雷霆,从此局党委下了文件:对讲机为防火专用工具,非工作情况,一律不得使用!读完信,打了个招呼,我就匆匆下山了,坐在车上,边走边想着老叔的话,蜂场咋办?别人,我相信不着。“别人”?又是针对谁呢?针对老婶?和她那三个孩子?
半路夫妻,自然是靠不住了!春节我去串门,老叔就气哼哼地说道:“这么个娘们,活不干,一天到晚练什么功……走火入魔,我去街里两天,就给练死了十多箱蜂子,还搭上了一缸蜂蜜!败家玩艺,快把我气死了,我咋就找了这么个玩意呢!唉!当初……真不该救她的命呵……”关于老婶的为人、品德,我是再清楚不过了。没有老叔那一枪和大黑的奋不顾身,即使是有十个老婶,也早变成黑瞎子的粪便了……但练功为什么能练死蜂子,我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于是就问:“练功咋能练死蜂子呢?”“练功练晕了头,仓房门四敞大开,舀完蜂蜜忘了扣盖,你想想,蜂子能不涌进去?能不淹死?我日他个祖奶奶的,白瞎了,一缸椴树蜜,十多箱蜂子啊!”老叔忿忿地说道。
唉!可也是!我不能妄加评论,只能安慰老叔:“算了算了,破财免灾!况且又不是故意的,谁还没有失手的时候?”没来山里之前,我就听说了,七叔是连级干部转业,分到夹皮沟任主管后勤的副场长。官,虽然不大,“文革”期间也照样挂了大牌子,在批头会上,造反派头头邹法财故意把老叔也拽上了台子,并厉声喝道:“夏大禹,过来陪着,说你们哥俩到底是不是一个爹的!破……”“破”字刚刚出口,老叔铁青着脸就蹿了过去,半截黑塔一般,邹法财见事不好,想逃走吧,又怕丢了面子,只好梗着脖子,瘦驴屙硬屎般地大声吼道:“你你你……你想干啥?”“干啥?”老叔嘿嘿地笑着,“你不是想上天吗,今天,我就让你坐坐这个土飞机!”说着,一伸手,就像老鹰抓小鸡似的,轻轻一提,就把邹法财拎了起来,邹法财两脚悬着,在空中哇哇大叫,挣扎威胁又是告饶。老叔膀子一晃,像掷铁饼似的,悠了半个圆圈,“嗖”的一声,就抛了出去。
“跟老子装屁,去你妈的!”邹法财面如土色,哇哇叫着,掠过众人的头顶,就砸在了地上。多亏那儿有一堆锯沫子,捡了一条命,仅仅是摔折了一条腿。从此以后,造反派再斗争七叔,只要老叔在场,就没有一个人再敢胡作非为,“妈的,没有你弟弟在那儿站着,你早瘪茄子啦!”造反派悻悻地骂道。七叔赚了便宜,从内心里,得感谢我的老叔。而老叔呢,一生中给他造成最大的威胁就是饿肚子。在农村,一年的口粮半年光,来林区,口粮加工种补贴最多也才四十多斤,而且还是伐树刨穴的工种。他人缘好,诚实厚道又肯干活,但没有一个姑娘肯嫁给他的,三十多岁了还没成家。年三十,食堂的洪师傅说:“大禹呀!今儿个过年了,你就放开肚子吃,赔赚也不在乎你这一个人了!”洪师傅眼巴巴地盯着,一笼屉馒头,不多不少,六六三十六个,老叔往那一站,风卷残云,外加半盆子白菜汤,吃得洪师傅一个劲儿瞪眼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