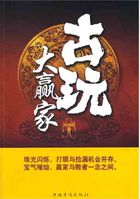“……很喜欢他,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喜欢。在毕打街第一眼看见他拿着报纸吆喝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他了。我把他从街上找回来,接到我那儿去住,给他不漏雨的房子,给他温暖的被子,给他买他爱吃的烤鸡。你知道吗?他妈妈死后,他就没睡过带房顶的屋子,他和一帮报童、流浪汉挤在一起睡在桥墩子底下,整夜与耗子、臭虫为伍,那个时候你在哪儿?在苏联接受特工训练,还是潜伏上海妄图打入我党内部?你根本不知道你儿子过着怎样的生活,你在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抛头颅洒热血,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亲生骨肉。”王大霖听着,只是听着。他发誓,今天不把张幕干掉,誓不为人。“看你那表情,肯定在责怪我指责你是吧?我有这个权力,因为我亲眼看到他过着怎样的悲惨日子。我不想让他再过那样的日子,我勾画过一幅美妙的蓝图。战争结束后,就带他去美国,送他上学,接受教育,住洋房,娶美国妞,永远不要回到这个肮脏的国家。可惜,你打断了这一切,我的计划将永远变成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他抓紧你的衣服的那个样子,我这个当叔叔的是永远没资格享受的。血缘这玩意儿谁也割不断,我彻底服了。我对他说,去吧,你爸爸就在这条船上,你找到他,就可以跟爸爸去北方了。他很听话,也很想找到爸爸,不然就不会央求我上报刊登那条该死的寻人启事了。我现在才知道,正是那条寻人启事害我惹了大祸,干了一件丧尽天良的坏事,我心中的痛苦丝毫不亚于你的痛苦。他在这条船上转了很久,终于在这儿找到了你,应该说是替我找到了你,不然我都不知道你长什么样。现在,我把这个哑巴孩子还给你了,你高兴吗?高兴吗?吗?”张幕多说了一个“吗”,夸大地表现着自己的得意。
跟刚才相比,他紧张的情绪已经得到缓解。他俨然一个胜利者,居高临下地望着王大霖,失去王锤后的沮丧已经被一种莫名的快感代替。
“然后呢?”这是王大霖开口跟张幕说的第一句话,他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然后你把教授还给我,我们来个交换,我用你儿子换回我想要的教授,你认为如何?”张幕晃着脑袋说。
果然,张幕的底牌翻了出来。不,不是底牌,而是第一张牌。王大霖把儿子紧紧拉在自己身边,对张幕说:“教授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我想你应该知道,你动脑子想想,我能给你吗?”“儿子对你的重要性,我也知道,”张幕立即反击,“你动脑子想想,我能轻易给你吗?”王大霖心里一震,张幕不是善茬儿,他要打出第二张牌了。王大霖盯着张幕,问:“如果我不给你教授呢?”“解开你儿子的衣服看看,那儿有现成答案。”张幕说。王大霖解开王锤的衣服,大脑顿时一片空白,他蒙了。张幕冷笑着,说:“你应该清楚,我是一名大学化学教师,没别的本事,但捣鼓一个炸弹还是绰绰有余的。那是我发明的定时炸弹,张幕牌。你肯定没见过,谁也没见过,连我都是第一次见。郑重提醒你一下,请不要担心它的威力,明确地告诉你,把这条船炸成一万块碎片是我对它最低的要求。你应该能看到,有一个比馒头还大的圆盒子,它特别厉害,里面全是电线。每一根电线都有它的特殊含义,剪断任何一根,电流都有可能连通起爆器引起爆炸,也可以中断定时装置。我很认真地奉劝你,想都不要想,你没有能力拆,我采用的是美国最先进,也是最新式的纽维尔式捆绑技术。我敢保证,你过去学的所有拆弹常识全部作废。就算不作废,你愿意拿你儿子的生命做实验吗?”张幕抬手看了一下腕上的手表,“现在是4点50分,炸弹将于5点准时爆炸,只给你10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不交出教授,那么你和你儿子就等着跟全船人同归于尽吧!”张幕第二张牌的分量很重。王大霖全身冒着冷汗,差点被这张牌击倒。张幕是他见到的最毒辣最阴险最强硬的对手,他用孩子的生命做赌注,逼一个父亲摊牌,而且这张牌是指定要王大霖认输的牌,让他一败涂地的牌,他没有其他选择,否则他会失去儿子。
王大霖镇定地问:“那,如果我交出教授呢?”张幕似乎早就等着王大霖的问题,他迫不及待打出第三张牌:“很简单,我会剪断需要剪断的那根线,终止计时器,让你儿子安然无恙地回到你的怀抱,让你们父子团聚。失散这么多年,思念该是多么折磨人的一件事啊!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我得到教授,你找到儿子,各取所需,各享其乐。说实话,我也不想让全船人陪我们玩这么危险的游戏,这条船上有年过八旬的老人,有刚满一个月的婴儿,有新婚燕尔的夫妇,也有跟你儿子年龄一样的少男少女,让这么多无辜的人给我们陪葬,我真的于心不忍。”“你说的有些道理……”王大霖点着头,表情诚恳地答道。“你看,我早就知道你是识时务者,俊杰不易得,那是人间最稀有的人才,可贵的是,这个人才就站在我面前,我想不高兴都难。”张幕愈加得意,开始揶揄王大霖。
张幕的表演有些夸张,以貌似强大的心态嘲讽对手,刚好证明他内心的恐惧。他在恐惧什么呢?王大霖心里激烈地推敲着,嘴上却若无其事地应付着张幕。他眼神迷惘,不解地问张幕:“有一件事我有点不明白,如果我答应你的要求,你怎么把教授带走呢?”“茫茫大海,四周无边无际,除了天就是水,是不太好离开。怎么办呢?”张幕挠着脑袋,然后做恍然大悟状,“凡事都要把准备工作做好,否则寸步难行,这个世界青睐有准备的人。王大霖先生,这条船我已经研究好几天了,它配有一条不错的救生艇,不大,刚好能坐三个人,教授、夫人和我。想追我吗?不可能,因为客轮速度不够,追不上救生艇。想对我射击吗?可以,完全可以,你觉得可以射中剧烈晃动中的快艇上的某个人就尽管开枪,我可以跟教授夫妇同归于尽。怎么样?我的回答令你满意吧?”这是张幕打出的最后一张牌。应该说,整个牌局设计得天衣无缝。王大霖无奈地摊开手,束手无策,他别无选择,再铁的汉子,也不可能不顾自己的亲生骨肉,再说,把教授以及全船乘客当赌注,不是他王大霖的处世方法,他不能让那么多无辜的人陪丧心病狂的张幕玩这种危险游戏,这是原则。
“我……答应你……”王大霖打出第一张牌。他的额头上渗出一层冷汗,脸色变得异常苍白。
张幕嘴角一撇,笑了,说:“聪明,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实际上,你也没有其他可选的。你千万别妄图跟我赌什么,你赌不起,因为你没有赌注。而我可以把你儿子,把全船人抛在赌桌上,你呢?我借给你一万个胆子你都不敢。信不信?”张幕晃着身子,好像赌局还没开始就已经胜券在握。
王大霖看见远远的驾驶舱顶上有两个人影,他知道那是狙击手祝小龙和封新,他们卧在舱顶,架着两杆莫辛·纳甘狙击步枪,相信瞄准器已经锁定张幕的脑袋。不知道什么时候,毕虎也端着卡宾枪出现在王大霖身后。大概他想回来安慰一下队长,正巧看到张幕举枪指着王大霖。他们知道队长这里出现棘手的情况了,不是扣动扳机一枪击毙张幕那么简单,尤其毕虎,他清楚地听到张幕刚才说的话,知道那个小孩就是队长的儿子,也知道孩子身上绑了炸弹,任何轻举妄动都会导致全船覆灭。
张幕也发现了驾驶舱上有两个狙击手,更看到了端着卡宾枪的毕虎。他把枪插进腰里,然后倚靠船舷,抖着双腿,对王大霖说:“让他们开枪吧!一枪就可以击毙我,打这儿,”他指着太阳穴,“薄薄的一层脆骨,高速旋转的子弹瞬间可以击碎它,你会看到我的脑袋就像突然爆裂的水阀一样,喷出的血足有一尺多高,我连哼一声都来不及便可以魂归西天。多么灿烂的时刻啊!这是最痛快,最没有痛苦,也是我最喜欢的方式,一个离开这个世界最干净最可爱的方式,我一生一世都在渴望它。求求你,让你的队员成全我吧!”王大霖不想理会张幕的表演。他蹲下身子,双手扶着王锤的肩膀,动情地说:“孩子,爸爸让你受苦了,我本想从上海回去后跟你们母子俩团聚的,谁知道在上海出了事。是妈妈带你来香港的吗?妈妈真的已经去世了吗?”王锤点着头,眼泪哗啦哗啦流着。王大霖喉头哽咽着,“孩子,你知道吗?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们,就像你想念爸爸一样,我到处打听你们母子俩的消息,可一点音信都没有,现在爸爸终于见到你了,你知道爸爸有多高兴吗?”王锤抱住王大霖,嘴里呜呜叫着,说不出一个字。王大霖放低声音,说:“孩子,现在爸爸遇到一件非常难办的事,你听爸爸说,爸爸这次来香港,是想把童教授带到北方,就是带到咱们老家去,这是爸爸的任务。童教授就是童阿姨的爸爸,他是一位科学家,是北方最需要的人才,爸爸必须把教授带回去。可是,有坏人不让,他就是跟你在一起的张幕,他是爸爸的死对头。他不但把你的舌头搞成这样,还把炸弹绑在你身上,如果爸爸不交出教授,你身上的炸弹就会爆炸。孩子,听爸爸说,不要害怕,不要慌张,爸爸不会让炸弹爆炸的,爸爸会千方百计救你。孩子,你是爸爸的好儿子,你要相信爸爸,爸爸会把这个难题解决好的,爸爸准备把教授交给那个坏蛋,你现在要做的是,站着别动,千万别动,扶着船舷,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听爸爸的话,好吗?”王锤呜呜着摇着头,眼睛盯着王大霖,好像有什么事要告诉王大霖,可又无法说出。
“唉!别逼孩子了,你看他多难办啊!纵有千言万语,也汇不成一句囫囵话。他是哑巴,什么也说不出来。”张幕幸灾乐祸地说。
“好吗?”王大霖继续问儿子,他想确认孩子听懂了他的话,但王锤仍然不停摇着脑袋。
王大霖的背脊全被汗水浸湿了,他不能再拖延下去,必须打出第二张牌。他回头对毕虎嘀咕了几句,毕虎点着头,枪口朝下,退着走了。很快,教授拄着拐棍被毕虎搀扶着走了过来,同时搀扶教授的还有童笙,跟在教授身后的则是教授夫人刘子晨。
王大霖向教授点了点头,面露难色地说:“委屈你了,教授,我没有选择。”教授拄着拐棍,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他看上去身体异常虚弱,好像不能长久站立一样。张幕看到教授,眼睛为之一亮,这是他来到香港后第二次见到教授和教授夫人。按照计划,去教授家取名单时就可以再见到二位老人,谁知道共产党的介入,把这一切都搞乱了。他望着教授,为自己曾经欺骗教授而羞愧难当。
教授看上去身体状况似乎不太好,走路颤颤巍巍,还需要两个人扶着。王大霖对张幕说:“教授这些日子身体欠佳,患了急性肺炎,咽炎也犯了,很严重,根本无法正常说话。你可以跟教授交流,但教授无法跟你交流。”张幕远远地端详着教授,大声问道:“教授,你还好吗?”教授面色冷峻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张幕能感觉到教授心中仍然充满怨气,他理解教授,也能理解此时的教授夫人,以及童笙心里的感受。有人发出一声尖厉的惊叫,是童笙,她看到了王锤。童笙扑过去,蹲下身子抓住王锤的肩膀,急切地问:“王锤,你还好吗?”王锤张开嘴,露出黑色的舌头。“怎么了?”童笙不解地问,“舌头怎么变成这个颜色?”王锤眼泪汪汪地望着童笙,默默地摇着头。“是我的错,我的错,”张幕应答着,“是我把他变成了哑巴……”“为什么?为什么?”童笙愤怒地盯着张幕,紧接着又倒吸了一口冷气,她看到王锤胸前绑着的圆盒子。王大霖说:“那是张幕绑在孩子身上的炸弹,他想用炸弹交换教授。”童笙的脸部肌肉强烈抖动着,那是愤怒至极导致的无法遏制的痉挛。她站起身,一步一步朝张幕走去。张幕似乎有些害怕,下意识地向后退着。童笙大声说道:“你以为是王锤透露你住在哪儿吗?难道你看任何事物都是一根筋,就没有想到有其他可能?没错,那天在毕打街,我打听过你的住处,但王锤始终没有透露一个字。是寻人启事暴露了你的住处,你个笨蛋,你上面白纸黑字地写着联系人张幕,这不是分明告诉全香港的人你住在哪儿吗?根本不需要王锤透露什么,每一个读报的人都可能看到。你唯一没有想到的是,王锤是共产党特遣队队长的儿子,所以你才明目张胆写出自己的名字。这一切完全是你的低级失误导致的,你怎么不问青红皂白就对一个孩子下毒手呢?你还是人不是?”童笙的话让张幕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他开始反击,仰面大笑着,“哈哈,十多年前,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曾经疯狂地爱着一个智商有问题的男人,这个男人当机立断拒绝了她,他不想跟一个陷入爱情智商为负数的女人为伍。我觉得这个男人很伟大,很高尚,他的思想境界是那个女人无法理解的,他避免了为这个社会诞生一个更低智商的傻子……”“啪”的一声,张幕脸上挨了童笙一个响亮的耳光。他瞪大眼睛,盯着童笙,好像不相信这个女人敢对他做出这样的举动,他捂着发烫的脸,拔出腰里的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