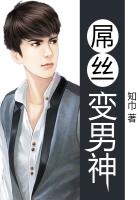都是受害者,当然也有同样的感受和愤怒。“这些家伙,别说是人了,就是逮着头老母猪,他们也不会放过的!男人的日子也真难熬啊!”“要不怎么说,不能让他们闲着呢!闲上两天,说不准会出啥事呢!这些家伙都跟那牤牛一样,见了个二样的,眼睛不得红啦!”“可也是!”一边牢骚又一边前进。关于高崇江和刘平山,几次犹豫,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女人毕竟是女人,一旦走漏了消息,后果之严重,可真就不可想象啦!荒山野岭,又都是些什么人物呀!还是小心谨慎更好。可是,到了现场,一看那场面,我们三人差一点把鼻子都气歪了,都在睡觉,横躺竖卧,呼噜连片,工具都在山坡上扔着,镰刀、镐头、大锉、磨石,乱糟糟的。毫无疑问,昨天夜里一宿没睡,上山后,集体都在这儿补觉呢!相比之下,我们忙活完两顿饭,又跋涉了三四里地,不辞辛苦地送来,这不是明显地被人耍弄了吗?放下背篓,陈菊花恶狠狠、委屈地说道:“睡觉来啦?你们可真行啊!里里外外,把我们给耍啦!”“哟!好家伙!王嫂来啦!”四班长韩苍揉着眼睛,紧忙爬起来高兴地说:“嗬,都来了!玉秀老妹子,你好辛苦啊!”然后又扯着嗓子向远处喊:“剑书!王剑书,你媳妇来啦!还不快过来,表示点意思!”他这一喊,大伙儿呼啦啦都坐了起来。不好意思,一脸的讪笑,同时也流露出了新鲜和意外。
女人上山,毕竟是大姑娘生孩子——头一回啊!王全清也过来了,非常抱歉,微笑着说:“嘿,这事干的,都怨我考虑不周,没再留下一个人送饭,小庞有病,我他妈的也懵了,一连两宿,可把大伙给折腾苦啦!来来来,趁热乎,赶紧吃饭,吃了饭好干活!”说完,又冲我笑了笑:“三四里地,这一篓发糕,可真不轻啊!”剑书过来了,看着我,不好意思地苦笑了笑。六班长郭洪都紧着说道:“这小子,像大姑娘一样,平时不放个屁,今天你媳妇来了也不吭声?晚上睡觉,还想不想上炕了?”“人家作家,能和咱一样吗?”有人酸溜溜地拿他开玩笑说。王剑书憨厚地笑着,抓一块发糕,就满不在乎地吞咽起来。我知道,剑书不是没话,而是所有的语言都变成了文字。即使是吃饭、干活、睡觉,也在构思着他的故事。晚上熬夜,白天干活,睡眠不足,凭着毅力,也还在顽强地坚持,出于对文学共同的追求和愿望,作为妻子,我总觉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疼爱和歉疚。吃食堂,大锅饭,若有机会,我是多么想为他单独做一次小灶啊!补补身子,增加点儿营养,同时,也让我这个当妻子的为丈夫尽点儿义务和责任。大伙儿吃饭,我和菊花就坐在一根倒木上休息。沐浴着阳光,也欣赏着山景。突然,从驻地方向的山包那边传来了一阵阵狍子的吼叫声,急切、悲哀、苍凉。如哭似泣般地,“汪——汪——汪汪——”一边吼叫,一边在拼命地奔跑。听上去,既有点惊恐,也有些恍惚。陈菊花一愣,“哎!狍子叫唤,好像奔咱们来啦!”侧耳听了听,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昨天晚上,狍子没在家,这光景又回来,说不准哪,又出大事了呢!”听菊花说完,我也猛地想到,那两只老狼,我观察的时候,尽管短剑刺入了脑门,头上也流了那么多的污血,但它们的眼皮似乎还在微微地颤抖,我刚有点疑惑,就听刘平山高嗓门大喉咙地轰开了,“看啥呢你,还不快走?有啥好看的!”现在回想,老刘头在思想上,也许藏着更多秘密吧?狍子的叫声已经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一边吃饭,一边皱着眉头观察和猜测着狍子奔来的原因。几分钟,一愣神的工夫,两只大狍子就到了跟前,其中一只是刘平山饲养的那只大母狍子,它目光忧怨,表情悲哀,全身抖着,直奔王全清而来。不再叫唤,用毛茸茸的脑袋,在王全清的小腹上摩擦和撞击着。摩擦两下,又抬起头来看看,目光悲痛,眼角上也挂着泪花。尾巴摇动,仿佛有千言万语在等待着向主人诉说。王全清抚摸着它的脑袋,刚要说啥,旁边的陈菊花就感叹着说道:“哑吧牲口,这么远跑来,肯定是来送信的吧,全清?”再看另一只狍子,没敢到近前,在远处站着,用窥视的目光侦察着动静,想过来,又害怕上当被骗;想离去,又恋着同伴有些不太忍心。目光是信赖的,也是警惕的。摇摆着小尾巴,既有些烦躁不安的迫不及待,又有些忧心忡忡的茫然若失。正吃饭的韩苍先冲它跺了跺脚,见它不走,就打趣地说道:“这家伙,好英俊啊!给我们母狍子当姑爷,你就大大方方地过来呗!都是一家人,还客气什么呢!”一个叫宋疤脸的工人说:“看咱们母狍子,在段长面前一句话不说,就满脸泪花地大哭上啦!”大伙儿再看,果不其然。母狍子先是用舌头舔,然后用脑袋撞。用前蹄子刨,见段长仍然不明白它的意思,就扭头奔到了高崇江面前。高崇江读懂了它的意思,站起来,望了望驻地的方向,皱着眉头,严肃又痛苦地感慨着说道:“同志们哪。家里头出事了,刘平山让狼群给咬死啦!别吃饭啦,快回去吧!”说着,又用左手捋了一下秃头胖脸上那几根滑稽的头发。他刚说完,母狍子就迫不及待地返了回去。跑出去有三十多米远,又扭回头来,汪汪地大叫,仿佛在说:“快点儿吧,我都要急死啦!你们还默叽啥呢!”段长似乎也醒过了腔,催促大伙:“别吃饭了!赶紧回去!”陈菊花更慌,“哎哟妈呀!这可咋办哪!别吃饭啦,快点儿走吧!回去晚了,刘师傅他——”关键时刻,女人的煽动比命令还好使,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扔下发糕,抓起镰刀,扭头就跑,边跑边喊:“快走啊,再走晚了,房子就没啦!”见人们跟了上去,两只狍子扭头就跑,边跑边吼,“汪——汪——汪汪——汪——”我们几个人,惴惴不安地走在了后面。
离驻地很远,我们就看到,秋阳下面,微风之中,白桦林周围兽毛飞舞,腥臭味弥漫。人们在沮丧中出出进进,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边叫骂一边呼喊:“杂种的,这群野狼贼心不死,又第三次杀了回马枪啊!”“看见了吧,看见了吧,那两只老狼,压根儿就没死!就等咱们走后,又开始报复!……老刘头,白瞎喽!这一身功夫……”熙熙嚷嚷,捶胸顿足,而那只母狍子呢?脖子伸出去老长,垂着脑袋,在食堂门前,悠悠地晃动。看得出来,为了主人,这只傻狍子悲伤到了极点。我们先是一愣,扔掉工具,又加快了脚步。奔到了跟前,食堂前面污血横流,尸体遍野,臭气冲天,目不忍睹。七八只老狼被砍掉脑袋,惨死在了草地上。叫人无法相信,更不可思议的是,那两只早已经断气毙命的老狼,脖子被砍断,两眼紧闭,脑袋正中各有一个黑枣般的白窟窿,剑已经拔掉,污血凝固,但那小半截半秃的尾巴,及另一只仅半个耳朵的尸首,众人一看,就轻易地辨认了出来,尤其是菊花,身如筛糠,颤抖着说道:“哎哟妈呀!这两只老狼怎么又……又活了哪?”再看刘平山的尸体,左手上还握着那把特大号的切菜刀。脖子被咬断,全身是伤口,眼睛闭着,胡子也已经脱落。看得出来,临死之前,残酷搏斗,是多么激烈。陈菊花夫妇仍然蒙在鼓中。特别是菊花,哭泣着喃喃说道:“刘师傅呀!你把我们都撵走……用自己的老命救了俺们呀!”王全清更是悲痛到了极点,欲哭无泪,不停地叹气:“唉!都怨我,咋就没想到呢!”看看周围和众人,我知道是该揭开谜底的时候了。
怯怯地弯腰拾起了染血的胡子,在菊花耳边,小声儿说道:“陈姐,刘师傅和咱俩一样,也是个女人,你看这胡子,历来就是……”话没说完,陈菊花就像突然中了邪,目瞪口呆,瞪着眼珠子喊道:“你说啥老妹子!刘师傅他,是个女人?”她这一喊,众人也都呼啦一声围了过来,相互望着,惊讶、骇然、疑惑、迷茫。张着大嘴,时而摇头,时而又专注,异口同声,喃喃着说道:“不可能,不可能啊!刘平山他怎么能是女人?这么些年啦!……”摇头感叹,最后又把目光投在了尸体和那张灰白的脸上。七嘴八舌,说不出是惊讶,还是更大的恐惧。“不相信呀!你们问问高部长好啦!高部长他最清楚不过!”我边说边扭头看了一眼高崇江。只见他面如死灰,泪雨滂沱,全身抖着,手抓尸体,哽咽着喊道:“……谢、银花呀!……谢银花呀……我老高咋就没、没想到啊!”喊着喊着,竟然双膝一软,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张开大嘴,由哽咽变成了号啕,“呜呜呜呜……谢银花,你好命苦啊……”众人再次惊呆,也再次发蒙,“你们俩是?”“他不是东北最大的土匪头子,国民党的将军吗?”“高部长,你开始就知道她是个老太太?”“我操!怨不得,她从来不脱衣服睡呢!”“还有,这些年啦,在咱们三工段,从来没见过刘师傅他当面儿撒过一次尿!原来是,哎呀!咱们这么多人,天天在一起,咋就没发现呢?还是李玉秀的眼睛厉害啊!”是赞美、揶揄,还是别有用心?事后对菊花,我终于向她透露了那次所见所闻。
在原来那两只狼的墓地旁边,大伙儿动手,又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大坑,把所有野狼的尸体,包括庞国君的尸体,统统地葬了下去。与狼紧紧挨着的是刘平山的坟墓,全段职工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事后,高部长才终于跟我们说了实话,“……1940年前后,我们俩都是抗日联军的师级干部,我是政委,她是参谋长,她的哥哥就是北满最大的土匪头子谢文东。谢文东曾经是抗日联军第八军的军长,妹妹谢银花,自然是他的得力助手。在哥哥的逼迫和劝说下,兄妹两个均先后投奔了国民党。在那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夫妻了!不过政见不一,最后也只好分道扬镳喽……”嘎拉其河及梧桐河附近地区,都是两人当年战斗过的地方。“高饶”事件出现以后,作为东北军区的组织部长,高崇江在鸡爪子河林场与谢银花邂逅相遇,既是命中注定的缘分,也是不幸中的一次安慰。谢银花女扮男装,但不管怎么化装,高崇江来后,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偷偷地幽会,在密林深处,除了李玉秀,恐怕再也没有第三人知道了吧?不管是情人还是夫妻,高崇江不管怎么悲痛,大伙儿都能理解。不能理解也深感焦虑的是那只母狍子。
趴卧在坟前,闷闷不乐,不吃也不喝。不管谁劝,也均是徒劳。第八天头午,昂着的脑袋终于垂到地上停止了呼吸。“唉!人哪,论感情,都没有只狍子深哪!刘师傅九泉有知,也该知足啦!”陈菊花感叹道。我们两人在死狍子面前都流下了大把大把的眼泪……第二年春天,怀了孕的我,已经显怀了,动作迟缓,精神压力也很大。怕发生意外,怕回不到故乡,怕见不着爹娘。一天到晚郁郁寡欢,心事很重。可是就在这个期间,一件意外的特大喜讯,突然降到了我们面前,是多日没见面的车老板子唐金彪,赶着马车,兴致勃勃地又来到了我们三工段,进门就嚷,满脸胡子,像开花了一样。“李玉秀、王剑书,报喜来啦,大叔给你们金榜题名,比金榜题名还要让人高兴啊!你们快看看,黑龙江出版社,给你们来信啦!”我们俩,还有陈菊花夫妇慌忙地迎了出去。激动万分,孩子般地从唐金彪手中接过了那封渴望了十几年的编辑部回信。牛皮纸信封,下面是红色的印刷体“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括弧是钢笔字,“第一编审室”。我两手抖着,小心翼翼地打开,信笺是毛笔字写成的,工整大方,流利潇洒,字数不多却非常激动人心。
王剑书、李玉秀二位同志:寄来的长篇小说书稿《雁舞塞北》,生活气息浓郁,经研究,准备列入下半年的出版计划。但文字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修改。接函后,请二位速来出版社面谈!……没有看完,我的眼泪就噼里啪啦地滚了下来。剑书更像傻子一样,裂着大嘴,先是傻笑,马上又大哭,激动的眼泪比我还多。是啊!十年耕耘,十年奋斗,如今总算是丰收在望啦!别说我们两口子,其他工友也为我们激动得不知道如何是好,特别是高崇江和王全清,一劲儿地夸奖:“小王,不简单,不简单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呀!年纪轻轻就出版了长篇小说,尔等之辈,可真是咱们大山里的骄傲啊!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常言说的好嘛!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认识了二位,也是我这个老军人的一大荣幸啊!”“行!行!好样的!好样的!白天干活,晚上写书。继续下去,肯定就是大作家啦!”陈菊花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陪着我哭,也陪着我笑,“哎呀大妹子,你们俩这会总算是熬出头来喽!……不管到哪,进京上省,可千万别忘了你这个傻大姐哟!你这一走啊,三工段,大姐我就再也没有个说话的知心人喽!走吧!走吧!这深山老林的,早早晚晚我也得离开!我也得离开……”眼睛红红的,没等分手,她说话就有些颠三倒四了!大伙为我们举行了一次告别午宴。回到场部,才从唐老鸭的嘴里头知道,剑书的舅舅——田景宽,被判徒刑,在外地改造,舅母和傻冬冬也搬到农场去居住了。我在街上溜达了两趟,不知道为啥,那几十只狗狼,在家属区我一只也没有见到。
第二天一早,唐金彪就征求我们的意见道:“乌伊岭通车了,一天一趟,直达伊春。伊春就有直达省城哈尔滨的火车。你们二位是坐马车去鹤岗呢,还是从乌伊岭坐火车去伊春?”没有思索,我和剑书几乎是异口同声地答道:“去鹤岗!坐你的马车,再过一次野狼沟!看看那儿的野狼,到底还有多少!”“行!好!有种!那我今天就主随客便了!上车吧二位!今天,咱们就再从野狼沟过它一次,将来继续写书,也能多点儿素材!你们俩的决定,我唐金彪双手赞成!”原来的车,原来的人。不同的是,牵引的马匹大批下岗,驾辕的还是白马,前面的枣红却减员了一半。我感到好奇,坐在车上,不解地问道:“哎,唐师傅,那三匹马呢?咋变成四匹了呢?”唐金彪悠了悠鞭子,晃晃脑袋,叹息着说道:“唉!一会儿哪,你就知道喽!不减员,不就是浪费了嘛!驾——不那么威风,可也真就省心多喽!”路过嘎拉其河大桥,大桥没变,河水也照旧,木箱子还在。但狼群再没有看到,马匹不再紧张,晃动着脑袋,咣啷咣啷,稳步前进。蓝天、白云、远山、近树。
春风拂面,满眼是碧绿。老鹰在头顶上翱翔,马匹在放胆地前进。昔日的狼群,此时此刻,都哪儿去了呢?在野狼沟的沟口,我忽然看到,离我们有二百多米远,两只老狼在冲着马车张望,一只是小半截尾巴,另一只则是半个耳朵,我不由地一震,脱口说道:“哎呀,剑书你看,那两只老狼不是早已经死了吗?去年秋天,与刘平山同归于尽……”剑书没有回答,非常冷静地,把多疑的目光转向了唐金彪唐老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