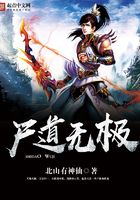这是二哥死后的第二年我回家后目睹的景象。妹妹已经十二三岁,出落得愈发标致了。她穿着一条白裙子,像一只小鸽子那样可爱。我们可以从她的身上看出那个狠心将她遗弃的母亲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人。妹妹后来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她是无意中听别人闲谈说到的。她也曾经暗自去寻找过她的亲生母亲,可是茫茫人海,加之当时襁褓里没有任何纸条之类的东西,可以说完全是大海捞针。妹妹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她悄悄地进行,又悄悄地结束了这件事情。
妹妹的功课很好,每次都能捧奖状回来,这让父母很是欣慰。就在我回到家的那次,恰逢妹妹要去县城参加歌唱比赛。尽管会有老师陪伴,父母还是不怎么放心。母亲一见我,马上就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
我母亲眼眺远方的大道,鸡冠花在她身后的斑斓色彩犹如涨潮一般。她的脸部瘦削,有很多的棱角。脸上的笑容却是那么柔和。她满怀喜悦地说:“我第一回这么一望,就把我的儿子望回来了。”她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她一边说一边抚摸着我的手。她之后说,要是你二哥跟你屁股后面一起回来多好啊,说着说着就低低地呜咽起来。
父亲在厨房里探出头来,说,你又来了,又来了吧,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自己的身体当心。父亲似乎又老了许多,鬓角的白发又多了一撮。他额上的皱纹很深,每一条远远看上去像是黑色铅条,在他的脑袋上形成了几道箍。胡子似乎刮过,但是像一个无精打采的韭菜地。
父亲在家里排行老四,他的大哥是县城一家化肥厂的推销员,自己开着一个小百货店,后来因为外出一次车祸死了。当时死得很难看,几乎看不清楚面目,最后还是身上的一块胎记和一颗假金牙,帮助他们作了最后确认的。他的二哥则是一个下岗工人,和父亲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父亲还可以拿几个伤残军贴过日子,而他的二哥则必须起早贪黑骑自行车四十华里去远郊一个纸盒厂上班,为了区区300元。三哥是一个羊角风,据说大部分时间是在春季发作,发作的样子很是可怕,我没有见过,听父亲说倒在地上翻白眼,吐白沫,一直抖个不停。羊角风不发作的时候,在家附近摆一个台球盘供人娱乐消遣,得来一些零钱以此补贴补贴。老五算是一个厉害的角色,只不过走的道不一样。他在县城菜市场收保护费,道虽说不俗,日子过得也还不错。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小姑妈,现在成了一个老板的二奶。有一次我和父亲去县城见过,是那种典型的风骚美人,虽然那时候她还没有从学校毕业,但就有招蜂惹蝶的意思了。
他们似乎不怎么搭理我和父亲。事实上,我父亲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送到了远离县城的小镇,为镇上一户姓安的人家收养,他几乎和我母亲是兄妹,后来结成了夫妻。当初我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就是这么个想法。据说外祖父是一个开明的人,有两撇老式的胡子,话语慢条斯理,亲切可爱,这都是父母告诉我的。
父亲每年都要去县城一趟,有时候我会跟他一起去,有时候也会带姐姐去,有时候他独自一人。我们上门总会带些东西,大部分是镇上的土特产之类的,由于他们的冷漠和城里人特有的骄傲感以及一直把我父亲当做那个家庭的局外人,父亲每次上门总是很快就离开了。我的祖父和祖母还算不错,他们每次都心怀歉意地挽留我们吃饭。
我对我的祖父深有印象。据我的观察,父亲几乎就是他的一个翻版。据父亲说,祖父当年也受过不少罪。对于祖父的历史我的了解也就这么多,一切可以想象。那么多的历史资料和书籍告诉我,那个年代很多的人都受过罪,他们的人生错综复杂,受罪却是千篇一律。有一个诗人在一篇文章里如此写道:那些日子,许多的人只是一个受难者。这句话和我祖父的浓眉一样令人难忘。至于后来祖父成为我们血亲里继二哥之后第二个溺水身亡的人,这是始料不及的。在此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在第一章提到的那个二伯并不是我父亲的二哥,而是我母亲的堂二哥,据母亲说他们是自小一起长大,兄弟情谊很深的。再有据说我那位未曾谋面的外祖父生前曾经有过一些许诺,那次返乡说他(指二伯)另有所图并不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当然具体是什么我始终不太清楚,我也不想去搞清楚这个复杂的家族问题。无外乎就是那么点散了架的家具和家族传说中的瓷器宝瓶之类的。这点财产继承的小利,如你所知,我那位心地善良的二伯还是不得不放弃了。
父亲从他退伍回家后,改了以前的很多脾性,母亲说他以前脾气不怎么好的,都是因为老爷子惯的。
在这个家族里我清楚父亲小时候来到安家是备受重视和欢喜的,毕竟他们视他为这个家族的男丁。他由以前老爷子惯出来的任性、暴躁,变得出奇地安静、平和。我猜测母亲的病体是他沉默下去的理由,当然他的腿被流弹击中成了一个伤残,也是使他日后沉默寡言的一个要素。至于那个漂亮的女售货员将他写给她的信件公之于众变成集镇上的笑谈,也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要知道,我父亲当年是很英俊的一个男人,我的意思是说,是父亲的自尊使他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来的话,他的那些光荣历史也就是和我们说说了,那个时候二哥和我最喜欢的玩具就是父亲退伍回家带回的不少金黄色子弹壳和一些红色五角星。谁也不知道他如何将这些东西带回家的。后来这些东西又成了妹妹的炫耀之物。妹妹至今还保留在一个文具盒内。
父亲对生活似乎没有什么怨言,这正如他那次对返乡的二伯所说,这是老天爷摊给他的,他没有办法,谁也没有办法。父亲还在那天说过另外一句话,他对二伯说,兄弟,老天想在哪儿刮风,就在哪儿刮风,这都是老天的事情。
那次父亲在厨房里忙了半天,烧出了几道可口的菜。这么多年,你老子其他不会了,就会烧几道菜。父亲抿了一口酒如此说道。
母亲坐在饭桌的另一端,她满是怜爱的目光看着低头喝酒的父亲。这一幕我至今回想起来,都要强忍住泪水。父亲的酒量并不大,一盅左右,他一生中从不在外恣意醉酒。他知道家里还有一个老药罐在等他,他不能误事。他多半在家喝一点,这是他这些年来养成的一个习惯。
父亲给我斟了一小杯酒,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和父亲共饮。
父亲的脸颊上微微发红。他喝酒喝得很享受,抿住嘴,总会喝出声响来。他总是不停地用筷子敲着碗碟的边缘,叮叮咚咚作响,示意我们要大块夹菜,否则他就会自责地说,大概是菜的味道不好。
那次桌上,父亲特意摆了两副碗筷,一副是给姐姐的,一副是给二哥的。他在布置桌子的时候,我听见他低低地嘀咕着他们的名字。在K市,姐姐听完我告诉这一幕的时候,她自然感动不已。二哥生平没有照片,唯一的那张全家福上,二哥歪着头,也拍得不是很理想。我对二哥的记忆总有一个隐秘的引点,那就是他著名的花衬衫。一想起二哥,总先是想起一件花衬衫。且说,我与父亲共饮那回,娇美的妹妹还在席间一展自己的歌喉,那声音清冽悦人。我对父亲说,你们说得对,妹妹才是真正的艺术家。父亲望了望我的长发,莞尔一笑。我第一次见到父亲笑得那么恰到好处,里面什么都包含了,谴责、原宥、狡黠。
在家里我母亲总是半开玩笑地喊我“长发”,就这样“长发”成了我的雅号。妹妹总是问我,三哥,大学里都这样吗?男孩子都留长发吗?那么女孩子应该要留短发喽。我的回答使她要高兴得跳起来,我说一进大学不久就要改头换面了。她说,我将来就要剪得短短的,长发虽然好看,但是不利索。后来,这个后来就是我决定写这篇小说之后的若干年,妹妹考进了音乐学院,的确如她所言剃了个短发。我们时而见面还会记起她这个年少时的笑话。当然这都是将来的事情了。对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大学意味着一个新奇无比的世界,那得经由一道若干书本铺成的康庄大道。母亲总是打断妹妹的遐思,说,别听你三哥瞎说八道。哪儿有的事情,没有,无论到哪儿,女人都是长发。
二哥对我的长发却有着不同的观点,他曾经如此说过:“这样可以打辫子了,我们有鸡鸡的为什么就不可以打辫子呢。”此话有道理。
在席上,母亲似乎很少言语,她默默地吃着菜,眼睛一会儿注视着我们,父亲、我和妹妹,一会儿注视着姐姐和二哥的空碗筷。一吃完饭后,母亲就上了床,埋在枕头里哭了起来,她的哭声低低回回在房间里萦绕。这个时候父亲在桌子上就会很有力地敲了敲最大的那个汤碗,声音脆亮。他说:“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这个人就是这个德性,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事实上正是如此,我很少回去的一个小小因素就是母亲总是把每一次的家庭相聚变成一个惨兮兮的局面,我的记忆所及,几乎无一例外。母亲对姐姐充满了没完没了的想念,她颤颤巍巍地抓住我的手,告诉我说,又梦见你姐了。妹妹总是站在她的身边,一手搭在她的肩上,一手拿着一条给母亲随时擦眼睛的毛巾。你姐姐也不知道生活得怎么样,以前还有一封半封信,现在一个字也看不见她寄回来了。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多有不便的。母亲絮絮叨叨的叙述浸泡了泪水。就在我临走的时候,她抓住我的手,说,你要是碰见她就好了。碰见她无论如何要她回来一趟。
父亲对母亲近乎谵妄的言语不置一词,我只得安慰她说:“好的,只要碰见,一定把她带回家。一定,我保证。”在这个小集镇妇女的眼里,外界的城市几乎就是一个个连在一起的长长的大街,她固执地相信车水马龙中相逢的偶然。
我是在妹妹比完赛返回家之后才离开的,妹妹的音乐老师是一个秃顶的老头,他穿戴整齐,戴着一副镶金边的眼镜。他是一个外地人,早年在此扎根。老婆是本地人,儿女都无一例外地继承了他的音乐事业,据说大都在省城或者外地,还有一个在国外皇家乐队里。他家的儿女曾经也是我们集镇上有名的人物。集镇上每次考上好学校的,总会在集镇的八水桥附近公榜。他们的大名可谓闻名乡里。想当年我的大名也曾经出现在那个大红榜上过的。此后的几天里,那张耀眼的大红纸上,出现了我妹妹的名字。音乐老师一路上都在夸奖我妹妹的音乐天赋,事实上,妹妹后来成为一名短发音乐家,这位秃顶老师功不可没。那次的比赛场地是在县城的人民剧院,我们从集镇的枫杨树大道一路骑的自行车,那个时候城镇还没有通中巴车。我们整整提前了一个钟头。当时为了赶时间,妹妹和我都没有来得及吃早饭。我在附近的一家食品店买了一个面包,因为不敢走远,妹妹很想吃碗馄饨,最后只得以一个面包充了饥。虽然我们知道父亲的大哥家就在附近,但是我们出于一种自尊没有上门叨扰。倒是比赛完了后,我们去了祖父、祖母家。祖父母两人正在家里看电视,开了门之后,他们都认不出我们来了。
祖父乐呵呵对祖母说,他还以为哪儿来的两个女孩子呢。那回,我的长发的确吓了他们一跳,当然妹妹金灿灿的奖杯也把他们乐得不轻。
音乐老师很是细心,他还为妹妹准备了一杯水,以润喉之用。我们在剧院外面的大厅里看见很多和妹妹年龄相仿的孩子。在嘈杂的人群里,他们一个个都沉默着,只有少数几个和颜悦色,胸有成竹的样子。从妹妹的表情看得出来,她也显然作好了准备。妹妹在那些孩子中间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虽然一个十来岁的小集镇少女身上还看不出所谓美丽和魅力来,但是她往那儿一站,你的视线不得不第一个将她挑选出来。
妹妹和音乐老师消失进剧院后台的大门,我的心反而紧张不已。我坐在剧院后排的位置上,静静地闭上眼睛。一切正如妹妹事后所说,那种感觉真好,就像梦一样。灯光照耀着你,舞台上只有一个人,刹那间你会觉得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灯光在你的头上,犹如永恒的日月。
我听见了剧院里潮水般的掌声,一波一波地涌动。后来我一闭上眼睛,就会置身在旷阔的剧院,我的思绪飞越无数观众的头顶,飞向舞台的中心。那里我的妹妹,娇美动人,歌声嘹亮。我将这激动人心的场面转述给父母听的时候,他们都笑了起来。父亲说:“难道我说错了吗?我说的哪回错过?”他说过我妹妹才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话可谓一箭双雕,既指责了我的长发,又表扬了我的妹妹。
4.跑步的但丁
但丁打定了主意,他要和女朋友分手。这个念头缠绕他有些时候了。他看见她蜷缩在床上,像一只赤裸的大虾。他忽地升起了一股厌恶之情,恨不得将她扔出窗外。可是这个歹毒的念头还是吓坏了但丁。早晨的光亮在窗帘上飞溅,她的脸部埋藏在一只花枕头的阴影里。他忽地又觉得她很无辜,他怎么可以如此对待她呢?他舔了舔唇,继续眺望着窗外。远处的大街上不断有人骑自行车闪了过去。在他的角度上看过去,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像是从树冠里穿梭似的。近处的巷子逼仄而昏暗,偶尔有人响一两声铃铛。但丁回头又望了望床上的女朋友,女朋友还陷在睡眠之中。
他绞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像困兽一样。这个情形和大学时代在充满架子床的大学公寓几乎一模一样,那个时候他为如何追求她而绞尽脑汁,费尽了心思。而现在却要将她抛弃。这样两种迥然不一的生活场景犹如一枚钱币的两面。
他第一次见她是在大学一条漫溢着桂花香味的小径上。那个时候似乎是刚开学不久,她坐在邻近一个池塘的石椅子上看书,脸庞如皎然明月,全身都处在一种静穆之中。她显得那么优雅非凡,穿着一袭长裙,头顶上的树冠都似乎发出一种神奇的光亮。那会儿但丁不得不被吸引住。女孩有好几次都坐在那儿静读。那些树阴的深处有很多的椅子,椅子上也坐着一些在读书的人。但是这一切,包括后面的花丛,都形成了一个曼妙的氛围和背景。这些都为她而存在。但丁开始心神不宁,开始悄悄地尾随着这个女孩。后来女孩说,其实她早已经发觉。但丁对女孩的跟踪没过两三天的工夫就有了进展。她住在哪栋公寓,经常上哪个自修教室,在几号餐厅就餐,甚至她的饭盆号、班级信箱,但丁都了如指掌。很快他就开始真正行动了。
但丁之所以成为一个诗人,这大概和很多诗人的经历相似,都是因为爱情的缘故(当然这说法并不绝对)。现在难以想象,但丁在那些个夜晚写了多少诗篇,那个时候他激情澎湃,诗思泉涌。女孩后来成为他女友后,将很多的求爱信给但丁看。但丁替自己捏了一把汗,因为他发现有些家伙的诗艺完完全全地超过了自己。当然他要做嗓音最亮的公鸡。他要一直唱下去,直到母鸡低下头来,掀起屁股。这个拙劣粗俗的比喻融会在但丁后来的诗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