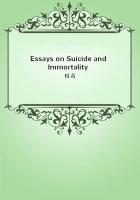生活依旧在工作的枯燥与爱情的甘美中并肩前行。三个月的见习劳动,让刚参加工作的禾玉曼感到每日的坚持,在技术层面上似乎并没出现多少螺旋式的上升,而是被定格在相同形式的循环往复中,时间过得漫长而无聊。
一天早上,刚上班不久,宿舍走廊上忽然传来一声呼叫:“小禾!”见无人应答,姜科长提高了嗓门:“禾…玉…曼!”一听是姜科长的声音,正在读外语的禾玉曼赶忙跑出宿舍。
“赶紧到车间去一下!”
还没等到禾玉曼开口,顶头上司已经转身准备下楼。她锁上门,向车间的方向一路小跑。昨天晚上她还在想:如此态度,假以时日,何以应对生产中出现的问题?没想到一次离岗,恰好就出了问题,领导安排这么重要的岗位,自己却私自离开。禾玉曼一路都在责备自己。
来到车间。几位职工蹲在地上,脸色阴沉,围着几张牛皮发懵。禾玉曼瞥了姜科长一眼,神情马上变得紧张起来,想到自己昨天晚上没有在岗,不禁心里有些发虚,她连忙蹲下,只见浅蓝色的牛皮上有几团不规则的几何图案,就像什么深色液体留下的痕迹。她用手指抠了几下,感觉有些发硬。
最近,禾玉曼一直跟中班(下午两点至晚上十点)。昨晚下班时,为人温厚的组长师傅笑盈盈地说:“要是没啥事,吃过晚饭你就别来了。”她爽快地答应了。
“这是一起严重的质量事故,查不出责任人,你们就得集体受罚。”姜丽珍神情严肃地发表早间的第一道训词。
“小禾,你说一下昨天的操作过程,”姜科长直愣愣地盯着她说。
“我…我昨天……”禾玉曼窘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在还没搞清事故原由的情况下,她用非常低哑的声音,把自己工作缺岗如实作了交待,以此作为最真诚的忏悔。
姜科长听完,气得用鼻腔‘哼!’了一声,扭头就走。几名职工抓耳挠腮,神情沮丧,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在车间的通道上踱起步子,湿胀的胶靴在有些寒意的水泥地面上摩擦出无奈的声响。本来就不多的收入,如果有罚款,就会更加囊中羞涩。
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接班走进工厂,成为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年轻力量。每天上班,换上沾满污渍化料的工衣,胶皮靴(工厂至少有一半职工都是类似的包装),每日面对三十多吨重的牛皮,硬是靠着几个人力去完成装卸、运输和加工。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一切就像天体的运行一样周而复始,按部就班。
车间的大门,一年四季都敞开着。那是为了装载皮子的车辆进出顺畅,或是为了有一个良好的通风条件,让有毒有害气体能够更好的散发。只有到了冬天,才会挂上几片麻袋布遮风避寒。钢筋水泥铸就的地面,承载车轮春秋冬夏的重压;酸碱盐的侵蚀;热水凉水的交替浸泡;不堪忍受天长日久的摧残,裂开一道道深深的怨痕。
常年累月劳作的人们,无论是艳阳高照的夏日,还是寒风瑟瑟的冬季,或是细雨绵绵的秋天,都是一身单衣,汗流浃背,多少年如一日。一代又一代制革人,就是这样默默无悔地坚守着这片饱含希望,饱含梦想的阵地。
瞧!他们又开始新一天的忙碌了。启动转鼓倒出皮子,装上架子车,运向蓝皮仓库。禾玉曼跟随奋斗者的脚步来到仓库,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问题牛皮的数量及损失程度。
新建仓库堆置的蓝皮,就像家乡晾晒场上的麦垛,还有严密包裹整装待发的出口蓝皮,中间通道上堆着刚运来的牛皮,蓝色废液满地横流。
“挑选率能达到多少?”禾玉曼走向一位戴着花镜,满脸皱纹的老师傅询问。
“不一定,”
几位年轻人猫腰铺平皮张,老师傅弯腰仔细察看质量,随后喊一声:‘二级!’有人用木尺对准牛皮的背脊线喊道:‘28!’又在横向的某个位置落下尺子喊道:‘21!’一名女工赶紧在皮子背面和尺码单上同时记下这三个重要数据。
一张牛皮,像验明正身的尸体被立即拽到托盘上折叠码好。当老师傅喊三级、四级或等外时,就不再丈量尺寸,而是直接甩到皮垛上,作为工厂加工的原料皮。
禾玉曼看了一会儿,发现‘问题牛皮’属于个别现象,就出了仓库。一股寒风从湿冷的地面上刮起,吹拂着她的额前碎发。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她忽然想到先同车间主任交换一下看法,便沿着通道继续往前,拐过弯,再往西走一百米,就是车间主任的办公室。
晨光越过拥挤车间的屋顶,照在往来车辆和行人的通道上,照在她的背上,前方却映出一个高大模糊的阴影。禾玉曼刚跨进办公室,年轻的车间主任蒋志平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热情招呼,倒茶让座。蒋主任的这一举动,让她颇感诧异与不解。
“小禾,我正好有问题找你,”他一面倒水,一面笑呵呵地说。
“我……”她误以为主任所要说的问题正与自己思虑的问题不谋而合,却在刚一开口就被岔开。
其实,对于车间出现的质量问题,早上刚上班,蒋主任已经看过了,才知去会姜科长。至于事故的原因,他有一些想法,却又怕不成熟,也就不便与她作进一步的探讨。
“你们大学生都是高材生,天之骄子,”
“哪里!实践比理论更加重要,”
蒋志平的话不乏带有恭维的嫌疑,也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改革开放初期,每年4%的高考升学率,百废待兴的各行各业对人才的极度需求)。蒋主任有意绕开避而不谈的质量问题,禾玉曼打算准备离开。
“我现在上你们学校的电大,有些课程还需向你请教,”蒋主任说着就从抽屉拿出一本《机械制图》,又从包里拿出一些糖果递给她。这个时候,一位高个头,满脸青春痘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不假思索又带诡秘地微笑着说:
“领导向你献殷勤?”
“我帮他看作业,想哪儿去了,”禾玉曼被一句莫名其妙的话瞬间烧红了脸颊,快速反驳道。
“看看,别胡说!”蒋主任一手指着桌上的书,笑着为其辩护。
“是时候了!”年轻人一边剥着主任寄给他的糖果,一边紧追不舍的借机打趣道。
这位年轻人名叫郑正,是牛皮车间配料室的一名员工,和蒋志平同一年接班走进工厂。长着一副国字脸的蒋志平坐在那里只顾嘿嘿直笑,一只钢笔在手指间莫名其妙的不停翻滚。禾玉曼再也没有心思给他讲题,可又不好意思薄了领导的颜面。
别人调侃的戏言在禾玉曼的心中渐行渐远。每天下午,她照例按时来到车间,上中班的职工先到上游工序装运牛皮,两人一组,用近1米长的铁钳,将膨胀后的重量达一百多斤的牛皮逐张抬上架子车,接着一个驾辕,一个用铁钳抵挡在随时可能滑落的牛皮上走出车间,快步冲向高出地平线的露天磅秤称量,再一路小跑运到加工车间,装入转鼓。按照工艺规定的流程,调配热水凉水至所需要的温度,加料……
这个岗位,转鼓停下,就得干活;转鼓转动,就可以稍作休息,这是有别于其它岗位的显著特点。加完料后,他们就坐在休息室里等候时间。早上发现的质量问题,似乎和他们没什么直接关联,事实到底是怎样的?还得等候专家最后给出结论。
不足十平米的休息室,黑乎乎的墙壁上挂着日积月累无法褪去污迹的工衣,地上东倒西歪的胶靴,这是早班职工脱下的战甲。靠墙的四周放着已经磨得油光发亮的衣物箱,这是他们利用休息时间,利用工厂废弃的小木箱自个加工而成的。瞧!每个箱盖处还加了把小锁,里面放着私人物品,平时又被当成休息的座椅。
一位刚来不久,身材有些矮小的瘦小伙儿面对每日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些吃不消,一到休息时间,就迫不及待地找个空位躺下。一条腿提溜在半空,湿透了的裤腿‘嘀嗒…嗒’地淌着水,让湿漉漉的地面更加潮湿。没什么兴致时,大家缄默不语,各忙各的事情。喝茶,吸烟,或津津有味地嗑瓜子。有共同话题时,你一句,他一句就热聊起来。
“听说对面肉联厂每个职工要发一套煤气灶,”一位留着整齐髭须,膝盖打弓,脚后跟蹬着箱盖的年轻人发布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
煤气灶,这个新名词,让做饭仍在使用蜂窝煤炉的大多数职工感到非常好奇,几乎同时睁大了眼睛,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发布者的脸上,就连没了精神的瘦小伙也立即翻了个身,坐了起来。禾玉曼同样感到惊讶。只有家住城郊,端着白色搪瓷缸喝茶的组长师傅对此没有显出任何兴趣。他一大家子人,一年到头地里的柴火都烧不完。
“不过,听说咱们厂也要给每人订做一套毛料西装,”发布者再一次慢条斯理地发布第二条新闻。
屋里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大家期盼着美好愿望现实的那一天,并纷纷猜想,议论该是什么颜色,质地……
“嗨,小朋友,啥时候把女朋友带来看看?”精力充沛的新闻发布者接着又转换了话题,苗头直指躺那位瘦小伙。
“八字还没一撇呢,”为了逃避同类接下来穷追不舍的调侃,他忽略了身体的疲乏,有些害羞地走出了休息室。
为了融入群众,禾玉曼站在门口的桌旁待了一会儿,无法忍受狭小空间呛人烟气,说了句:“师傅,吸烟有害健康!”便离开了。一位性格活泼机灵的年轻小伙儿看了下墙上的挂钟说:“时间到!”大家起身相跟着向车间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