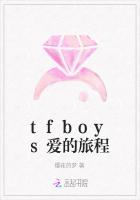陪大哥去放牛牧羊的地方很远,那里能很近的看到火车,听到它嚣张的鸣笛,震耳欲聋。还有那有规律的咔嚓声,像一条绿色的长虫子蜿蜒驶来。每次看到它我都有种想爬上去的冲动。“火车要去哪儿呀?咱们爬上去看看好不好?”
大哥为我的幼稚发笑,“你真能瞎思谋,我也不知道它要去哪儿,但是这是拉煤的车,你若上去就会和煤一样黑。我可告诉你火车附近很危险的,千万不能靠近,还想爬上去,那得飞人才能办到。”
“噢!那还是算了,我被太阳晒的已经够黑的了。”看着渐渐远去的火车我撅起了嘴。大哥听后爽朗的笑了。
那是一片山林,好多好多的树郁郁葱葱,草植繁茂,野花遍地。大哥坐在树荫下很专注地读呀背呀,而我呢从小就不粘人,一会儿捉蝴蝶;一会儿逮蜻蜓;一会儿扑蚂蚱;一会儿摘野花。。。忙得很也快乐的很,不需要别人陪也不怕火辣辣的太阳,那时的开心很容易是无所顾及的,怎么开心怎么来。
林子里有很多刻着字或刻着花纹图案的大青石,还有雕刻成动物形状的不完整的青石,我非常喜欢,觉得它们有一种雄浑而又霸气的美,特别想把它们都搬回去,可惜我力气太小试了几次连一块儿都搬不起来,也不知现在那些青石还在不在了。
男孩子们喜欢玩踩高跷,就连妹妹都敢绑在腿上玩,我不敢,想着摔下来肯定是痛到龇牙的样子。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儿能变换好几种花样,一玩儿一头汗,却玩儿得非常开心非常有成就感,只有我在一旁为他们提心吊胆。他们说数我最像女孩儿,可我觉得数我最没用。
我们捅蜂窝、吃蜂蜜、掏麻雀、捉蛐蛐,还打死过一只蝙蝠,我当时认为那是世上最丑的生物了,还倒着睡,头不晕啊?每天不用自己去想跟着他们每天都有的玩儿,即使一个简单的游戏持续玩好几天都不腻都很开心。小孩的小小心里装不下感伤,每天被新奇好玩的事就装得满满的了,越长大心越大的空洞,怎么填都填不满,寂寞、孤独、彷徨、忧伤、迷茫便充斥在这些填不满的地方,让自己孤单的害怕。
每天特能吃,比在自己家能吃多了,一来姥姥家我就胖了,心宽体胖。可是快开学的时候还是很想家,很想爸爸妈妈。
上了初中后就再不住姥姥家了,而且去的次数越来越少,结了婚之后甚至几年才去一次,一来自己的日子一直过得捉襟见肘去了怕被众亲友笑话,二来小气的丈夫不愿把钱浪费在人情世故上,总是千方百计得阻止我和娘家人保持太亲密的关系。而且姥姥也不喜欢我丈夫,说他一个男人家太爱计较,拿不到大面上,谁家请都摆臭架子不去。让我很难堪,我也讨厌他这个样子,但被数落的是我。
那几年我也过得很心力交瘁,只沉湎于自己繁琐的悲喜故事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姥姥家给忘了,直到有一天,母亲打来电话说姥姥得了皮肤癌已病入膏肓时日不多了,我惊得差点扔了电话,怎么会这么突然?电话那头的母亲已经泣不成声了。
当我和母亲妹妹风急火撩的去看望姥姥时,映入眼帘的是更加破败的老屋。堂屋的房顶上有几处连瓦都没了,都能看见外面的蓝天,还时不时的簌簌往下掉土,它和姥姥一样老的好像随时会散架似的,看着真让人心酸。
周围都是新翻盖的大瓦房,姥姥家看上去与周围的环境真的是格格不入,一样过日子舅舅家就是扶不起的阿斗,有多少钱都不会规划,全进了二哥一家的腰包,有时真的很生舅舅的气恨他是否没长脑子,一点正事都不做,最起码你不留点钱修修这房子?你就不怕啥时房子塌了把老娘埋进去?一如既往的贫穷破烂,这就是姥姥苦守了一辈子的家,忽然觉得姥姥好委屈,从来没享受过好日子没过过一天好生活,人呐!苦难是漫长的,生命却是短暂的,怎样活才是最重要的。
为姥姥买了很多好吃的,都是她平时最爱吃的东西,可惜她什么也吃不下了,真的好懊悔,姥姥身体好的时候能吃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买给她吃呢?哪怕多来看望几次也好哇!可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后悔是最深的谴责。
她躺在炕头愈加得瘦骨嶙峋,孱弱的轻微呼吸着,总是处在昏睡的状态,面容却一直很安详。醒的时候很少,见到有人来很高兴,谁也认得,一点都不糊涂,牵强的笑笑点点头,连说话都吃力,很没精神,一闭眼就又睡了过去。脸上拳头大的患处不停地流着很臭的液体,周边还有很多的小蛆虫在爬着,一定很煎熬吧?我们时不时的给她擦着流下的液体,那么爱干净的姥姥却得了这样的病。她的孙女是她一手带大的用我的拔眉镊子不停的把小蛆虫夹下来,想让姥姥好受些。
后来母亲对我说姥姥是把自己活活饿死的,岁数那么大,自己上厕所都困难,更别提做饭洗衣了,女儿一个比一个离得远,没人照顾,活着就是受罪,还拖累舅舅大老远的常来送饭照顾。母亲和姨姨们给买的吃的就放在那里,她什么都不吃,让我想起了我的爷爷。穷人也许什么都缺,但有些穷人就是不缺骨气。
姥姥的家里脏得很褥子上都是土,被子都黑得发亮。姨姨们也都陆续赶来了,都没闲着收拾家给姥姥换洗衣服,母亲用剪子剪烂了姥姥身上穿的衣服,给她擦洗身子,瘦的每个骨头码儿都看的清清楚楚。母亲边擦边哭,我想她那时是很后悔吧?要不是我坚持她明天才会来,她一直不觉得这会是件很急的事,死是暂时死不了,但行孝就晚了。人啊,不看到结局,永不知后悔。
母亲和姨姨们留了下来,我们没地方住二嫂也没有要留的意思,就只好回家了。三天后母亲打来电话:姥姥去世了。我悲痛的眼泪流了下来同时吁出了一口气,对于姥姥来说死是一种解脱,对病魔的解脱,对贫苦生活的解脱,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早就不想活了。但愿她圣洁的灵魂升入天堂后会得到她从未得到过的所有。
上次去姥姥家,门窗换了,屋顶重盖了,地面也铺上水泥了,围墙也铲了之后涂得白白净净,雕刻精美的夹扇也被不成器的舅舅几十块钱便宜的卖了出去,没有了一点过去的痕迹,也失去了过去的感觉。母亲无限忧伤地说:“现在应该叫舅舅家了,不能再叫姥姥家了。”
前几天母亲去看望生病的舅舅,说是得了哮喘,儿女怕花钱就在小诊所医治。自己想去大医院查查手里没钱呐,人们又不敢借给他,借了就不还。在四姨那里存了几万块,可是因为地钱的纠纷,四姨把不该给她的钱据为己有了,真是阎王爷不嫌鬼可怜,连同大哥在她那里存的钱她也一并存在了自己的名下不给了。钱不是万能的,但钱却是最能看清人性的东西。相信人没错,但不能太相信了,人性是禁不起利益的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