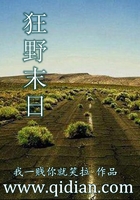时代的浪潮,总是在向前涌动着的。
有那么一些日子,田间地头、屋里院外、街头巷尾,时常有大人们这样的声音:
“听说,苦日子快到尽头了——”
“听说,有些地方已经分田到户了——”
“也该这样了,邓伯都出来工作了。”
“说来说去,就是那一句,不管黑猫白猫,捉得老鼠就是好猫。”
“以前的那些什么草啊苗啊,我可弄不清楚;我只知道,老百姓就是要吃饱穿暖——”
“让我们放开手脚,我就不相信会填不饱肚子?”
“邓伯都出来了,有盼头了——”
几年前,我年纪尚小,也不太清楚“邓伯”是谁;我只是很清楚地感受到,老百姓对他充满了信任与期待,有很深的感情。终于,那年春天,队里迈出了试探的一步:把整个队分成两个大组,开展为期一年的劳动竞赛。让人欣慰的是,人还是那些人,年终结算时,队里出现了盈余,超支一词从此成为过去。开春时,分田到户的大幕正式拉开了。尽管所分到的水田旱地、耕牛农具,极为有限,社员们依然是兴高采烈,真比过年还高兴。
由此,一头老黄牛进入了我的生活。这头老黄牛,有着山羊一样盘旋着的两只角,我们三家人也亲切地称它为羊角。一般情况下,三家人轮流看,每家一天。轮到我家时,一大清早,我和哥哥就来到队里的牛栏前,让羊角出来。其实,放牛也不是什么难事,大家多半都在同一时间赶牛出栏。于是,这富有灵性的羊角,三步并作两步,跟“大部队”去了。跟在牛群后面的,是人群。小街北面数百米处,是一大片连绵的群山,山脚山上早杂丛生,也就成了天然的牧场。来到山脚下之后,目送着牛群边吃草边往山上走,我们上午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可以回家了,只等着下午赶牛归栏。由于熟门熟路,傍晚时分找不到牛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只是每天走两个来回,放牛并不是什么苦差事。
如果碰到假期,时间充裕的话,你尽可以躺在山脚的草地上,仰望那蓝天上的白云,仙鹤般飘荡着;你的那一颗心,不知不觉中,也像飘到了云朵旁边,似乎只要一伸出手去,就能够摘下一片云彩的衣角。当然,当你觉得这一幕有些单调时,也可以面朝北边,目送着那一大片绿地毯,微微的斜斜的向前向上延伸着,与大山、更远处的天空,浑然一体。远望着这一切,你甚至会想起,说不定大山的某一个角落,还真的住着一个白胡子的神仙呢。
跟放牛相比,种田就没那么轻松惬意了。
哦,好几十天之前的那个夏日上午,我穿着一件白衬衣,挑着一担秧苗,向大田走去。
我们岭南地区,种的是双季稻,也就是平时所说的早稻晚稻,当地人也习惯说头苗二苗。大致上是这样的,每年清明前后,就开始育秧了。这专门用来育秧的那一小块水田,叫秧田。五一前后,就可以把秧苗全移到大田里。这就是插秧,街上人也习惯称为种田。为了赶上季节,在早到成熟前的二十天左右,要提前收割几分地,然后用这几分地来育二苗秧。因此,对于有几块田的人家,秧地与大田不一定就全在一起,也就是说,有些大田,是要把秧苗挑过去的,才能种下的。每年的七月下旬前后,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双抢时节。这双抢,一是抢收,二是抢种。不难想象,盛夏时节,才真正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候。
这个盛夏上午,从秧地到大田,是要走上一段路的。
“一天之计在于晨”,的确很有道理。自西向东走着的我,由于要面对太阳光,脚步也就说不上轻松二字了。当地人为了多种一两行稻谷,把田间小路(田基)弄得极为狭窄。在这种情况下,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到人家的田里看青蛙去了。于是,我压住脚跟,小心谨慎的走着,向着我家的大田。双肩隐隐作痛时,大田就在前面三四十米处了。
要到达目的地,先得路过杨卫东家的大田。
这杨卫东,与我家共有那头名叫羊角的老黄牛。巧合的是,两家的大田,也是连在一起的。其实,那本是一块三亩地的水田,他家分到了一亩七,余下的一亩三归我家。
我挑着秧苗路过时,他正在耙田。
本来以为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过去的,大概是这位叔叔要稍稍放松一下吧,他点燃一支香烟时,发现了我,接着就对我母亲说道:“梁嫂,你看,二公子来了——”
我心头一怔:这“二公子”,说的就是我?
我母亲望着手里的秧苗,回答道:“杨叔叔,这样的穷苦人家,哪有什么二公子啊!”
跟在母亲身边一起插秧的,还有我的哥哥,我的两个妹妹。
放下担子时,我的思绪却直往脑门上涌:这杨叔叔,怎么会叫我二公子呢?我排第二,又穿了一件白衬衣?又或许,他觉得我不像一个种田人。当然,他可能也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是啊,如果我都是公子了,那普天下的公子哥儿真要比天上的星星还多了。
我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那这样秒往田里走。
幸好,这是最后一担秧苗了。
杨卫东缓缓的吐出一口烟雾后,这才说道:“以后他读书毕业了,有工作坐办公室了,整天穿得整整齐齐的,不是公子是什么?”
我母亲边插秧边微笑道:“就算是这样吧,那,那也得下功夫读书啊。”
“读书的事情,梁嫂,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勤读书的人——”
“托你的福,但愿他以后读出点名堂来,不用再像我们——”
杨卫东淡淡一笑:“我们这一代人,面朝黄土背朝天,也够辛苦的了。”
“是啊,他们这一代要脱胎换骨,只能靠读书了。”
“如果时光倒流回十几年前,我也愿意下苦功读书了
“晓刚,听到了吗?要读书,就要懂得抓紧时间——”
我点点头:“其实,读书也是很累人的——”话一出口,我就有点后悔了:晒晕了吧,怎么说出这种不识抬举、没出息的话来?
果然,只听杨卫东说道:“读书累人?再怎么累,也比不上种田做活路累啊!你看,我现在一身是汗,衣服都可以扭出水来了——”
我尚未想出可以遮掩一番的话,母亲就说道:“现在不努力,以后会后悔的。”
说的很有道理,我点了点头,继续插着秧苗。
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觉得,小腿上有一种麻麻痒痒的感觉,且夹杂着一丝刺痛。觉得不对劲,抬起腿一看,天啊,一只手拇指粗细的蚂蝗,正贴在我的小腿上!
“啊——”的一声惊叫后,我连忙用手去扯;这家伙正吸得欢,已是竟然弄不下来。
我一咬牙,用力一扳,总算将这该死的蚂蟥弄下来了。
小腿上,多了一个比牙印稍小的口子。
只听西面正在耙田的杨卫东笑道:“二公子,今天早上你赖床了吧?”
我皱着眉头,迟疑道:“没有啊,今天早上,我起得蛮早的——”
杨卫东哈哈一笑:“没有?别骗我了,蚂蝗专门咬那些睡懒觉的人。不信?问你妈妈妈——”
我霎时反应过来了:这种话,根本就没必要问!既然被咬了,就自认倒霉吧。再怎么样,那边的杨卫东都可以这样说:你不睡懒觉,怎么会被蚂蝗咬呢?你看,我天刚亮就出门了,我可没被咬呀!蚂蝗,也会看人来咬的。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每过了两三分钟,我就会抬起脚来,看看小腿上有没有蚂蝗。
在我的严阵以待之下,蚂蝗,一时倒也没再来袭扰了;不过,还有比蚂蝗更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