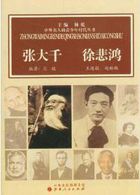狗熊不战而败,灰溜溜地逃蹿,小伙子们不再按喇叭,跳到路面上扯着脖子呼喊:“噢!噢!有种你别跑呀!噢!噢!”“妈了个巴子的!它也知道害怕!黑瞎子打立正——还想着一手遮天哪!噢!噢!跑啦!跑啦!是他妈的狗熊啊!”“哎!师傅!奇怪啦!盯着咱们这么长时间,怎么不跑呢?又不敢过来!黑瞎子这家伙,它怕过谁呀!这红石砬子,真他妈的见鬼啦!豹子皮吊了七、八天,光天化日之下,大黑瞎子又拦路,大概是想劫持咱们这两辆大汽车吧?”“嗯!没准!急了眼,火车它都敢截!铁力林业局,去年冬天,火车头,不是就叫它给拱住啦!司机一铁锹火炭,才把它给烫跑!真把汽车截住了,咱们还真没招儿呢!”“……”司机跑车,见多识广。尤其是这两台拉煤的载重汽车,昨天下午去鹤岗矿务局,今天头午装货返回。全天的时间三小时的路程。不急于赶路。
从牌照上就能看出来,西林钢铁厂的汽车。翻过野猪岭就到了金山屯。出金山屯第一站就是西林钢铁厂。柴拖拉又是大功率的,路上的车辆极少,畅通无阻,风驰电挚,一个半小时就到。所以司机们不急于赶路,没有黑瞎子出现,后面车上的老太太,还要在这儿烧香烧纸逗留,祈祷点儿什么呢!刚才是一场虚惊,这一下子就更有了话题。互相交流,也是说给宫本魁和赵长山听的。围绕着黑豹子和大狗熊,热火朝天,兴致儿特浓。其中还掺杂着感慨、愤怒、惋惜、痛心、惆怅和无奈。特别是第一台车上的大胡子司机,打着手势,有声有色,高兴之处哈哈大笑,愤怒的时候痛心又疾首。因为感情上崇拜,白话的时候还一口一个宫大校叫着:“宫大校您听说了吧?野猪岭那边,鸡爪子河林场。嘿!卫生所的大夫正给患者扎针呢!一头大狗熊‘哞’的一声就撞了进去。卫生所的窗户外面就是山坡,这黑瞎子,真它妈的狠啊!一口咬着大夫又一巴掌抢到了患者的屁股上。患者急了,嗷的一声就跳了起来,拼命呼喊:‘救命啊!救命啊!黑瞎子来啦!黑……!’第二声‘黑瞎子’没出来,狗熊的第二巴掌又抓了下去。患者的屁股被撕开,轱辘到床下才捡了一条小命。大夫当场就让大狗熊给咬死了,多亏卫生所隔壁就是生产调度室,一帮子现场员、检尺员、调度员、生产场长正研究工作呢。听到喊声就奔了出来……
可是晚啦!大夫活生生地给咬死了,大狗熊破窗蹿到了山上。等众人赶去,连个影子也没有看到。“妈了个巴子的,这黑瞎子,是真他妈的狠啊!一伤一亡,眨眼就没影啦!开天辟地,小兴安岭林区,大姑娘生孩子,这可是第一次啊!赶巧我拉煤回来,把患者拉到了林业局医院,快半个月了吧?听说至今还在病床上趴着哩!弄不好,出院也得残废啦!老婆孩子,可怎么办啊!啊?不是公伤,私伤公家又不管,林场的头头都没有办法。家家街门紧闭,大白天街上都不见人影,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啊!啊?今天更悬,看见了吧!咱们这么多人,它还不怕呢!你看那小眼,死盯着咱们,看架势,不咬死几个,它是不带罢休的。这不是亡命徒嘛!就是枪漏子,胆儿也没有这么大吧?这家伙,不信就试试,杀了它,晒干了的熊胆,也得有倭瓜这么大。明子你不用笑,没有倭瓜大的胆子,这么多人它就敢叫号?宫大校,您说是不是?老鹤林的炮手,枪法再准,没有狗护着,单崩儿也不敢照量它吧?“还有,刚才那两声枪响,大概其,我揣摸着,也是冲着这老家伙来的吧?怎么没有动静了呢?黑瞎子跑啦!炮手们也该出来了吧?”说着,大胡子司机昂首挺胸地往道南沟里面撒摸着。林木葱葱,重山叠嶂,眼睛再尖他又能看到什么?宫本魁心情沉重。久病初愈,久站两腿也有点儿酸溜溜的。想坐下休息,周围又没有合适的地方,只能点一支纸烟,一边踱步一边在思考。他是队长,管理猎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还有大胡子司机刚才说的,岭西对外开放鸡爪子林场的悲惨故事。谁敢保证,蹿进卫生所,咬死大夫咬伤了患者的那头大狗熊,就不是刚才的这只黑瞎子呢?如果是刚才的这只黑瞎子,我宫本魁就更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啦!七鬼峰之行,就不仅仅是一只枪漏子了,还有负了剑伤、拐走中正剑的小豹崽,救它逃走的母豹子。山顶上推下石头来的黑豹子,金钱豹都报复社会,林区不是就乱套了嘛!行政上自己是狩猎队的一队之长。可是,七鬼峰之行的枪漏子,自己那可就是始作甬者了。噢!他忽然明白了。头上这两张悬挂的黑豹子皮,是个象征。象征着野生动物们的指挥权,标志着同盟作战的号令与旗帜。毫无疑问,为了抗议和报复人类,猛兽们已经离开了自己的穴巢和根据地,以居民点为目标,同时出击,玩命儿地反抗。威胁它们的头号敌人是狩猎队,由灰蜘蛛帮忙,黑豹子皮就挂在你狩猎队的家门上,豹子皮不摘,报复就不会停止……
老豹子!好阴险、好顽固、好残忍,也好霸道啊!久闷着的心情,再看红石砬子顶上的两张黑豹子皮,宫本魁的思维忽然就裂开了一条缝。通过缝隙,窥视到了真相!秋天,天上没有多少白云,阳光始终在尽着它最大的努力,给兴安岭以温暖,给大林海以详和。大狗熊逃走,汽车熄火,野猪岭地区又恢复了它的宁静。没有杂音,除了树叶的摇晃,流水的潺潺,就是有两只老鹰,耐着性子在南沟的高空处盘旋。一圈儿又一圈儿,它们发现了什么还是在寻找着什么,翅膀扇动,一会儿又挺直,看样子是刚才那只大狗熊活动的地方,灌木丛下面肯定能有遗物。宫本魁扭过了头去,他对两只雄鹰不感兴趣,他关心的是这两张黑豹子皮,用肉眼观察,努力想找到它更多的破绽。对他而言它们早已经不是一般的野兽皮了,是珍宝,又可能是魔鬼。是魔鬼还是珍宝,只有进一步研究,通过观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老太婆又到第二辆汽车的屁股后面烧香去了,还是面对着那两张黑豹子皮。有惊无险,一场虚惊,此刻她仍然是那么虔诚,仍然是那么执着,一丝不苟,小心翼翼又全身心地投入。跪在路边,先燃烧香纸,又极缓慢地在叩头,闭着眼睛,一边叩头一边又开始了祈祷。司机是理解她的,茫茫林海,山峦叠嶂,不是迷信,可也得求个吉祥吧!
听说自己是宫本魁宫大校,第二个汽车的司机,那个秃头、长脸、大下巴的中年汉子,非常斯文地慢慢踱了过来。先是一笑,露出大板牙,可能是不善于交谈,与大胡子比较,性格和脾气也恰恰相反,无声地一笑。笑完了才不自然地摸了一下自己的秃头,再次一笑才眯缝着眼睛小声儿说道:“噢!您就是宫大校啊!久仰,久仰啦!鄙人金永基,也去过朝鲜,在国外,您的名字就如雷贯耳啦!”听说是战友,宫本魁刚要伸手相握,但这位叫金永基的驾驶员却把双手缩了回去,改变姿势,抱了抱双拳,脸上的表情也是自卑和尴尬的,再摸了摸头皮才又讪笑着,而且是小心翼翼地说道:“宫大校!虽然我也参加了志愿军,可是我和您,可不敢比啊!您是老抗联战士啦!我可是被俘虏的‘解放军’啊!就因为这点儿技术,政府才……嘿嘿嘿,怎么敢和您相提并论呢!是不是,宫大校?”说完,尴尬地笑着,又摸了一下头皮。似乎是秃头上有老多逮不净的虱子。金永基把伸出来的大手又缩了回去,摸着脑袋,自卑又矜持地笑着,宫本魁就明白了。
金永基曾经是国民党的汽车兵!或者投诚,或者是被俘,后来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联军,再后来又出国参加了志愿军,如今是西林钢铁厂汽车队上的技术骨干。跑运输,带徒弟,埋头工作,但说话处事却非常地谨慎,唯唯诺诺,谦虚又小心,怕有闪失,招来横祸,不像前面车上的大胡子,声若洪钟,直来直去。两位司机尽管在年龄上差不多,可是性格和言谈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位坦荡、豪放、耿直、粗鲁,另一位却木讷、迟钝、内向又谦卑。想到这儿,宫本魁理解、同情又温和地小声儿问道:“金师傅!前两天是您的车,在道北扣了兜子吧?”说着,他用左手指了指道北公路下面的那个大坑。坑里面灌木丛狼藉,杂草被碾平,油污把沙石染黑,翻车与自救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
大坑是盘子形的,大坑的两边,一边是路基,另一边就是红石砬子,砬子顶上的两张黑豹子皮,在秋阳下面,依然是悠哉悠哉地晃动着,除了悲凉更多的是得意。似乎是嘲笑又仿佛在威胁:“宫本魁,怎么样?我可是在这儿等你七八天啦!……”瞅着豹子皮,恍惚间听金永基说道:“宫大校!我金永基是老司机啦!在这条道上,也跑了六七年啦!可是……唉!怎么说呢!星期三那天,瞪着眼珠子,清清楚楚,就翻了下去!我还以为转向系统失灵了呢!可是,细一检查,是啥事儿没有啊!您说,宫大校!怪不怪呢?给共产党开车……啊?我金永基开天辟地,这可是……第一次啊!在朝鲜,那盘山道,陡不陡?咱金永基啊,宫大校……老母亲都跟着,不放心啊!来回跟着押车,这不是……这一疙瘩怎么就,老翻车呢?宫大校,您说?”说完,他又情不自禁地摸了摸秃头,似乎还有虱子,在秃头上爬行。
“你注意力不集中,就翻车了呗!”宫本魁不以为然地答道。说着,顺手把独筒儿望远镜揣了起来,尽管心不在焉,可是,他的两眼仍然死死盯着那两张黑豹子皮。接着宫本魁的话茬儿,大胡子也开腔了,甩着大巴掌,眉飞色舞地说:“宫大校说的没错,金师傅你就是胆小,眼睛老往山尖上撒摸,来时又是下坡,心里头一慌,就翻了下去。这野猪岭啊!都他妈的是诸葛亮的空城计啦!孔明弹琴,吓退了司马懿,你金永基可好,两张破豹子皮,在树尖儿上挂着,就吓得你毛了爪。如果是活豹子!还不得屙一裤兜子!方向盘在你手上把着!嘁!疑神疑鬼的,还有脸在这儿白话呢!老驾驶员了,厂部没处分你,就算是烧高香啦!宫大校你说,是不是这码儿事?”话没说完,徒弟小胡子就尖着嗓子喊道:“看!看!他们出来啦!出来啦!还背着只傻狍子哩!刚才打枪,肯定就是他们!这些散仙,把山里头闹得是鸡犬不宁啊!”“宫场长!你看你看!”赵长山也饶有兴趣地牵着马缰绳说道。
路南路北,听小青年咋呼,宫本魁的目光就从道北山尖豹子皮上收了回来,包括其他人也都把目光情不自禁地转移到了路南,盯着一行人,从沟里的密林子深处,不紧不慢、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一条沟,沟塘子不宽,刚才那只大黑瞎子是沿着东山根,而这一行人是在西山根,踩着塔头,绕着树棵子,三人背着两支单筒儿猎枪,走到跟前,大伙儿才看到,其中那个矮粗胖的小伙子,肩膀上背着一只猎物,气喘吁吁,趔趔趄趄的,猎物屁股冲前脑袋在后,开始还以为是只傻狍子哩!走到近前,大伙儿才看清楚,他们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猎杀的竟然是一只梅花鹿!一只母梅花鹿,揣了崽子,即将要分娩。这个月份,是所有雌性梅花鹿的分娩季节。辨别出是一只母梅花鹿,宫本魁大张着嘴巴,眼珠子都直了,他后退了两步,情不自禁地、也是下意识的,虚弱的身体,差一点儿就栽倒……“梅花鹿,白瞎啦!”大胡子的徒弟——小明子惋惜中感叹着喊道。“唉!奶奶的!缺德带冒烟的,王八犊子!就能下得去手!”大胡子司机低声地、忿忿地、拍着大腿根儿吼道,“没规矩喽!小兴安岭,完喽!完喽!用不了两年,就得绝根哪!”“可不咋的!猎公不杀母,猎杀母鹿,这是犯罪哪!”金永基也心疼不已喃喃着喊道。
宫本魁始终没有言语,看着滴血的母鹿,因为心疼,他全身都在颤抖。他不是局长,也不是附近地区的行政领导,可他还是场长,野猪岭鹿场的场长,尽管被开除了党籍,眼下他还仍然兼职中心狩猎队的队长,队员滥猎,他有权制止,可是这伙人,都是从山外来的难民啊!没组织,没领导,随意捕杀,除了公安部门,别人是无权来制止或干涉的,看着他们三人走近,宫本魁刚要张嘴,询问他们是哪个林场的,可是没等他发话,牵着马缰绳的赵长山就气哼哼地喊上了,居高临下,对着草甸子中的三个人问道:“你们是哪儿的?乱捕滥猎,懂不懂山里的规矩?猎鹿犯法,你们知道不知道?”赵长山理直气壮,一手掐腰,一手晃动着马缰绳问道。白龙驹也瞪圆了眼珠子瞅着他们,梅花鹿的血腥,使白龙驹嗅到了一种异常的气味。三名猎手到了近前,沐浴着秋阳,宫本魁清楚地看到,三名猎手一色儿是农村打扮,持枪者岁数在三十岁上下,两支猎枪,其中一支是老套筒子,锈迹斑斑,都怀疑能否打响。另一支猎枪却是新的,枪筒乌亮,紫红色的枪托闪烁着一种诱人的光泽。这么新的猎枪在狩猎队也少见。
购买猎枪需要公安部门的证明,猎枪出厂也都是统一编号的,持枪要有枪证,尽管是民用枪支,公安部门也管理得很严。难民进山,多数是下套子,支拍子,挖鹿窖,用大斧头劈,持枪猎捕,林场、作业所、居民村屯,也是有数的那么几家。持枪者不是场长的小舅子,就是村长的表叔二大爷,有靠山和后门儿,才有恃无恐在林区横着膀子晃悠。果不其然,肩背新猎枪的高个儿黑瘦子眯缝着小眼,盯着汽车,抖了抖膀子,大咧咧满不在乎地亮着嗓门儿说道:“岭西,丰沟作业所的,哟!嘿!这不是金师傅吧?金师傅!今儿个还是搭您的车呀!给您只兔子,您瞅瞅,肥着哪!”边说边嚷边咋呼,边从背老套筒子的黑脸汉子的猎包中掏出来一只带套儿的死兔子,右手扬着,三分炫耀七分都是巴结:“金师傅!七八斤哪!你瞅瞅多肥!”说着,一使劲,“嗖”的一声就扔了上来:“金师傅!你接着!”一只兔子,既是礼物,也是三个人搭车的票钱。“哈哈哈!金师傅!咱们是缘分哪!啊?刚一出沟,我一眼就看出来,是您的车呢!”
年轻小个儿也有二十多岁。“噗嗵”一声把死鹿扔在了草地上。用满是鹿毛的手背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然后也一屁股坐在了塔头上。山东腔,大黄牙。坐下后又伸了个懒腰:“胁他娘的,远路无轻载啊!”喘了口粗气,又笑着说道:“胁他娘的!这大白马!好威风噢!”忽然一愣,似乎是发现了什么又意识到了什么。抓着杂草就站了起来。他目光盯着大白马和左手牵着马缰绳的赵长山,皱着眉头,严肃、地虔诚又渴望般地喃喃说道:“老天爷!你们,是不是,野猪岭鹿场,宫、宫大校一、一伙儿的呀?”低头看了一眼死梅花鹿,声音更低,也是有点儿无可奈何地,不仅仅是歉疚,更多的是惭愧,黑手揉摸着猎服上的污血处:“唉!本来嘛!这只梅花鹿,套着对儿还没死哩!可是,俺们都听说,宫大校,没工资啦!鹿场没钱收购!逮着活的,国家也得放掉。于是就……就……给了它一刀……唉!胁他娘的!实话说,也不忍心啊!本来下套子的时候,是打算套活鹿,卖给鹿场的宫大校的啊!可是!唉!奶奶个熊,嘛也别说了!”说着,有泪花就滚落了下来,半是哽咽半是乞求:“老哥!你不说犯法!这么好的母鹿,捅死啦!俺心里头也,也觉着不对劲儿啊!”说着,竟然呜呜地哭出了声。死梅花鹿和小伙子的哽咽,使所有在场的人,心里头都觉着沉甸甸的。梅花鹿是食草的吉祥动物,更何况摆在大伙儿面前的又是一只揣了崽子的母鹿,母鹿死了,崽子也憋死了,一刀捅死了两条性命。目睹死鹿,谁心里不觉着疼痛又惋惜?可是眼下,在小兴安岭千沟万壑的密林深处,处处枪声,遍地都是套子。饿疯了的难民,进山就是为了猎杀,填饱肚子是第一使命。
梅花鹿死得再多谁又能站出来干涉?良知和道德,首先得摆脱了饥饿,才能用其来衡量标准和素质。灾荒年代,据说还有人吃人的消息呢。相比之下,猎鹿吃肉,众人也是能够容忍和理解的,特殊年代嘛,道德与良知,当然也得用特殊的标准去衡量了!秋风吹来,满山的树叶哗啦啦地齐响。时间还早,太阳不动,似乎钉在了小兴安岭的上空。阳光灿烂,但不能驱散每个人心头的阴影。鹤伊公路的两头,从老鹤林到野猪岭,路边四野仍然是那么静悄悄的。宫本魁走下路基,步履蹒跚,心头仿佛堵着一团烂梅花一样,憨闷难忍,可是又说不清楚主要的原因。鹿场的场长兼狩猎队的队长,目睹死鹿他心里好像是一滴滴地在流血。可是,他没责备他们,只是弯下腰,伸出大手,在光滑又亮丽的绒毛上,从脖颈、肚子到大腿处,来来回回,用手心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抚摸着……没有埋怨也没有叹息,只有浑浊的泪花,在他布满了皱纹的眼角上,一闪一闪地在晃动着……
老鹰在头顶上盘旋,乌鸦在最近的山头上哀叫,也许它们盯着这只梅花鹿已经老半天了。而且受饥饿的驱逐,从大山深处一直跟踪到了公路旁边。尽管公路上停放着两台大汽车,还有熙熙攘攘的人群,难民的猎枪也在时时刻刻地威胁着它们,但老鹰和乌鸦却不打算躲开,除了哀鸣,贪婪的目光仍然分秒不误地盯着。为了生存,人与猛禽也在潜伏着一场刀光剑影般的危急。司机金永基不声不响,弯腰拎着死野兔脖子上的铁丝,脸上挂着笑容,冲大个子点了点脑袋,返回自己的汽车,打开车门,塞进了驾驶室内,面对饥饿,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食物才是最亲密的朋友。金永基的老母亲过来了。看着死鹿,昏花的目光立刻就亮了,但很快又暗淡了下去,皱着眉头,嘬着嘴角,以老太太特有的诧异和善良,手捂胸口感慨中在不停地诅咒着:“啧啧!老天爷!造孽啊!啧啧!老天爷,造孽哟!还有孩子哪,火辣辣的,您就敢下手!您就敢下手?造孽呀!老天爷,啧啧……”忽然有黑瞎子的吼叫声传来:“欧——欧——欧——”是刚才逃走的那个老家伙,方向离老鹤林不远。大概是遭遇到了炮手们的围攻吧?突出重围,仓惶中一边逃跑一边在一声声地吼叫着,开始还在正东的方向,几分钟就越过了公路,与七鬼峰接近,变正东为东北。苍凉的吼叫声也越来越冷,但始终没有听到枪声。逼它逃走的,也可能是其他的猛兽,大狗熊腹部的伤口至今没有痊愈。发生冲突,选择逃走是它的聪明之举。
宫本魁辨别着熊吼,暗暗思索着。听到黑瞎子的叫声,大伙儿的情绪很快由悲哀转换成了喜悦。七嘴八舌争相评论着:“妈了个巴子的,听动静,是在狼狈逃蹿啊!”“可不,懵头啦!哪儿是狩猎队,老母猪进耙场——找着挨打!”“不对吧?没听见枪响,也没有狗咬,十有八九是遇上了大孤猪。大跑卵子可凶着哪!”“没准儿是黑豹子呢,争夺地盘,野兽之间,也是寸土不让啊!”……议论起这只黑瞎子,肩背新枪的黑瘦的大个子顿时就来了精神。大手比划着,两眼贼亮,黑脸上的表情却布满了疑惑。瞅着大伙,略有恐惧地亮着嗓门儿说道:“嘿!师傅们!这只黑瞎子,简直就是神啦!我下的套子,有狍子套,也有黑瞎子套,半个月以前,我就发现一只大狗熊,在阳坡的水沟旁边活动,走路拉拉腿,叫唤的声音也不是很大,我就琢磨,奶奶的,肯定是受伤啦!受了伤,就是枪漏子,得赶紧想办法,把这只枪漏子勒死。前两天在鸡爪子林场卫生所,听说也是一头受了重伤的枪漏子,咬死医生,抓伤了患者。逃走后下落不明,发现了枪漏子,我就敢肯定,这家伙,别看它走路拉拉腿,叫唤起来声音不大,可是它太狡猾了,听见动静,马上就藏到了一棵红松树的后面,把身体遮起来,然后才把熊脑袋探了出来,四处撒摸,寻找要报复的目标……这头狗熊,好狡猾,也好阴险啊!不是枪漏子,低级动物,能有这么多的心眼?不行,这老家伙是祸害,得想办法把它处死。不然的话,上山采蘑菇、捡木耳、拾松籽,老婆孩子,还要吃它的大亏哪!回家后,我就叫上了小山东和二驴子,带上家把势,埋伏上了几十个粗套子。我宋宝山干别的不行。下套子,百分之百,秃头的钉子——绝对没帽。
不出半个月,套不死,也得勒昏啦!钢丝绳,指头这么粗,想挣断,没门儿!“嘿!奶奶的,今日个我们来一看,顿时就傻眼了!我们下的是活套子哪!两米长的柞木,比大瓷碗的碗口还粗。下套子,咱不外行,不是忽悠也不是白话。金山屯一带,谁不知道咱宋宝山啊!老鹤林有宋丽萍、宋丽娟,都是我们老宋家的,她们打枪,百发百中,我下套子,小兴安岭一绝,不管是狍子套、狐狸套、野猪套、兔子套,还是黑瞎子套,支土套子,就能手到擒来。碰巧啦,哪天不套个十只八只?猎枪和猎物,都不敌咱的套子好使呢!这下子完了!二十年了,今日个碰上了黑瞎子精,宫大校、师傅们,与野生动物打交道,我宋宝山这也是大姑娘生孩子——头一遭啊!”
听说是黑瞎子精,大伙儿都把耳朵支愣了起来,张着大嘴,听这位自称是宋宝山的猎民,讲传奇的、惊险的、套黑瞎子的猎奇故事,黑大个儿挺能白话,卸下来猎枪,眼瞅着大伙,咽了几口唾沫又接着说道:“山里人都知道,套大的山牲口,不仅仅是钢丝绳粗,还有,不能下死套子(死套子就是拴在粗树上的那种),山牲口力气大,皮厚骨头硬,时间长啦,死套子就容易拧断。这玩意儿,可不是傻狍子、梅花鹿什么的。挣扎几下子,越勒越紧,就伸出了舌头,山里的猛兽,不管是黑瞎子,还是大孤猪,套住了,三天两晚上也死不了。一旦把套子拧断,就变成了山里最大的祸害。报复性强着哪!所以呢,这些年,大伙儿就琢磨着下活套子。小颈木,一米半长,野猪、狗熊,套住了就拖着小颈木跑。挣不脱,甩不掉,还勒不死。有时候就跑出去几十里,围着山头转。
钓鱼一样,得悠着劲儿来,着急了鱼线就能挣断,等它折腾够了,气尽了,再一点一点地收纲,大鱼就能够拖上岸来。套黑瞎子也是一样,它拖着小颈木满山跑,林子密,挡住了它就挣扎,挣脱这一个树桩子,下一个树桩子又把它拦住啦!用不了三天,就能把它的蛮力耗尽,到那时候,再刀劈斧砍,结束它的性命。“可是今天我们三人来一看,嘿!奶奶的,黑瞎子成精啦!备不住你们还不相信呢!这头黑瞎子,脖子上挂着套,小颈木在它肩膀上扛着走。悠哉悠哉,是嘛事儿没有啊!你说说,这家伙,这不是成精了嘛!不是亲眼所见,说死了我也不相信啊!黑瞎子扛着小颈木走!还有更绝的呢!见我们来了,老先生竟然把套子褪了下来。嘿!奶奶的!粗铁丝套,没费事,两只巴掌托着,就把套子给松开了!当面又扔在了地上。大摇大摆,你说它气人不气人吧!成精啦!成精啦!真的成精啦!“黑瞎子没套着,这只梅花鹿,却当了它的替死鬼,钻了套子,活活地给撸死!唉!该套的,漏了网;不该套的,却送了命!本来嘛,这只鹿还没死,套子太粗,可是逮住活的,又卖给谁呢?鹿场不收,听说宫大校停发了工资,没有办法哟!就别说良心不良心啦!填饱肚子不饿,才是正格的哪!”黑瘦的大个子说完,冲着刚才黑瞎子叫的东北方向,摇了摇脑袋,很长很长地舒了一口粗气:“唉!黄鼠狼子钻烟囱——逼急了眼,没法子哟!”
黑瞎子的故事讲完了,但大伙儿仍然在深深地思索着,琢磨着,品味着,也回忆着大棕熊从面前逃走的过程。是的,确实是成精了,这么多人,还不急于逃走呢!直到两台大汽车的喇叭同时被按响,才慌慌张张、跟头儿把势地顺着河沟子逃走。逃到老鹤林,又逃往了七鬼峰,毫无疑问,这只受了伤的棕熊,肯定是前些日子七鬼峰之行,受了重伤的那个大家伙,鸡爪子林场卫生所的案件,可能也是这家伙所为。在野猪岭地区,不是它又能是谁呢?想到这儿,宫本魁直起腰来,看着自称为宋宝山的黑大个子,不动声色,轻轻地问道:“黑瞎子的伤口处,你看见了吗?”“没错!绝对没错,不信你问问他俩,走路拉拉腿,肚子下面的伤疤,有半尺长哩!”宋宝山持枪肯定地说道。“伤痕是不小,我亲眼看见啦!现在我还觉着奇怪呢!不是枪伤,生殖器咋没啦!”持老套筒子猎枪的矮胖子补充说道。“俺娘哎!可吓死俺啦!就在河沟子那沿,俺眼瞅着它褪下的套子!”小山东子休息了过来,可是面孔上的表情仍然惶惶的,心有余悸,眼睛都不眨,瞪着眼珠子说道:“他俩有枪,俺可是空着手啊!黑瞎子真若奔了过来,他俩自卫,我哪!不是干等着送死?……这功夫啦,想起来,心里头还突突地跳哩!”小山东瞅着东北方向,心有余悸地一个劲儿叙说着。
从关里到关外,第一次进山就碰上这头魔鬼,没有吓死却大开了一次眼界。在小兴安岭,即使是炮手,类似情况,也是极为罕见的。遇到这只魔鬼,大难不死,有惊无险,也算是小山东自己的福份。宫本魁认真地听着,内心感慨,想法也很多,毫无疑问,这头受了重伤的大狗熊与自己有关,与野猪岭有关,与狩猎队更是有关。可是,尽管大伙儿议论纷纷,关于内情和底细,宫本魁却一个字也没有吐露出来,七鬼峰之行,说不清的怪事太多了,不说那挺歪把子机关枪、死而复活的野猪王,眼前的两张黑豹子皮、肆虐报复的大狗熊,吐露了出去,社会上的谣言就会更多,谣言多,于政治局面和林区生产是极为不利的,自己是大校,稳定人心而不能去添乱,就是七鬼峰上行的一系列真相,首先得向党组织和政府的有关部门汇报,待政府部门派科学家勘察出了真相,自己再宣传,为时也不晚,想到这儿他平静地说道:“枪漏子不怕,最怕的是滥捕乱猎,乱砍滥伐,树都砍光啦!在自然灾害面前,老百姓,就更是无路可走啦!相比之下,枪漏子再凶,对林区社会也构不成威胁,你们想想,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儿道理?”话音刚落,大胡子司机就赞成地附和着说道:“宫大校,你言之有理啊!可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砍树,工人就得失业。不套野猪,就没有肉吃。都是从农村来的。”他用手划拉了一下刚出沟的三位,尽管反感也微略有点儿同情,“不弄点儿野味,老吃橡子面,不得把人给吃死啊!”忽然,有隐隐约约的汽车声传了过来,是老鹤林方向,大胡子就匆匆忙忙地喊道:
“走啊!休息的差不多啦!你们几位坐我的车吧!我不要兔子,白拉着你们哥们儿几个?”说着,目光再次在死鹿身上扫了两眼。“哪儿能白拉呢!见见面还分一半哩!”宋宝山左手抓枪,右手和小山东抬着死梅花鹿,爬上路基,扔到车上又补充了两句:“下车给你条大腿,常来常往,以后还指望坐您的车呢!打围的人,还兴吃独食?!”说着,踩着车轱辘,三个人纷纷地爬到了煤车上。汽车发动了。挂档起步,大胡子又探出来脑袋,按着喇叭打招呼说道:“宫大校,再见啦!再见啦!”汽车扬起来一阵灰尘。隆隆响着往野猪岭上爬去。第二辆汽车上的金永基仅仅是按了按喇叭:“笛!笛!”大下巴微颤了两颤,一声不响,载重车就隆隆地开了过去。他的老母亲坐在当中,满脸虔诚,似乎仍然在祈祷着什么。宫本魁告诉赵长山:“走吧,咱们也回家!”骑到马上又扫了红石砬子的山尖上一眼。
和熙的阳光下面,伴随着微凉的秋风,两张黑豹子皮缓缓地摇摆,似乎是提醒着这个社会,又仿佛用无声的语言在叙说着什么。事态的发展与宫本魁想象得一模一样。悬挂着的黑豹子皮,就是两面不倒的旗帜,指挥同类,向林区社会一次又一次地袭击。就在宫本魁离开了红石砬子的第三天。光天化日之下,两只马鹿王子的标本不翼而飞,精神病略有好转的陈桂兰,被黑豹子咬死,尸体横陈一号圈的门前。更令人恐怖的是,悬挂了十一天的两张黑豹子皮,仿佛被大风忽然间吹走。无影无踪,从这个世界上彻底地消失了。野猪岭再次遭袭击,宫本魁被迫向七鬼峰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