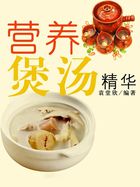转回正题。
赵弃被接了回来,一直昏迷着,脸色苍白,全身冰冷,兄弟三人给他盖上被子,却见虚汗从耳鬓渗流出来,整个身子是不停地微微颤抖。孙执给他紧了紧被子,用毛巾拭擦虚汗,安慰的说道:“四弟,睡吧,睡一觉就好了。”
整个屋子安静极了,大家都不做声,也没有人说要去请大夫,大家都明白,他这是心里紧张放不下,他怕睡着了,那刑场上的一幕如电影般地在脑海中反复回放,亲人的撕心裂肺响彻耳边。虽然即便他醒着,依然逃脱不了梦魇环绕,但至少不会于平静中一声厉问如贯天而降,惊悚起每一根寒毛。
寂静……死一般的寂静……
赵弃的脑海里浮现出父亲竭嘶底里的声音,“呸!你这妖孽不配与我同死!”,“枉我这一世英名,怎能与你同台行刑?”,赵弃只知那时候没敢去看赵蓦一眼,或许在他人看来这是赵蓦的薄情,而他却深深的感觉到了父情沉重的关切与哀伤。
孙执用毛巾拭擦了一下赵弃额头的汗,那动作很亲切,让赵弃如沐春风……
他看了,一片苍白中,慢慢浮现出的夫子宴,凝目注视他大吼道:“你不叫宴弃,你就叫弃,单名一个弃……有名无姓者……”,那神情让他感觉到威严,又让他感觉到亲切。他一度揣度,自己就是个被世事所弃之人,无颜苟活于天地之间,可夫子宴又偏偏是夫子,夫子不得不诵《诗经》,讲《道德经》,讲《周礼》,可又偏偏是夫子让自己学而有惑。
朗朗的书声传来,那是夫子的课堂,“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是呐,“维桑与梓”,多少个梦里,自己是睡在自己家门前的那颗粗大的桑树上,知鸟嗡鸣,喜鹊跳枝,熟透的桑葚掉落一地……
“咎,我念你一向为人耿爽,敬你三分,你却灭我大义,成就你之假仁假慈?你且记住,你这不杀之仇,我定铭记于心!”,他又忆起自己那愤恨的眼神,连他自己都不知为何要如此痛恨余咎,明知道余咎是出于好意,却无法控制住自己,他明白自己的愤恨简直可用“无理”来形容,却宁愿就这么任性地无理。
他已经准备好了,当那的钺刃落下的时候,只需一瞬,自己的梦想就要达到了。纂刻着蟠虺纹的钺背神秘而冰冷,在他看来却是如此亲切。这一切,都被余咎给中止了。赵弃是痛恨余咎的,那是真真切切,发自肺腹的痛恨,却又不知该如何去痛恨。
他又想起了父亲、母亲、妹妹……此后,何去何从?命运不由得他们去安排,只不得不被命运驱使着……他不想去想,也不敢去想……
尹冲撩腿侧坐在门口的台阶石上,眼睛盯着屋檐落下的水滴,跌入渍水中荡起的涟漪,一言不发。在他心头,始终无法言表的是对赵嫈的情感,始终觉得内心深处对赵弃、赵嫈兄妹深深的欠意,尽管先前对赵骞的揶揄之辞尽出自于公孙单的计谋,但丝毫也无助于他减少心中的亏欠。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在尹冲的眼里,赵嫈是那个背着竹筐,雀跃在山涧采着卷儿,哼着小曲的姑娘。他也曾凝目远视过赵嫈纤弱的背影,心头潺潺,有女如此,如何能不动于衷?远望而去,已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如何深想?
那时,公孙单却告诉尹冲,赵蓦此番出行,凶多吉少,边境摩擦不断,赵国国强兵广,现已战气勇溢,赵蓦一代名将,是要以忠烈告慰国门啊,最好的结果也是吃了败杖而回,你越是与之前往,他那傲气越是上涨,正是因为那份自恃才放不下面子,不肯认儿子,必须要打压一下他这份自傲。正是有此番说辞,尹冲才听从公孙单的安排,现在事态发展至此,想来公孙单内心也不会好受。
尹冲微微瞥了公孙单一眼,只见公孙单也是步履深重的来回踱步。
赵弃是活着回来了,按理说,这应该算是胜利的一仗,比预想中的结果好太多了,可公孙单看着兄弟们的表情,自己竟然没有丝毫的成就感,这气氛,比当初听到榜文消息时还要糟糕得多。
“我公孙单算尽天机,搅弄时局,把玩人心,如今四弟与家父虽未正式相认,可那亲情切切已不言而喻。我猜得了开头,却算不出这结局,人命是救了下来,父子隔阂已形同虚蛇,可我却诛了这帮人的心呐!”公孙单想。
这赵弃如今的状况看来,那赵蓦自是好不到哪去,邳氏已在刑场昏厥,赵嫈此刻又当如何?想到这里,公孙单禁不住的瞟了一眼一言不发的尹冲,二人双目对凝片刻,又各自陷入沉思。
公孙单看看此刻的尹冲,满心地愧疚。望着赵弃,又痛心疾首。再望了望三弟孙执,心中一下子静了下来,略作沉思,缓缓地说了句,“三弟,还是请你出面跑个腿,你且前往殿前打探一番,只管在门口盯着,我估计这大夫孙桓,丞相余咎已经前往,你再差人去府尹打听一下,我估计府尹也不在府上,若时至日落,这三人中有两人都没有出来,则无忧,若三人都出府来,定会忧心冲冲,你即可回来告知,我们可能需亡命天涯了。”
“好,我这就前往。”这孙执倒也不问原由,只觉得二哥所说,定有其理,生怕耽搁,马上起身出门。
尹冲听到此话,起身走了过来,“二弟,此话怎讲?”
公孙单一脸严肃,却也没回答尹冲,沉思片刻,向尹冲伸出右掌,示意其稍停,说道:“大哥容我梳理下思路,我有些混乱,暂时不知道如何向你说明。”
话说那丞相余咎,从刑场上走出,便没有乘轿子,一路缓缓而走,不是去朝堂,而是回到了丞相府邸,也没和家人打个照面,只与家宰诺了声,便回屋脱了衣衫浸入浴盆之中,将整个身子埋入到水里,直到再也摒不住气,才将头露出水面,一副呆滞的目光望着屋顶的那两片透光的琉璃瓦。
“咎,我念你一向为人耿爽,敬你三分,你却灭我大义,成就你之假仁假慈?你且记住,你这不杀之仇,我定铭记于心!”,赵弃这话是一路上回旋在余咎的脑海里。
“假仁假慈?”,余咎反复的念叨着,想着赵弃那愤怒的眼神,似如看穿了连自己都不曾看穿的,自己的那颗“虚伪”的心。他反复的思索大夫孙桓离去时的那眼神,那眼神分明就是愤恨,夹杂着不屑。
余咎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丞相的位置,按理说,自己也是一度肯定自己的处事方式,可如今,怎么也没搞明白,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余咎在水中泡了半晌,换了身干净的衣衫,这才跌跌撞撞地向王府走去,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回府中浸泡,只觉得这样自己会清醒些,尽管浸泡之后没有任何区别。
孙执是在到达府门之后,躲在老远看到余咎进去的,之后没多久,府尹汲鼢也冒冒失失地往王府走去。他倒是不明白会发生什么,只是觉得正如二哥所说,这才放心,派了一兄弟回去通告。
公孙单思索许久后,对尹冲说,“大哥可以放心,这赵蓦三人,有没有人去接走,我是不知道,但他此刻一定是自行前往大牢,以他个性,不会枉私。此番,牢狱之中,也不会有人为难于他,反而得到了照顾,性命也自是无忧,大可放心。”
尹冲听后,顿觉有理,微微点了点头。
“四弟情况,虽然不容乐观,但仔细想想,已是万幸中的大幸,当日我出策本是助他与父一同归天,现在一家性命均无忧,至于日后如何,那得看承相与府尹大人如何调度。此刻,四弟所思之事,乃是父母之安危,已不是不被父母所认,因此,我们可稍舒心。”
说到此处,二人又不禁感概一番,事事无常,本已做好最坏打算,成全四弟之念,送其去死,可谁又曾料想,刑场一番云雨,却是保住了全家人性命。若是不知情者,还真以为如余咎那番说辞,“天命不可违”。可真要有天命,天命真要保佑四弟,兄弟几人也不至于还忧心匆匆。
想到此,尹冲凝重中却也不忘揶揄一句:“这么看来,是这老天要配合二弟,二弟连风雨何时能来,都可以计算得出。”
公孙单无奈地摇摇头,说道:“并非我有算计天意之能,正如三弟能预知天雨,只因他幼年时常被父亲毒打,锁入地牢囚禁,才留下顽疾,若天气将变,其浑身疼痒并发难受,在外人看来神乎,不过是命苦罢了。三弟本性是开朗之人,却有不时沉寂得可怕,谁又能知三弟曾经发生了什么呢?”
公孙单叹气道:“我又怎知事件会发展到如此田地,怎知那赵将军所犯何事,竟然榜文也不敢明说。可事已致此,那不可明之原由,定会有个了结。大夫有杀将军之理,丞相有不杀将军之隐,岂是我等能揣度的?”
公孙单顿了顿,望着尹冲说道:“大哥,恕二弟姑且妄论,可能事情比你我想像得严重。赵骞定是非死不可之人,且要赵骞性命的人,乃是当今君上。”
“哦!”尹冲惊诧道:“二弟说说原由。”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公孙单说道:“我料想,定是只有赵骞之死,才可以化解赵、卫矛盾,否则战祸将致。马陵一战,虽是齐、魏、韩之事,却发生在卫地,卫国也受此祸害,唯有赵国置身世外,如若此刻再有战事,魏、齐难以再行救济。因此,君上不敢轻易开战,势必以最小代价平息事端。唯有赵骞之事,方是良策,赵骞之罪才有此而定,实是无妄之灾。”
“那赵骞一家,岂不是死得太冤枉了?”,尹冲激动不已。
“这些只是二弟的猜测罢了,大哥不必动怒。”,公孙单缓缓说道:“若赵蓦命丧刑场,此事便也了结,现如今,丞相与大夫二人前往,无非是交君上定夺,府尹前往自是为了探个究竟,我知丞相、府尹心向于赵骞,我等便也得其所幸,二人定会在朝堂之上据理直辨,是必力保赵骞性命。”
“嗯”,尹冲微微点点头,说道:“即如此,赵骞就应该没事了吧。”
公孙单摇摇头,说道:“究其原因,是君上想诛杀赵骞,此事由君上钦定,怎么会把责任追究到自己?可终究权力会达成平衡,事情终会有个承担者。这刑场闹剧,怎么会多出个赵弃,君上自会问个明白。梳理因由,本是这赵蓦一死而终,却由我搅弄出诸多事端,君怒之下,定会查出始作蛹者,唯有我死,方可平息众怒。”
“分明就是这君主胆小,不敢与赵人开战!”,尹冲咬牙咧咧的说道:“难怪诸国皆言,卫公怯懦,胆小如鼠!”
“大哥且勿妄言”,公孙单又是摇摇头,笑着说道:“并非君上胆小,而是小国有小国的治国之道,卫国乃四战之地,周边皆是大国,赵、魏、韩、宋、齐,哪年不战?卫国虽因战而祸连,却夹杂在大国中间,已是很多年无战事,尽管城池土地不停丢失,百姓却并未受战火牵连太多。君上也有他自己的难处,怎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尹冲又是连连点头,却又是摇头,止不住的哀婉。
“如此说来,我公孙单竟也无端地卷入到了领土博弈之中,为此丧命,岂不快哉!”,公孙单侃侃而谈,语气中却是带有些许豪气。
“怎能这般?”,尹冲听到此刻,才知道事情并非自己想像得那么简单,可这公孙单是一心为四弟着想啊。“要死,就让我一人来承担,我是你们的大哥,只有匹夫之勇。二弟,我知你心中有大志,切勿以我等贱命,枉费你天纵之才呐!”
“大哥!”公孙单按住尹冲肩膀,“想我公孙单变卖家财,以为资身之费。母、嫂俱力阻之而不能,治车马仆从,遨游列国,访求山川地形,人民风土,尽得天下利害之详。”
公孙单望着门外,细细而说,是似回忆着自己当初如何从故土出行,怀抱着满腔热血。没有谁能懂得,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无数有识之士,带着自己的一番见解与偏见,弃家人于不顾,只身投入到长途跋涉之中,个中辛酸,又有谁能懂得。功成名就者亦有,郁郁不得志志更多,有又谁去歌颂他们蝼蚁般的前赴后继?当忆起往日种种,唯有他们自己为心中的那腔热血感慨。
公孙单转而又望向尹冲,说道:“……如此数年,未有所遇,反险亡命于宵小,得大哥相救,今却又害得大哥与那赵蓦、赵嫈生隙,枉为人弟。实不相瞒,弟有时也窃以为自己有天纵之才,实则是把弄人心,玩权弄势之劣,怎敢大哥替我去死?”
此番话一说,那尹冲,公孙单二人已是潸然泪下,咽哽于喉。
一会,公孙单又说道:“大哥也不必都往坏处想,我让三弟前往,也是期待是有另一种可能。若那丞相、府尹二人中有一人未走出王府,则说明有人承担君怒,我等兄弟自是无性命之忧。可……这承担之人命运如何,我们又如何面对?”
二人说着,开始揪心于朝堂,直等三弟回报,却不知该期望何种结果。是啊,一切的决断,都指望高高在上的君上了,生杀予夺,尽在他一言之间。
可,又是谁,将这生杀予压的权力,更应该说是责任,推给君上,让其承担定夺后得到其“应该“得到的评价?
《诗经?大雅?桑柔》有云:“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苍。维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犹,考慎其相。维彼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狂。”
“苍天若是降祸乱与死亡,就要灭掉我们立的王。降下虫害,庄稼遭殃。哀痛国人,连绵灾荒。无人尽国,如何心怀上苍。唯有仁君,百姓爱戴。体恤民情,慎用国相。若不如此,独自享福。只念自我,国民会逆反。”
朝堂之上,将上演一场暴风骤雨……
(第五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