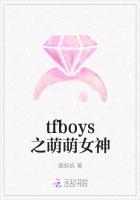”这TM怎么偷?这防护简直天衣无缝嘛,地面,空中都防着,怎么下手?”高丽棒子不认为我们能解决掉这么严密的防护。琳则笑他:”你个猪脑能有什么办法。”我也觉着有点玄了,这事要是能成,我们是不是太有大盗的范儿了?还能有偷不到手的东西?
林觉远也笑笑:”摄像头,热源感应,指纹认证,面孔识别,都不是问题。保管室里开启墙上安保的开关钥匙,这个就麻烦了,馆里没人知道那钥匙天天都收在哪里。就算找到了钥匙,最后的保险柜,第二层锁怎么办?”琳点点头:”钥匙是个问题。保险柜我有办法。”
找不着钥匙,便只好用最暴力的办法:破坏开关。林觉远给我们找了个熟悉电子原件和电路的高手,法国人,叫做Jean Pierre,到时候跟我们一起行动,专门负责破除那个开关。于是,我们便正式开始了这个庞大的计划。
Emma Lucas,四十六岁,女,离异单身独居,奥赛博物馆副馆长,是几个可以有权利进出保管室的重要人物之一。个人生活作风严谨,作息规律,每天的动向经过我们跟踪都几乎雷同。
Emma清晨六点半起床,半小时后从家里出发,晨跑一小时,八点回到家中,换上套装去街中一家固定的叫做La philosophie咖啡店用早餐,然后驱车到博物馆。在博物馆工作一天,晚上下班先去La philosophie咖啡店用餐,然后回家,接下来是处理个人事务,业余生活,天天如此。
这日清晨Emma照例在La philosophie点了杯红茶和两份点心,拿着在街边买的报纸慢慢边吃边看着,一边桌上的中年男人便跟她笑笑,借报纸要看看天气。Emma回笑向他,便将报纸伸手递过去。男人伸手接着报纸,手肘不小心碰到了红茶杯子,杯子便应声落地,碎裂成两半,茶水洒出个大大的水花。
男人忙连连道歉,边主动帮她拾起杯子,表示要回请她一杯,Emma笑着拒绝。于是男人边再次道歉,边坚持着又帮她点过一杯,付了钱,起身离开了La philosophie。
这位奥赛博物馆的副馆长Emma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清晨,遇到的这个小小的插曲,便是我们得到她的指纹和面孔的计划。
男人出了店门,拐过街角,将之前收好的碎裂的杯子和一个相机递给等在那里的一个华人,接过一沓钱,便匆忙离开。
林觉远在杯子上提取到了Emma清晰的指纹,用硅胶混合着树脂做了个指模和面模,小心的放到塑料袋中包好,交给了琳。于是,我们查点起要用的装备,准备着晚上的行动。
行动由四个人进行,Jean Pierre,我,高丽棒子,琳。
这日正好轮到林觉远买通的那个安保头目值班,那人提前关闭了个通风口大换气扇的开关,于是那个开在屋顶的有着巨大金属浆叶的大换气扇的通风窗口便被我们侵入了。
通风口刚刚好容下一人通过,好在我们四个人都是体型适中的,爬着倒也不费力。参考着结构图,顺利摸到了馆内一处离着摄像头最近的棚顶,我们便都停了下来,打头阵的琳拿掉挡着通风口的百叶扇,四下张望着,又看看手表,计算着巡更时间,示意我们都不要动,不要发出声音,便又将百叶扇拉回去。
我们尽量平稳了呼吸,一动不动。几分钟后,底下便有了脚步声,这是巡更的保安,手电筒闪烁着,伴着展厅里昏暗的灯光。
待声音远去,琳才重新拿掉百叶扇,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相机,以摄像头的角度为参考,照了张快速成像的相片,然后找出根小铜丝,将相片一角绑好,铜丝的另一头绑在摄像头上固定住。这样从摄像头上看来,便只有展厅里影像的照片了。
琳轻轻的翻身落下展厅,我们便一个跟一个的下去了。依着结构图,快步的摸到连接着保管室的大走廊。走廊顶上就是热源感应警报,四下有几盏红色的灯做为光源。高丽棒子咧咧嘴,掏出随身带着的一个小型灭火器,拽掉保险环,边喷着干冰,边小跑到感应器底下,对准了感应器一阵死喷,直到干冰喷尽,那感应器上便结了厚厚一层白霜,彻底失去了效应。他这才脸上有了得意,回头招呼我们过去。
我们在走廊尽头立定,面前就是保管室大门,门边便是指纹认证和面孔识别。Jean Pierre翻出一个我们都不认识的密码破译装置,连接到认证系统中,大概用了十多分钟,密码通过,开始认证。琳找出做好的指模套在手指上,按住了指纹认证仪不动,一声轻轻的”滴”响过,通过。
接下来琳又套上了面模,将脸对准面孔识别仪,固定住身体不动。几秒种后,仍是”滴”的一声,保管室大门顺利打开。高丽棒子这阵子兴奋起来:”老子也有当大盗这一天,偷的还TM是奥赛博物馆!””你激动个屁。”我示意他稳一下情绪,这个功夫最好不要冲动,不然是要犯错误的,会害死好多人。
保管室的大门就这样敞开着,我们却都不敢进,因为门内的地面有震动感应警报,空间中则是不规律的红外线。这个时候,就该看Jean Pierre的了。
Jean Pierre自信的笑笑,用不熟练的中文说:”这是个小问题,交给我。”
琳点点头,示意我们靠后,掏出了夜视仪戴好,眼中便出现了错综交杂的红外线。她翻出事先做好的一端扁平的金属棍,小心的探进门内,躲开红外线,插进控制开关的盒子的缝隙,一顿胳膊,”咔!”盒子外边罩着的盖子便落了下来。
”发克!”眼见那盖子要落到地面,我心中一沉,这要触发了震动感应,那我们全完了。说时迟那时快,我完全是凭着自然本能的反应,倒地伸手一抓,便将那盖子牢牢抓在手中,保持着姿势不敢再动,脑门上全是冷汗。
琳拍拍我,示意我成功了。
将要收回手来,琳却按住我:”别乱动!”我听得一愣,只好身子僵着,边看向她。琳将夜视仪摘下来帮我戴好,我便看到了密密麻麻的红外线交织在我手的周围,刚才我实在不知道哪来的运气,刚刚好就把手伸在那堆线的中间,再歪个几公分,就完了。
”我的天。”我小声的说,便沿着线的缝隙慢慢抽回了手,心中这才咕咚咕咚的一阵狂跳着,这是实实在在的后怕。
我躺在那里缓了有一分钟时间,才定了神。
”琳姐,险啊。这盖子要是落了地,我们全完了。””这属于意外情况。谁能料到这盖子一捌就能完全落下。””恐怕当初就是故意这么设置的,那盒子如果被破坏了,震动感应就能发现。”
”别说废话,我们不是来玩的。”高丽棒子打断我们,看向Jean Pierre。Jean Pierre点点头,将夜视仪从我眼前拿下,戴到头上,小心的绕过红外线,伸了头进去看看盒子,然后缩回头来:”不难处理。一个主控装置,通过线路连接。你们谁去剪线?有六根线连在底下最大的一个电容附近,一般主线都是红色的,需要剪断红色的那根就可以了。””你不能剪线吗?””我的朋友们,我是个色盲,我看什么颜色都是红色的。”
林觉远这个畜牲。我心说,你给我们找了个色盲?我们三人大眼瞪小眼的瞪了半天,最后无奈的看向Jean Pierre。既然他是色盲,现在报怨也没什么用了,再说眼下的状况也容不得我们犹豫。琳是不放心高丽棒子做这样的事的,便将夜视仪套在我眼睛上。我心说就剪个线,问题应该不大,注意别碰到红外线就行了呗,然后点点头,寻了钳子,小心的探进头去,便看到了那个盒子。
盒子底下有个醒目的大电容,边上确实分布着六根线,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怎么看,那六根线怎么是一个颜色的,全是红色。
我小心的把头探回来:”琳姐,我剪不了,那线全是红的。”高丽棒子就吃了一惊:”驴蛋儿你也是色盲?””你TM才是色盲!”琳让高丽棒子别说话,亲自带了夜视仪探进头看了看,缩回头,指指走廊里头顶的红色暗灯:”是这个灯的问题。在这样的红光下,这些线当然全是红色的。”
现在怎么办,那怎么剪?
”要不然,随便蒙一根吧?”高丽棒子说:”反正都是红的。蒙对了我们就成功。不对了顺原路撤回去,以后再说。””以后再说?这个只能一次成功!这次不成功,以后的难度就要大上几倍!你这脑子这辈子还能不能有机会进步了?”
”我的朋友们。”Jean Pierre说:”根据我多年的色盲经验,虽然都是红色,但是按照本色原理,红色和其它颜色的混合红,是不是应该比红色本色的颜色浅一些?”琳听得一愣,问:”你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六根线中,看起来颜色最暗的那根应该是。””应该是?你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吗?””我不确定,但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