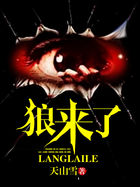水风轻从我背上跳下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着那阁楼的大门就是一脚猛踹,砰的一声巨响,真的像战场上的大鼓擂得地动山摇。阁楼上的灰被震得四分五裂,稀稀落落地连串掉下来。
“傻丫头,别费老劲了,你看这大铜锁,大得跟石锤一样,岂是你一个女孩儿家能够踹开的。”我仍然躺在地上懒洋洋地休息。
“我就试一试,一千多年的玩意,谁说它就一定是好的。没准还搞出匹木牛流马来骑上一骑呢。”她笑着说。
对啊!这不是军械库吗,外面山洞中的壁画上有诸葛连弩,结果地道中真出现了。那壁画上不是也有木牛流马吗,谁说这青铜古城中就一定不会出现木牛流马。管他的,不管是有是无,先搞它一搞再说,反正我这童心跟水风轻一样炽盛。当下二话不说,爬起来就拉住她,笑着说:“你力气太小,让本大爷来试试。”说着往后退了一退,一涌一跳,砰的一声就踹那青铜大门之上。
这一脚下去,奇迹还真的出现了,那石锤般的铜锁喀拉一声响,哐当就掉到地上,左右两扇大门一紧一挣,把铜锁都撂起老高。本来我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心想那么大的锁,再怎么着也得用砍刀加工它两下,没想到这么一踹就整开了。心里不由得一紧,赶忙双脚点地,往侧边一跃,把水风轻挡在铜门开启的范围之外。没办法,我是被这鬼地方的机关给整怕了,彻头彻尾地怕。
两扇铜门嘎吱嘎吱地向里开去,虽日久年深,但在惯性的作用下倒也开得顺畅,哐当两声就撞在了内墙之上。铜门开启之处,一切都是风平浪静,除了灰尘漫天飞,并没有什么飞箭流矢之类的射出来。我朝里面打了一圈手电,发现里面还有一层隔墙,也是从低到高用青铜铸成,现出斑斓的翠绿铜锈。这到底是什么鬼国家,如果不是富有得流油,就是有色金属多到用不完。
我和水风轻走进军械库里,几个山人没有照明设备,呆在外面黑洞洞地心里怕得慌,也各自搀扶着跟了进来。这内墙用的不是铜锁,而是那蛇头形的触发装置,也是嵌在墙壁里。我叫大伙儿躲到一边,也像在地道中那样按部就班,向右旋转那蛇头,可惜没有半点动静。又向左使劲一旋,也没有动静。这下可火了我了,加了一把劲,朝里使劲推,还是没有反应。完蛋了,这开门的机关跟外边不一样,看来满怀的希望就要这样泡汤了。刚才水风轻说木牛流马的时候,我这心里被激起的希望之光,真是比太阳光照都要耀眼。这一路上背着马良,可着实是把我累个半死,其他几个山人又或轻或重地受了伤,也帮不上什么忙。如果像这样以老弱病残的方式缓慢行军,只怕还没找到出去的路,我就让马良给压死了。所以此时此刻,我心里当真是巴望着捣出两匹会走路的木牛流马来,至少也把马良给驮上,如此,我们也就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水风轻见我弄不开,就自己捋起袖子来,扎了个马步站在那铜锁前,哼哼哈哈地摆弄了一阵,也是无济于事。
“水姑娘,歇着吧,歇够了咱就赶路。这是军事重地,一般人弄不开,古代皇帝调兵,还得动用兵符呢,要是随便就让一般人给弄开了,那岂不是要惹大祸。”
“做人呢,贵在乐观,这可是你说的啊,傻大帽。”水风轻漫不经心地回答着,用手电在那蛇头里照来照去。
“我乐观着呢,只是这会儿累了,走不动路。”
“别着急,等我看看这是啥。”水风轻似是发现了什么,把手伸在那蛇头里抠,“傻大帽,你把水和你那件破T恤拿出来。”
“干嘛?”
“唉呀,你累就少说点话,省着点力气用。快拿出来。”
“我的水没有了啊,一路上都让你给喝光了,不喝自己的,就知道喝我的。”
“那你拿我的,我的还有半瓶。”
我就先把背包里那件割得剩下一半的T恤拿出来,然后把水风轻背包拉开。这一拉开,两只眼睛一下子就被唬住了。
“水姑娘,你这玩意哪里来的?”我把包里的东西拿起来问她。
“什么玩意?”水风轻说着回过头来。
“胶卷……”我刚一说出这两个字来,水风轻看着我手上的玩意也是一愣,“还有这块东西是啥玩意?”
我手上拿着的东西,正是两卷柯达胶卷,这玩意现如今早都没人用了。还有一大块铜牌,表面凹凹凸凸的像活字版,自然也是满布铜锈,在一端铸了个拴钮,穿了一根老旧的皮质细绳。至此,我再也无法相信马老头先前所说的话。不是说这幽冥山中无人问津吗,为什么在这不知东西南北的旷古遗城里,却冒出了一个人模鬼样的蓝家伙来,为什么在水风轻的背包里,却莫名其妙地多出了两卷现代人所用的相机胶卷来。
“我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啊,这哪里来的?”水风轻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
“对了,会不会是那蓝家伙,塞手电给你的时候放进去的。”我略一思忖说,除了那蓝家伙,这玩意还真没其他来路。
“估计是。”水风轻以肯定的口吻说道,“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我完全就察觉不到背包被拉开了。”
“那会儿你都快吓死了,怎么可能会觉察到,再说那蓝家伙出手速度极快,咱又不是没见识过。”
“也是。……胶卷,这里面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呢?”水风轻拿起胶卷来端详着,“等等,这块铜牌是啥鬼玩意……哦,对了,傻大帽,会不会是门卡。”口上这么说着,她就慌忙抓起那块铜牌,去那蛇头上比。比了两下,终于兴奋地说:“快,水和T恤递给我,这铜牌八成就是开这军械库大门的通行证。”
我这希望的火苗又让她给点燃起来了,赶紧把水和T恤递给她。她往那T恤上掐了一只角,倒了点水浸湿,用手指塞到那蛇口中去擦,如此擦了两三次,又把那铜牌上的铜锈也抹了抹。就把那铜牌端平,聚精会神地向那蛇口里面插了进去,就像把钥匙插在锁眼里一样。插进去之后,又抓着那蛇头,向右边一旋转,只听喀喇一声响,这面大铜墙还就真的打了开来。
这一幕,差点把我的眼都看瞎了,压根就没想到这蛇头里面还隐藏有卡槽,如果不是这水风轻眼尖,还真的是要跟这军械库擦肩而过了。我本来打算好好夸奖她一番的,但从门缝中看到里面的情景,一切的言辞,都被震惊得颓然落地。那铜墙里面,居然真的出现了木牛流马,从外往里,齐整整地罗列了一大片,把几个人都震撼得忘乎所以。
“啊……”我高兴得大叫了一声,同时向水风轻竖起两个大拇指,“水姑娘好厉害,多亏你发现了那卡槽,要不然……”
“哼哼……谁让你那么性急的,性急误事,下次多学着点。”水风轻一撇嘴,傲骄地说。当然了,这并非真正的傲骄。
“是……是,水姑娘教导得极是。”我嘿嘿笑着,把那铜牌拔出来,连同胶卷一起,仍然放回水风轻的包里,往下面捂了捂,像对待夜明珠一样用心。水风轻想抢着往前走,我仍然把她往身后一拉,率先进入了这军械库里面。
军械库很是宽敞,面积估计有五六百个平方,而且看样子还不止一层,最里面还有楼梯接到上面。咱们面前的这一层,四周全是青铜架子,架子上俱都竖着刀枪剑戟之流,看起来几乎都是长柄武器。大厅靠左侧一边,列着两排攻城车,跟一挺挺大炮似的。除了两排攻城车,其余部位陈列的都是木牛流马,也没那么多时间去粗略地数,反正看这派头,一百多头的数绝对不会少。这些木牛流马形制跟山洞中壁画上的一样,有的是牛头,有的是马头。造型颇为美观,大致轮廓就是牛马造型,只是在关节衔接处,做得跟盔甲的护肘护膝一样,留出一些间隙与弧度,以方便木牛流马移动。
事不宜迟,当下我最关心的就是这些木牛流马还会不会走。就对着这些牛马仔细观察了一番,在那牛头马身上动手动脚。我发现这牛头马头都是可以活动的,使劲用力一扳,还会咯吱咯吱响。在牛马腹部的左右两边,也就是咱们骑马时挂马镫的地方,有一块巴掌长短的托子突出来,就像摩托车换挡的脚踏一样。看那构造形式,左右两边的托子应该都是可以活动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触发机械装置的玩意,就用袖子把身旁的一匹胡乱抹了抹灰,爬上去坐在背上,脚下缓缓用力。果然,只要脚下一用力,左右两边的托子都是可以踩动的。但遗憾的是,可能还是年代太过久远的缘故,这些木家伙内部早已是该虫蛀的虫蛀,该腐朽的腐朽。那托子只咯噔响了一下,木牛流马就一点泡都没有冒。连续试了几匹,都是如此,不觉垂头丧气起来。
这个时候,突然闻到一阵臭烘烘的味道飘了过来,这种味道我再熟悉不过,非常浓烈浑厚,熏得我都一阵阵反胃,就责问了一句:“是谁把鞋子脱了,赶紧穿上,这种宝地咱最好不要污染,当心地底的亡灵怪罪上来。咱只是进来借两匹马,不要乱来。”
“是我。”声音是马由江的,从我们右前方的墙脚处发出来,“我见这里有靴子,想换一双,我这鞋子在那大湖边踩到了烂泥,臭烘烘稀溜溜的,穿着难受。”
他话一出口,我就把手电向他那边照过去。他娘的,一下子又被吓得心都掉在地上,在马由江身后,又是那个大黑鬼。也跟先前一样,只是倏忽一闪,连眉目都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大叫一声,赶忙朝着四周打了一圈手电,可是连鬼影也找不到。这到底是什么鸟玩意,要再这样猝不及防地轮番上演,我非得被它提前吓出老年痴呆症来不可。
“你们……看到了吗?”我问身旁的几个人,除了马良躺在地上呻吟,水风轻在聚精会神地研究木牛流马之外,马老头和马如泉都看到了,二人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娘的,这到底是凶多吉少还是吉多凶少?每次都这样。”我悻悻地骂了一句。
回头再看马由江时,只见他耷拉着个脸朝门口走去,也没穿鞋,那双臭烘烘的运动鞋也就任它放在地上。“由江大哥,你没事吧。”我问他,寻思着不会被那大黑鬼怎么样了吧,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神情颓丧起来。
“我突然感到头晕,到门外去透一口气。”马由江头也不抬地回答,仍然顺着墙边朝门外走。
我就纳闷了,怎么突然就头晕了呢,这里边除了臭烘烘的鞋臭味,也没啥毒气呀。我就走到他脱鞋子的地方去看,挨着墙角果然是摆了一大排军靴,既有麻布做成的,也有皮革做成的,样子都颇为精美。麻布做的早就腐朽得不成样子,皮革做的有的勉强能穿。这里离我们站的地方有十多米远,刚才就我打着一把手电,光线不是很充足,也亏马由江能找到这些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