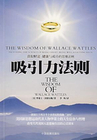你爱我,我会知道
罗宇/文
遇到他的那一年,我17岁,他47岁。
17岁的我,把头发烫得像盛放的牡丹,涂紫色的眼影,装模作样地叼根烟,跟一群不良少年混迹在夜店里。课旷得多了,老师就给我打电话,我很嚣张地笑:“不就是请家长嘛,又不是第一次,你看着办好了。”老师软软地说:“叶小羽,你这样对得起——”我知道她会说什么,就很快挂了电话,继续喝酒,可是心里酸酸的,很难受。
从酒吧出来,已经凌晨3点多了,我喝得醉醺醺的,忽然就看到他站在不远的树下,穿得像只甲虫。
他徘徊着走过来,声音抖抖地指着我说:“你,叶小羽,给我过来。”
我傻了眼,没有想到他会到这里来。男生们问我:“叶小羽,你爸爸呀?”我说不是。
他们喝了酒,正在四处滋事,一听便来了兴趣。我刚背过身,便听到拳打脚踢的声音和他的呻吟。我镇定地离开,强忍着没有回头。
是的,我恨他。很多夜里,我流着眼泪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还狠狠地诅咒他。可是今天,我远远地看着他佝偻成一团,腰弯得像只虾米,落寞地往回走,心里却涩涩的,并没有预料中的开心。
第二天,我酒醒了些,回想起来也有些后悔,便窝在家里不敢出门。直到那晚的朋友打来电话,说他伤重住院了。大家央求我去看看他,主要是去息事宁人,希望他不要报警。
去医院时,我带了些自己胡乱做的皮蛋瘦肉粥,在病房门口徘徊。他看到了,说:“是小羽吗,快快,进来啊,拎的什么,喔,好香啊。”
眼睛里有湿湿的东西在涌动。记得我第一次做饭,父亲也是这样,面对着一桌子难以下咽的东西,装出一脸的惊喜。可他不是我父亲,我忍住泪,狠狠地看着大口吃东西的他,心里的恨难以消除。
他本是跑出租的,我高三那年,他停了工作,在我家隔壁租了房子住下,开始做我的保姆和保镖。他买了菜谱,围上围裙,做好就敲我家的门,傻傻地说:“尝尝,小羽,我新创的,看可不可口?”还要时不时地把来找我的社会青年赶走。我站在窗口,看着这个内心胆怯却故作勇敢的矮小的男人大声呵斥他们:“我家小羽就要高考了,谁敢乱来,别怪我不客气!”有男生笑他:“你是她什么人,管得着?”
他义正辞严,表情严肃:“我是她爸爸。”
为此,我和他大吵了一架。我的手几乎指到了他的鼻尖,我的声音那般尖利。我说:“陈建生,不要忘记了你对我家做过的事,我告诉你,谁都可以做我爸爸,除了你!”
我一如既往地躲着他,他怕我变坏,也一如既往地跟着我。我的头发越来越长,黑黑的,盖住了以前那些花花绿绿的颜色,劣质的眼影让我的眼睛疲惫不堪,我只好把以前的大黑框眼镜戴上。偶尔他看我久了,会舔舔唇憨憨地说:“小羽,我第一次见你,就是这样的好孩子形象啊,也不说话,就那么乖乖地看着我。”我挑衅地看着他:“那你也还记得是什么场合吧。”我们的短暂谈话戛然而止。我的话刺伤了他,看着他受伤离去的身影,我的心里有轻微的快感。
是的,我似乎永远都那么恨他,不管他为我做过什么。
转眼我大学毕了业,又在这座城市扎下根来。家还是那么大,我走在中间,空落落的。父亲的照片还在,人还是微微笑着。镜框擦得很干净,想来他也常来帮我收拾屋子。他还住在我隔壁租来的屋子里,干起了老本行,早出晚归地跑出租。我们很少见面,见到了,也很少说话。我不理他,他老了,话也少了很多。
因为寂寞,我认识了一个男孩子,叫刘雨,是在酒吧里。他看我埋头喝闷酒,就带我去跳舞。强劲的音乐,闪烁的灯光和疯狂的摇摆让我暂时忘记了所有不快。约会几次后我带刘雨回家,他死死地守在门口,就是不让我开门。
时间似乎倒流到几年前,他脸上还是怯怯的表情,声音抖抖地指着我说:“你,叶小羽,给我过来。一个女孩子,像什么话!”刘雨问:“你爸爸?”我说不是。我的酒气喷了他一身,我说:“我就是没教养的女孩子,怎么了?可是,是谁让我爸爸死那么早的?”我的话永远带刺,他不眨眼地看着我,眼泪顺着眼角流,老泪纵横的样子。我的心突然软了一下。
从小到大,我从来没见父亲哭过。可是他哭了两次,满脸眼泪鼻涕,哭得像个小孩子,那该是怎样的伤心啊。
后来我和刘雨分手了。他说得对,刘雨不是个好男孩。他喜欢赌博,每次输了钱就去酒吧喝酒。我说分手,他不同意,还醉醺醺地说:“叶小羽,你家的事我打听过啦,几年前的车祸,那老头赔了你不少钱吧。”我狠狠地看他,心像被铁锤狠狠地敲,脑袋里也嗡嗡作响。不知道什么时候,陈建生进来,把我带了回去。
我蹲在门口,把头深深地埋进膝盖,哭了。他像哄孩子一样拍我的背,说,小羽乖,不哭,有我在呢,我们回家。
我默认了他的存在,他做的饭,我不再排斥,他偷偷地跟着我,我发现了也不去戳穿。我知道他只是担心。我对父亲说:“爸爸,除了你,这世上没有比他对我更好的人了。”
有一天下了班,我在街上闲逛,身后传来一阵急刹车的声音,很快便围了一堆人,我没有在意,继续往前走。可是忽然心猛烈地跳起来,跳得我喘不过气。我恍恍惚惚地回头,冲上去推开围观的人,忍不住叫出声来。倒在血泊里的,真的是陈建生。
在救护车上,我抓着他的手不停地哭,不停地喊。心在流血,仿佛从身上割掉了一块肉。他浑身都是血,还有一丝意识。他也抓紧我的手,气若游丝:“孩子,不哭,我还在呢。”
到了医院,我掏出一堆卡,哭着一张张地刷,弄混了密码,又急得跺脚,周围的人都看着我。好不容易交了定金,签了字,看着他被推进急救室,才慢慢地平静下来。等待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些过往。
初次见面,是在医院,他开车撞到我父亲,我唯一的亲人。我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他,心里是那么的恨。然后他开始管我,把家搬到我的隔壁,学着做饭。他怕我想不开,怕我交友不慎,就偷偷跟踪我。他怕我被人骗,就偷偷地调查刘雨。他那么老了,走路慢,又怕跟丢,所以被车撞。我边想边哭,边哭边后悔。我想,只要他平安,我再也不和他作对了,不,哪怕拿我去换呢,我也愿意。
这次意外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他的一条腿不能灵活走路了。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唉声叹气。我做了饭,他看着我吃几口又放下,坐起来专心致志地长吁短叹。我给他捶腿,他自怨自艾,唉,废了废了。我买了一辆轮椅,有太阳的时候就推他去小花园,我听自己的MP4,他看自己的报纸。出院后,我退了他租的房子,让他搬进我家。他做饭,我吃,他看电视,我上网,他叫我叶小羽,我叫他陈建生。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流,可是生命中的某些东西,似乎已经融在了一起。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可以好到不计回报,天下除了父母还有谁呢?陈建生不是我的父亲,也不用弥补过错。记得那天晚上,父亲急着来学校看我,横穿马路造成了车祸,陈建生没有任何责任,可他还是毅然地开始管我。
他住院时和一个朋友谈话,我在门外听到了,他说:“叶益民临终时拉着我的手说,帮我照顾小羽,她是很乖的孩子。”
我的眼睛渐渐湿润。叶益民是我的爸爸,原来他在临终前,找到了另一个人来替他继续爱我。
他的朋友继续问:“她现在接受你了吗?”
陈建生嘿嘿地笑:“她对我好,只是没有说,不过我知道。”
那一刻,我流着泪想,一定就像以前,他对我好的时候,我也相信,他爱我,有一天我会知道。
天冷就回家
屠克隽/文
2002年,我36岁的生日那晚,丈夫在一个年轻女大学生的温柔乡里不识归路。离婚时,他冷冷地说:“你一个中专生,没钱没业,自己都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女儿跟着你能有好日子吗?”潮闷的五月,丈夫的话像一场冰雹,七零八落地砸在我心里,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已被优秀的丈夫抛离了很远。他不断地进步,只有我原地不动做着“义务保姆”。为了女儿的前途着想,我含泪在离婚协议上签名,同意女儿抚养权归她父亲,我只分得3万元现金,其余财产作为女儿的抚养费。
清点衣物那个周日,女儿月月坚持不去学琴,默默地坐在床边陪着我收拾衣服。良久,她轻声问:“妈妈,如果我不上课外班不参加春游,就不会花很多的钱,你能养得起我吗?”女儿清澈的眼眸充满渴求,我咬着唇坦白,“月月乖,妈妈现在没办法供你上学,而且你也不能不去课外班。”女儿攥紧手,声音微颤地说:“那你要答应我经常来看我,我会很想你的。”女儿无声的眼泪让我恨透了自己的无能。此刻我才明白,丈夫的抛弃意味着我将一贫如洗,从物质到精神,从现在到未来。
我在女儿就读的实验小学附近租了间20平方米的出租屋,方便我探望她。我再三叮嘱女儿:“别让同学知道你妈妈住这里,他们会笑话你的。”月月却并不把我的话当回事。有一次放学,月月挽着同学的手在岗夏村遇见手提青菜的我,女儿骄傲地指着农民楼说:“我妈妈就住这儿,她专门找离我近的房子,就是想随时能看见我。”同学走后我问月月:“妈妈住这么破的房子,你不怕同学看不起你吗?”女儿仰头很认真地想了想说:“不怕。等你找到工作有钱了,不就能换大房子吗?”女儿的天真让我又欣慰又心酸,假如当初不是坐享安逸,我怎会落魄如此?
2003年春节,月月打电话央求我回家吃饭,“同学说大年三十不团圆的话,明年大家都不吉利,妈妈你回家吧,爸爸已经答应了。”晚上8点,街道上的行人寥寥可数,我穿行在寒风冷雨中,心里不免自怜。就在我独自伤感时,突然听见月月欢快的声音,远远的,月月举着一串冰糖葫芦从小区里向我奔来。“妈妈你来了,吃糖葫芦吧,吃点甜的就不冷了。”吃过女儿的糖葫芦,胃果然暖和一些,情绪也平复了,总算与前夫相安无事地吃了顿“团圆饭”。
离开的时候,月月坚持要送我去车站。走出小区,月月塞给我一个大信封,神秘兮兮地说:“妈妈,这是我送给你的新年礼物,回家才准打开。”在台灯微弱的灯光里,我从信封里倒出一摞人民币,1元到50元不等。凑起来共有769块钱。一张小信纸上是月月漂亮的楷书,写着——这是我今年攒的零用钱。爸爸说等我初中毕业就送我到澳大利亚读书,我不想去,也不想叫那个姐姐做妈妈。妈妈,还有3年我就初中毕业了,我们一起存钱,只要你有了钱我就不用再离开你了。
眼泪像冰刀一样划痛了我的脸。我暗自发誓,一定要想办法挣钱,想办法把女儿留在身边。
为了早日和女儿团聚,我更急切地找工作,然而数十封求职信石沉大海。
11月,我到酒店应征客房服务员。主考官问我:“做客房很辛苦,你为什么应聘这个工作?”我坦诚地说:“我需要钱养活自己,攒钱争取女儿的抚养权。”也许是我的遭遇和乐观打动了考官,酒店破格录取了我这个超龄服务员。知道我获得工作机会,月月特地买了朵康乃馨奖励我。
离婚夺走了我的骄傲,也让从前那个骄傲的小公主月月沦落成家里的保姆。每次月月来看我,总抢着替我洗床单被套,从她娴熟的姿势中不难看出“训练有素”。怕我难过,月月只字不提在那边所受的“待遇”,只是一再敦促我:“妈妈你什么时候才申请我的抚养权?”女儿的未来成了我的心病,父亲家有享之不尽的奢华却没有爱,我能给她200%的爱却挤不出足够的教育经费。
为了我和女儿的将来,我决心重新开始。我开始利用闲余时间去成人培训班重新学习英语。
2005年3月,我因表现出色被调到总机房工作。5月,一位加拿大客人错将打到前台的电话拨到机房,他说肚子很疼,请我们替他叫救护车。整个机房只有我能和他用英语交流,事态紧急,我直接拨打了120,幸亏抢救及时,客人才不至于阑尾穿孔。而我也因为出色的应变能力和英语能力,被推荐到了前厅部任经理助理,月薪从2000元涨为5000元。
说服前夫放弃月月的抚养权确实费了些工夫,但最终,我如愿让前夫签下同意书。当他提及抚养费时,我淡定地说:“不用了,我是她母亲,我有责任也有能力抚养月月。”我知道,当时我的表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信和骄傲。
从民政局出来,冷空气提前南下,我穿了件短袖T恤,站在实验中学的门口瑟瑟地等月月放学。远远地,女儿从雨中奔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说:“好冷啊!妈,我们快点回家!”
天堂里有没有蝴蝶花
小何/文
小妹不是我的亲小妹。
她是继父的女儿,母亲带我改嫁到许家的时候,小妹就在了,她比我小10天,我记得自己很紧张,一直牵着母亲的手,那年我9岁,小妹倚在门上甜蜜地叫我,哥。
我仍然记得那个哥字有多清脆多响亮多让人感动。
它于我而言,是最柔软的一声称呼。父亲去世后,我饱受同族人的欺负,万般无奈之下,母亲带着我改嫁。我的小伙伴们说,找个后爹更可怕,而妹妹告诉我,她的恐惧比我还要多,因为,她怕后娘。
娘是个善良的人,所以,几个月之后,小妹就不再恐惧了。她把我当成亲哥,有什么东西总是偷偷让给我吃。继父脾气不好,总爱打人,我挨的第一顿打是因为我把一盒粉笔全泡在了水里,数学老师找上门来。
我讨厌数学老师,她永远偏向那些有钱有势力的同学,所以,我才故意这样做的。
这样做的结果是她要我继父赔她的粉笔,本来是5毛钱一盒,她却要一块钱。
那时一块钱是很大的数字。继父在老师走后打了我,他骂,小兔崽子,不要以为一块钱有多好挣!
母亲把我抱在怀里哭了。
而小妹站在一边,一会儿出去给我洗了条热毛巾,我的屁股还红着,小妹说,疼吗,哥?
我的眼泪那时才掉了出来。
继父远远没有小妹的善良,他总疑心母亲偷了钱和粮食给娘家。终有一次,他说自己家的玉米丢了几十公斤。母亲跑到井边号啕大哭,父亲嫌她丢脸,揪过她就打,而我疯了一样冲了上去,差点儿把继父撞到了井里。
继父对我更不好了,简直是充满了敌意。他说养了半天是替别人养的小虎娃子,与他无关。所以,在钱上更苛刻我。我和小妹都上初中,小妹不用带馒头,我却要带馒头,小妹吃的穿的都比我好。母亲暗自流泪,却说,娃,在人屋檐下,低头吧,娘做不了他的主。
让人感动的是小妹,她总是打了饭菜端给我,然后就着我的冷馒头吃,我们兄妹一边吃一边聊天。在那5年,没有小妹的照顾,也许我心里充满了恨。但因了小妹,我原谅了那个男人。正像母亲也偷偷给我钱一样,我也是一分为二,一半给自己,一半给小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我们却是那样亲。
初中毕业,我们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高中,然而我知道,我和小妹只能一个人去上。
小妹的成绩比我还好一点。母亲的意思是,男孩儿干点什么都行,女孩子还是考上学好,所以,我决定退学了。
妹妹没有说什么,继父更是同意。
那个夏天我很郁闷。我和母亲暗自流了几次泪,甚至我觉得和小妹的关系都疏远了,母亲已经给我联系了远方的亲戚,准备去外面打工。17岁的男孩儿出去没有问题了,可我真的很想念书,因为父亲就是一名大学生,他也希望我能读大学,可惜,他去世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