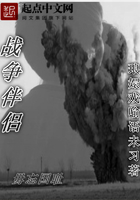爷爷仰天长叹一声:“八儿命硬,她是来讨债的……我们上辈子欠她的……”爷爷嘟囔着,老泪纵横,“黄叶不落青叶落……”老人嘟囔着,拄着拐棍一晃一晃的往村口挪去。
“都回去吧。”八儿爹用手拍拍坟头的黄土,拽起八儿,就往回走。八儿一步一回头,看着那个小小的土堆,默默忍着眼泪。大哥和四姐一起把娘搀扶起来,慢慢的跟在后面。
八儿奶奶心疼这个懂事的小孙子,逢人就说她这个孙子是被那个命硬的妹妹克死的,他妹妹是个扫把星。她每说一次,就生气一次,唠叨、咒骂、十分激动。
终于有一次,奶奶因为生气过度,高血压引发了半身不遂,瘫痪在床上。别说骂她,连说话都不会了,生气的时候直呜啦。
爷爷和爹爹要伺候奶奶,娘也要给奶奶做饭、洗屎尿布,为了方便照顾,就把爷爷奶奶都搬到这边院子里了,让四姐到奶奶那院看门。四姐害怕,不得已找了两个和她年龄相仿的邻家女孩子,三个大姑娘一起住在奶奶那院子里。
八儿和娘还有小侄女珏儿都搬到了四姐原来住的东屋,爹爹有时睡草房,有时在堂屋伺候奶奶。八儿娘一天到晚的忙家,哥嫂还要忙地,只有她和几个孩子是闲的,放学了就在奶奶院子里写作业。
已经好多天了,一家人都没有笑脸。
王家老三淹死的事情传遍了全村,一个个议论着当时的情景,甚至有人猜测,淹死了肚子里没有喝水,那是被水鬼作了替死鬼。很多大人都不敢往那条河里洗澡、洗草了。家人警告过他们几个小孩子,谁要是敢下水,回来就吊起来打个半死。
后来,八儿缠着爹爹,要和爹爹互换睡处。八儿爹拗不过她,只好答应她,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能自己点灯——爹爹怕她晚上打翻了油等着了火,一屋子的干草,烧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八儿答应了爹爹,就一个人搬到了三哥睡觉的那个西屋。西屋有三间是牲口房,中间一间留有门口,靠后墙一堆干草,旁边北间是一个喂牲口的地方。槽头除了她爹爹前两个月新买的一头母牛,就是侥幸剩下的几头山羊。南间有一张用绳子扎起的软床,床尾就是八儿最为宝贝的那辆车棚子,里面放的是那一柜子平时八儿用不上的书。
爹爹不准她在西屋草房点灯,西屋就只有槽头的煤油灯高高的挂在墙上,微弱的灯光飘忽着,把羊群照出各种奇怪的影子。一到晚上,八儿就呆呆的看着羊群,想着三哥喂白马的样子。
尽管草屋有蚊子,味道也臭臭的,但是八儿夜里睡的很死,除了偶尔做个噩梦以外,倒也安稳。三哥再也没有出现,哪怕是在梦里。她在梦里呼号着寻找三哥,可是除了翻滚的河水,连个人影也没有。
那块地,那块埋着她三哥的棉花地,娘不想去,去了就伤心的哭泣,嫂子和四姐不敢去,她们怕……
八儿不怕鬼,她甚至希望见到鬼,但是她怕水,也怕挨打。她不敢到河边去,实在忍不住,就经常借着到菜地去的机会,一个人偷偷的跪三哥的坟堆边,自言自语的说话。要么就是呆呆地站在棉花地里,远远的望着翻滚的河水,希望她那三哥哥能突然出现。可是,那么多天,她什么也没有见到,包括在梦里。
白马没有了,三哥也没有了,她最惦记的和最惦记她的都不在了。八儿除和侄子、侄女一起去帮着放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意外,就是学习了。
她发誓要好好学习,以后就要当个厉害的好警察,把那些害人精都枪毙了,她不能让她的白马白死,不能让她三哥白死,她长大了要是当不了警察就要当个大官,一定要搞清楚爸爸到底有没有被冤枉,谁要是冤枉了她爸爸,她发誓一定饶不了他!她知道自己会长大的,会长本事的,总有一天会把那些坏人都抓起来的。
她翻熟了课本后就找爸爸的书箱。不管是书上的,还是爸爸写的,不论是能看懂得,还是看不懂得,她在那盏煤油灯下看、她在树荫下看,她在放羊的时候还看,书成了她最大寄托。
能看懂得看,看不懂得查字典。一点点把那些书上的东西啃进去,把那些爸爸写的东西刻在了脑子里,不论是爸爸的笔记,还是爸爸的日记。爸爸的音容笑貌在文字间一幕幕呈现,永远的刻画在她的脑子里。
她觉得她身子里流的是王家的血,可脑子里装的不仅仅是王家的事。她在爸爸若隐若现的文字里找到了爸爸离开的原因,她明白,爸爸是有苦衷的,是不得已的,而且是代人受过的。一种不平与愤慨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了,她心里几乎产生了一种要铲尽天下不平事的欲望。不是说‘十年磨一剑’吗?不是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吗?她暗下决心,她也要用十年的努力,磨出属于她自己的龙泉宝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