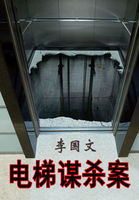二青慢慢地走到第二条街口,他感觉四肢无力,犹如大病初愈。他重新看到那个绿色的垃圾箱,两个多小时以前,他在这里啃掉一块又沙又甜的西瓜。他在路边坐下来,打开手里的钱包,却只翻找到五百块钱。五百块钱,可以买到三张回村子的火车票;或者,运气好的话,可以当成胜利住院的押金。
他在钱包里,发现了一张照片。
是一张合影。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男人浅浅地笑着,显出一副憨厚老实的模样。女人长得非常好看,眼睛又弯又长,又黑又亮。小女孩依偎在女人怀里,歪着头,两条可爱的小辫子高高翘起。忽然二青觉得那女人长得和胜利的女人有些像,那个小女孩长得和胜利的女儿秋妮有些像。这个发现让他吃惊不小,于是他死盯着照片看,结果越看越像。如果胜利的女人和女儿来到城里住上几年,肯定就是照片上的样子;或者把照片上的女人和女孩送到乡下晒几天太阳再换一身破衣烂衫,就会完全变成胜利的女人和女儿。再细看,那男人和胜利长得更像。如果胜利不是病倒,如果他刮去络腮胡子再穿上一件干净体面的衫衬,简直与照片上的男人难分彼此。二青端详着照片,心里有些害怕。他使劲眨了眨眼睛,再看那张照片,又觉得照片上的男人非常像他自己,照片上的女人和女孩非常像他的女人和女儿。仿佛他在一个未来的深夜里回到了现在,亲手用一把西瓜刀刺死已经在城里扎下根的胜利或者自己。二青把眼睛闭上很久,然后猛然睁开。他发现,照片上的三个人竟突然变了表情!他们仍然在冲他笑,只不过换成一种恶狠狠的狞笑或者意味深长的诡笑。二青惊恐地大叫一声,将钱包扔进垃圾箱。
这才发现双手沾满鲜血。
他从垃圾箱的旁边找到那块被他丢弃的西瓜皮,使劲地擦了擦手。西瓜皮很快被染成红色,就像那上面重新长出甜丝丝的瓜瓤。他脱下衣服,将湿漉漉的两手擦干净,将衣服也扔进垃圾箱。他揣好五百块钱,扶着垃圾箱站起来,再一次看到照片上的三个人。他慌忙闭上眼睛。他闭着眼睛往前走。他走得摇摇晃晃。
路在前方再一次变成 “丫”字形。往左拐,会到达一间即将拆掉的木板房;往右拐,会来到下午已经去过一次的火车站。他告诉自己说,往左。却踏上了往右的那条路。他对自己说:“往左!”脚下的步子却更快了。他越走越快,越走越快……他来到火车站广场,迈上广场台阶,走进售票厅。现在已是第二天凌晨,售票厅里人不是很多,他直奔窗口,隔着窗口上几根银亮的钢管问售票员:“今天有经过青石岭的火车吗?”
售票员头也没抬。 “有。”
他怔住了。“昨天下午我来的时候,你们告诉我五天之内的火车票全部卖空了。”
“有人退了两张票。”售票员仍然低着头,“要吗?”
“只有两张?”
“两张。要吗?”
他没有回答。两张票。大庆,胜利,他。三种可能。三十种可能。三百种可能。无限种可能。他呆立在窗口不动。
“买不买了?”后面的男人推推他,隔着他的身体冲窗口里的售票员喊,“去太原的票有吗?”
他往旁边让让,脑子里一片空白。那五百块钱似乎燃烧起来,将他的大腿烤出水泡。现在他不想买票了,他想回去,回到那个木板屋,看看即将死去或者正在死去或者已经死去的胜利,再和大庆喝点酒、唱首歌。
突然有人抱住他的腿,猛然向后抽拉。他的身体往前倒去,两只手在霎间抓住窗口上的两根钢管。抱住他的人将他的两条腿使劲往后拽,他的身体于是悬空并且被抻得很长。空中的他向窗口里的售票员大声喊:“两张!我要!”
突如其来的惊吓让售票员跳起来,缩到屋角。
“快给我票。我要!”他冲售票员大声叫嚷。他松开紧握钢管的一只手,伸进裤子口袋。“我要票!”他喊得歇斯底里。
又有几个人冲上来。有人往后拽他的腿,有人掰开他紧抓钢管的手。他的手被掰开,身体往下跌落。他的脑袋撞上坚硬的大理石窗台,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几个人将他摁倒在地,他像一只疯狂的野兽或者将杀的狗般挣扎。他把头高高昂起,冲窗口不停地叫喊:“我要票!”有人把他的手小心地从口袋里移出来,那手里,紧紧地攥着五百块钱。
戴上手铐时,他终于变得安静。他抬头冲一位警察笑笑,说:“西瓜涨价了。”
顿了顿,又说:“是生日蜡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