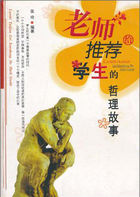天还没有亮,王小红就催妹妹起来。妹妹搓着惺忪的睡眼,嘟囔着:“我刚睡着。”王小红一把揭开妹妹的被子,把衣服和鞋子硬塞进她的怀里。“刚睡着也得起来,”王小红说,“去晚了,没准就没有那八钱炒面了。”
妹妹很快穿好了衣服,洗好了脸。她从一块三角形的碎玻璃片里看着自己,用一个缺了齿的木梳梳头。她和王小红每人喝掉一碗能照出人影的野菜粥,然后一前一后,出了村子。村子里很静,蛐蛐还在枯草丛里低鸣,那声音有点像田四婆子的呻吟,唧唧唧唧唧,痛苦,悲凉,刺得耳膜发痒。王小红知道村子里一会儿就该热闹了,只要不是卧床不起的老人,或者那些老人还有一丝挪动几里路的力气,都会在天亮以前,离开自己的村子。他们倾巢而出,像一群饥饿的蝗虫扑向几里以外的南泊村。这是他们的节日,所有人心花怒放。
南泊村紧靠着镇上。人多,地广,有山,有河,有让方圆几十里人们羡慕的泊地。种在泊地里的庄稼,总会比种在山地里的庄稼多收那么三到五成。饥荒年时饿死人是常有的事,可是南泊村硬是一个人也饿不死。因为南泊村有插根扫帚就能长成青竹的好泊地,因为南泊村有一位和蔼慈祥善良伟大的地主。
地主姓张,五十六岁。他有旱田五十五亩,水田十亩,骡马三匹,长工一个,宅院一处。这样的地主无疑有些寒酸,甚至亏对了地主这个雄伟的称号。可是没有办法,这里方圆几十里,自古以来就不出大地主。张地主本来也是普通的农民,他爹临死的时候,只留给他十亩旱田和一个破旧的宅院。可是他和他的婆娘硬是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把这十亩旱田变成了五十五亩旱田和十亩水田。听说他从来不吃细粮。他会把细粮一粒一粒地积攒起来,攒到一定的数量,直接跟别人兑换成土地。有时也会用现大洋买,他给那些农民开出了很高的价钱。这样的地主是很让人敬佩和爱戴的。谈起他,所有人都用了仰视和虔诚的表情。
张地主还是张善人。他总会给周围的乡邻分炒面。平常年月,一年分一次;遇上饥荒年,麦收前一个月,秋收前一个月,各分一次。炒面是在大铁锅里炒熟的面粉,装在几个纸糊的大簸箩里,由长工二愣把持着,分给四面八方涌来的人们。长工二愣右手捏一个玻璃酒盅,左手拿一根细细的竹筷,他把酒盅伸进簸箩,挖出满满一盅炒面,再拿竹筷轻轻一抹,把高出盅沿的炒面重新抹回簸箩。他把那一平盅炒面倒进你带来的碗里或者口袋里甚至直接张开的嘴巴里,脸上不会有任何表情。然后他盯着你的身后,叫,下一个。炒面是按人头分的,一人一盅。张地主说炒面是按嘴分的,一张嘴一盅,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有妇女领了小孩,或者怀里抱一个孩子,不管那孩子有多小,即使刚刚出生,只要有一张嘴,也能得到一个平盅。分炒面的二愣铁面无私,他从来不会多分给任何人一点点。他的眼也很尖,不管谁,只要从他面前经过,他都能过目不忘。你领了一盅,就别想混进队伍再领第二盅。有人这么干过,被他发现,他把对方往死里打。打死也是应该的。那是一种下贱的作弊行为,为人们所不齿。二愣分炒面的动作熟稔而又迅速。他从来不会忘记拿那根小竹筷抹一下手里的小酒盅。——有一次他娘来了,也得到那样一个平盅。那酒盅能装八钱酒,据说过年的时候,张地主会用它来喝点烧酒。八钱的酒盅能装下多少炒面?五钱?四钱?三钱?可是所有人都说那是八钱炒面。他们领了炒面,回到家,分一次,或者两次,或者三次,拿开水冲了,嗞嗞溜溜地喝,表情痛苦并且幸福。分炒面的日子,在街上遇了村人,问:“吃了吗?”对方肯定回答:“吃了,——八钱炒面。”分炒面的日子,村人放出来的屁都是香的。真是香的,你能够闻得到炒面的焦糊气味。别小看那八钱炒面,平常年月,可以打打牙祭。到了饥荒年月,那八钱炒面到底救活过多少乡邻,就没有人说得清了。
王小红和妹妹起了大早,就是为了去领那八钱炒面。两个人,一共能够领到一两六钱。二愣分的,肯定错不了。现在天刚蒙蒙亮,王小红和妹妹正在翻越一座小山。她们走得很慢,很艰难。山不高,却很险峻,即使在白天,也常有人从山坡上滚下去或者直接掉下峭壁。王小红紧拉着妹妹的手,小心翼翼地在山路上攀爬。山里雾气很重,那些浅紫色的雾气紧贴着地面,像一条稀薄的河,缓缓流动,甚至起着波澜。王小红今年十六岁,妹妹十二岁。王小红已经长成女人的形状,妹妹却根本不像十二岁的样子。说她十岁也有人信。说她八岁也有人信。她的个子很矮,身子很瘦,额头很宽,脑袋很大。
现在是秋天,这是张地主今年第二次放炒面。今年天气出奇得旱,方圆几十里的庄稼几乎全被烤成了灰烬,颗粒无收已成定局。能吃的几乎全都被吃光,狭窄的山路两旁,到处都是被剥掉皮的槐树和被撸光叶子的榆树。几年前这里也曾经历过一场大饥荒,一座山被啃得只剩下石头。那时王小红和妹妹都小。王小红记得娘不停地唠叨,“怎么还不放炒面呢?怎么还不放炒面呢?”后来她终于不再唠叨,因为她被饿死了。她是在放炒面的前一天饿死的,临死前她啃掉了自己的两根手指。她死后几个小时,王小红的爹也死了。骨瘦如柴气若游丝的王小红的爹高叫一声:“我的娘啊!”人就栽倒了,再也没有醒来。王小红一直感到很奇怪:一是爹和娘都饿死了,她和妹妹王小玲以及哥哥王小兵却都顽强地活了下来;二是爹在临死前,怎么也管娘叫娘呢?乱辈份了。
王小红的哥哥王小兵从没有领过张地主的炒面。他不去。他说就算饿死了也不会去。他承认张地主是个好人,他承认去领八钱炒面并不丢人,他什么都承认,就是不肯去。其实村子里还是有那么几个人不肯去领炒面,他们多是年轻人。有时他们会聚到一起,商量去镇上抢粮库。镇上和南泊村离得很近,赶上放炒面的日子,镇上的人们也都纷纷去南泊村排队领炒面。镇上有一个很大的圆锥形粮库,那粮库是军用的,据说那里面常年堆放着金灿灿的玉米和白花花的大米。常有人去抢粮库,只有抢粮库的声势,没有抢粮库的实质。一群衣衫褴褛的男人围着粮库,慢慢向前靠近。守粮库的兵就端起枪,大吼:“再往前就开枪啦!”人们马上就不动了。他们扇动着鼻子,贪婪地嗅着从粮库里散发出来的发霉的粮食味道。仅仅有一次,一个男人实在饿得受不了,竟然冲进了粮仓。
那天正好是晒粮的日子,粮库的木板门敞着,他就冲了进去。冲进去以前,兵端着枪,警告他:“再往前走就开枪啦!”他不理,继续前冲。兵拉一下枪栓,朝天开一枪,他仍然不理,仍然往前冲。两个兵一起向他瞄准,一起开了枪。他的肩膀和胸口同时中弹,可是他向前冲的速度丝毫没有减缓。终于他冲到了粮库的木板门前。把守着木板门的还有两个兵。一个兵端起枪向他瞄准,一个兵慌慌张张地关着木门。他赶在两扇木门关合以前冲进了粮仓,那一刹那,后面的三支枪同时射出了子弹。他扑倒在一条麻袋上,牙齿疯狂地撕咬着麻袋。他的后背全都是热乎乎的血,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窟窿。四个兵又一齐拉动枪栓,近在咫尺地瞄准他的脑袋。他没有理睬,继续啃咬着麻袋。麻袋被他啃破,雪白的大米流淌出来,在他的胸前堆成一座拳头大小的圆圆尖尖的小丘。然后四支枪同时响起,他的一大半脑袋就不见了。只剩一个下巴的他仍然用牙齿咔嚓咔嚓地啃嚼着麻袋。可是直到他变得冰凉,也没有一粒大米落进他的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