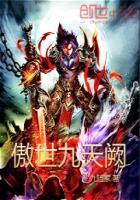我回到美美病房的时候,林童已经坐在了床边。她看见我,跳起来叫:“哇!姐夫!你也涂眼影啦!”
我心里一乐,说:“是啊,昨晚无聊,我用烟灰抹的。”
美美一下笑了出来,对我说:“你这烟灰可抹得真均匀,这几天累坏了吧。”
我说:“这点算啥呢,我正准备下楼给你买点汤。”
她笑容里满是幸福,好像我已经给她买了汤,说:“不用啦,林童来了,这会她陪我,你回去洗个澡睡个觉吧。”
林童也跳起来,抓着我的手,说:“姐夫,你回去休息吧,明天周末我不上课,我正好陪姐姐呢。”
她们这样说,我倒觉得真有些困了。我说:“好吧,你们可不要聊太晚哦,美美的身体要紧。”
美美笑着说:“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女人啦,真啰嗦……你就安心地回去吧,它也陪着我,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啦。”
她说着,摸了摸床头的婚纱裙,好像那就是我一样。
我对她说:“好吧,那我明天过来,你想吃什么就叫林童给我打电话”
我走出从医院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经过回学校的路,看见沿途暗淡的路灯光,光亮照不到的地方,是极致的黑暗。光亮和黑暗、快乐与悲伤,热闹跟寂寥……人类发明的形容词都带着极端的属性,那是因为人类本就是极端和歇斯底里的,他们会把各种本来不大的情绪放到最大,并不断强调,所以,我们的世界常常只有两面。我们站在其中,却分不清某一刻自己的情绪该如何形容。
此时的我,毫无困意,我看了看若水酒吧的方向,再看了看学校,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我突然想起我在医院里一直把手机设置成静音,摸出手机看,十多个未接电话,全是王明君打来的。不知为何,我突然有些想看到她,我回拨过去,响了很久她才接听。
电话那头只有她的抽泣声。
我问:“你怎么了?”
她一边抽泣一边说:“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这么久都不接……我在旅馆里等了你几天,以为你最近忙,忙过了会来找我,但是你没有……我就一直打你的电话,一直打一直打……师哥,你好像蒸发了一样,我好怕,我好想哭,我好想你……”
我说不出话来,我觉得我亏欠她。
她继续哭着,用尽力气地抽泣。
我小声说:“你在哪?我马上过来。”
她说:“我在旅馆……我一直在旅馆,我一直在等你……”
我就挂掉了电话,向旅馆的方向跑去。经过若水酒吧门外,听见了里面的欢声笑语,也看见了里面的灯红酒绿,我突然觉得它已离我很遥远了。
我敲开旅馆二楼最里间的门,看见了她哭红的眼。在我关门的时候,她从身后将我抱住,不停地哭,我的背有被湿透的感觉。
“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等你?”她问。
“嗯,我知道。”我说。
她狠狠地摇头,说:“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想起过我!”
我承认我这几天很少想起她,而此刻她抱着我,我能感觉到,我想的也竟然不是她。
“对不起,这几天我太忙了,我想过你,但没时间过来。”我撒谎说。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我好怕!”她又努力地哭起来。
我拿着她的手,慢慢转身,她顺势倒进我的怀里。
“师哥,你知不知道我好怕……我怕见不到你了……”她说:“见不到你,我才知道我好想你。”
“对不起。”我说:“剧团的副团长受伤住院了,他就是接替张志超角色的,这几天我都在医院陪他。”
“真的么?”她瞪大眼睛看着我,半信半疑地问:“他怎么受伤的呢?”
我说:“车祸,他走在马路上,一辆车飞过来,全身的好骨头没剩下多少了。”
“啊!”她惊愕地看着我:“他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还好……”我说:“虽然伤得不轻,但都是骨头上的伤,不危及性命,不过要很久才能好。”
“哦……”她点点头,表情里带着不可思议,她问:“那你们的戏怎么办啊?”
我说:“我就是正在愁这事呢,不过现在办好了,我另一个朋友来顶,他来演王子。”
“哎……”她叹了口气,说:“都怪志超不好,让你们受了这么多累……戏剧节就快到了,你们现在换人怎么来得及啊?”
“不换也没办法,总不可能叫王子坐个轮椅上台吧……”我笑着说:“那就成荒诞剧了。”
她突然笑了起来,刚刚痛哭过后的笑声听起来还挺可爱。
我说:“笑就好啦……最近我肯定会比较忙,每天都得去医院照顾朋友,还要继续排戏。”
“嗯,我知道。”她点头,又将我抱紧,说:“师哥,只要你想着我就好,你去忙你的事吧,有空就来看我。”
我点点头,打了个哈欠,突然觉得疲倦了。
她说:“师哥,你这几天肯定累坏了,今晚早点睡吧。”
我说:“是啊,终于可以睡了好觉了,不然我真的快崩溃了。”
她松开抱着我的手,看着我说:“你去洗澡吧,我洗过了……我等你。”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但我并没有那样的想法。那一晚之后的我和她,已经无法再明晰对于彼此的身份,但那次事件,更像是两条平行线因为时空重叠所产生的一个交点,是一次意外。身份、性格、未来……太多的因素注定了那只是个意外。我很清楚我已经明白,我也清楚她正在深陷。这个刚刚失恋的女生,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那我对她而言,又究竟是个什么呢?想起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一切,犹如梦幻。
我说:“我想回宿舍睡觉。”
她面带惊奇第看着我,问:“师哥,你不是来看我的么?怎么又要走呢?”
我说:“这几天事情太多,有些累,想安静地睡会。”
她突然冲到我的前面,挡住门,焦急地说:“师哥!你别走啊!我求求你了!我天天都在等你来,你不要走好么!”
她一急,眼泪又快要流出来。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王明君简直是纯净水做的。我轻轻搂过她的肩膀,说:“别哭,我又不是不来了,我明天再来看你好吗?”
她看着我,摇头,说:“师哥,为什么我们之间还要分得那么清楚啊……你就在这里睡好么……我不打搅你,我能看着你就够了。”
我们俩,的确连男女之间最深层的那堵墙都已经不复存在。通常的两个人,都是由外而内慢慢打开心墙。若是直接发生关系的,往往都是****发生过后不再有关联。而我和她的关系,却像是本末倒置地发展着,一不小心就濒临深陷。我很清楚,我们之间除了性,其他方面仍然距离遥远,根本不在同一空间。
“师哥,你过了今晚再走好不好?我求求你了!”她泪眼婆娑地看着我。
我不知怎么拒绝这个纯净水做的女人,环顾屋子,电视机里正播着体育频道的节目预告。
“嗯。”我点点头,说:“我去洗澡,看完球赛就睡。”
她不说话,将头埋入我的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