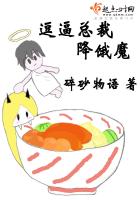余洪突然拔剑对着东宁雪道:“老夫为赤风征战多年,不能眼见王朝在我眼前覆灭,国师……交出麒麟金印,随我回赤风领罪。”
东宁雪望着余洪,一步步的逼近他的剑尖,眼中没有半分的惧怕,东宁雪抬手之间,林显以为她要对余洪动手竟也不自觉的拔了剑,可她并没有对余洪出手,只是徒手握住了余洪的剑尖,将那利刃带到了自己的心口,“余将军,雪原一战穆世怀可是如我这般以心口对敌,为你挡剑的?”
余洪的剑抖了抖,他难以置信的看着眼前不过二十多岁的女子,漆黑的瞳孔中似乎如亲眼所见那场旷日持久的苦战一般,那时的他也不过二十出头的少年,雪原之战主帅是穆世怀穆大将军,那时他年轻气盛自负剑术卓绝,没有上报主帅便擅自带了三百人去偷袭敌军,不曾想竟中了敌军的奸计,深入敌营不得支援,苦战至最后一刻时敌军的利剑本要一剑刺入他的胸膛,可是最后他活了下来,因为穆世怀带兵赶到,更是在千钧一发之际为他挡了那一剑,时隔多年,知晓此事的人大多都已埋了黄土,余洪的剑终是缓缓地放了下去,“你是从何处知道那场战役的?”
东宁雪没有回答他,反而是转向林显,那里也有一柄正对着他的利剑,“瑞山剿灭叛党,林威将军为救自己那个好胜的儿子,带兵强攻叛军营地,最后被困于山沟之下,险些被叛军以火油烧之,穆家少帅用三千头野猪挡下了叛军浇灌的火油,最终野猪携带着烈火冲入叛军营地,叛党尽数除去。”
林显声音有些颤抖,问道:“你……是谁?”
“若我记得没错,林显将军那时因好大喜功险些害的全军覆没,按军法处置是要判腰斩之刑的,穆家少帅念及昔日征战情谊便将野猪克敌之法的功劳都给了将军,将军也借此功过相抵一路走到了今天的位置。”
这件事本就十分隐秘,除了穆子风以外便再没有人知道,林显突然弃了剑,问道:“你……你是子风?”
见他竟将自己这女子之身联想到了穆子风的身上,东宁雪心中便已确定,“你果然早就知道了穆子风本是女儿身。”
余洪震惊道:“什么?穆家少帅竟是个女子。”
林显突然手足无措般上前拉住东宁雪的手,“你真的是子风?”
明月台移步上前,狠狠地打落了林显的手,顺势看了看她方才握住剑刃的伤口,林显正欲上前却听他冷声道:“你再碰她,我砍死你。”
随后一边给她包扎着伤口,“穆家救的人可真多,可一个个最后都成了白眼狼。”
东宁雪仍他包扎着,抬眼看着林显,话却是对他和余洪说的,“穆世怀是我的父亲,穆子风是我的姐姐,我是那个被穆家藏得很好也护得很好的穆子游,穆家灭门后许久不曾用过这个名字了,那一年,我将父母和姐姐的尸首葬到了东倾林里,那里与赤风皇城遥遥相望,我在墓前立誓,要让赤风皇族对着东倾林三跪九叩,以血还血、以命还命,祭奠我穆氏全族。”
那一年,东倾林里藏了一笔血债,她自林中走出时,便取了名字,唤自己东宁雪。
穆世怀的女儿,穆子风的妹妹,面对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穆家人,余洪和林显早已说不出任何的话来,当年的穆氏灭门有多惨烈,他们是亲眼见过的,穆府的嘶吼悲鸣之声他们即便忌于皇权夜里似乎也能听到,可他们无能为力,也是因为那一份无能为力,他们此刻面对东宁雪才会显得有些无地自容,而到了此刻,谁还敢说穆家的谋逆之罪呢?
何来的谋逆,不过是皇室的欲加之罪,而终究无人敢于质疑皇室威严。
就在此时,被四路护法从密道带入青城的三军主将沈文昌一身甲胄大步行来,他似三十出头的年纪,一脸肃色的看了看东宁雪后问道:“你便是穆大将军的女儿?”
东宁雪见了他重重地行了一礼,“穆子游见过忠义将军。”
沈文昌重重地叹了口气,“许久……许久不曾有人唤我‘忠义’二字了。”
东宁雪道:“父亲和将军在怀城赈灾的路上突遇山崩,是将军不顾危险亲手将父亲从山石挖出的,父亲曾言,文昌当得‘忠义’二字。”
“我自小便与你父亲上了战场,那时朝局动荡,沈家一门忠烈被奸臣暗算,是你的父亲将沈氏一族力保了下来,后来穆家被冠上了谋逆之名,穆家灭门时我身处云川边境,待我快马赶回时,赤风早已再无穆家,父亲为了不让沈氏如穆家一般被皇族连根拔起,便找了夜氏为倚靠,我那时一心想为穆家平反却遭家族遗弃,后来夜氏与宗政皇族争斗剧烈,沈氏一门直系男儿都成了两族相斗的炮灰,父亲以死相逼将夜氏三军交到了我的手里。”
东宁雪重重地说道:“若我要带浴火重生的穆家军血洗皇族,灭了夜氏,你可会阻我?”
沈文昌突然卸下了身上的甲胄,将随身携带的将印交出,“我身后的三军为赤风之兵,我身为主将无法无法悖逆誓言带他们夺宫,但我沈文昌一生只认穆家为主,当年血渍何其惨烈,文昌随穆家少主,为穆大将军讨回这血债。”说完,他重重地朝着东宁雪跪了下去,余洪和林显见此也如沈文昌一般,交出了自己的军印,叩首道:“军不动,人愿随少主,讨回血债。”
东宁雪将三人扶起,一声令下,“好——入皇城,祭穆府。”
东宁雪带着一万穆家军直奔赤风都城,昼夜奔波马不停蹄终是到了这座皇城,城楼之上已然换防,本以为会是云川的军旗,但当东宁雪一行人到达城楼之下时,没有刀剑搏杀,一派祥和,唯有穆氏军旗飞扬在空中,为英雄、为冤屈、为穆氏亡魂。
孙小童一身戎装率兵而出,余洪、林显和沈文昌皆是一副戒备的模样,手握利剑毫不松懈,东宁雪驱马上前,却见孙小童将手中冰刃放于一旁,率身后士兵对着东宁雪重重地跪了下去,一字一句,铿锵有力,“穆氏虎威将军孙武领穆军虎威营见过少主——”
东宁雪下马将他扶起,“这些年辛苦你了。”
孙小童摇头道:“不辛苦,若非少主筹谋多年,我和穆家军又怎能这般正大光明的重回赤风。”
东宁雪怕了拍他的肩膀,“好——穆家男儿郎从未令我失望。”
孙小童带着一行人往皇宫行去,他对东宁雪说道:“我遵少主的令,只派兵将皇宫围住,不得放走一人,宗政家和夜氏但凡参与到穆家灭门之中的皆我送了进去。”
东宁雪道:“开了祭天台,将宗政焘和夜清兰带过去,宣满朝文武,我要开朝升堂……问君罪责。”
四大朝钟敲响,祭天台开,穆氏一门先烈的灵位皆被奉到了祭天台上,东宁雪卸下了易容之术,露出本来面目,她穿上了穆子风的少帅戎装,长发束起,银冠高戴,一双美目,坚定不移的看着正一步步朝着这祭天台走来的宗政焘和夜清兰。
直至两人走上了这祭天台,满朝文武皆站于两旁,当他们看到穆家军旗时数年前的惨案似又重现于眼前,再看那正中央英气逼人的女子,眉眼间竟与死去的穆家少帅有六七分相像,他们终于隐隐开始明白,原来是讨债来了,向皇族讨债,古来首例。
宗政焘初见东宁雪时,眼中难以置信,是惊怒是窃喜他已然无法分辨,只是颤抖着的手指着她,问道:“你是……东宁雪……”
东宁雪三个字闻名遐迩,长丘第一女太傅,也是长丘故去的皇后,下葬之时,长丘国君以龙袍随棺入葬传至三国。
东宁雪道:“你口中的那人三年前就死了,如今怕是尸首都腐蚀成了白骨,我又怎会是她呢?”
倒是夜清兰此时比他冷静得多,她咬着牙愤恨道:“你……你是夜沙……我容你,信你,更是将军权交于你,而你……便是这般报答我的吗?夜沙……你要叛国夺位吗?”
夜太后无疑是精明的,她一眼便认出了东宁雪,倒是站在百官之中的夜沉听见她这般说,神色复杂的看向东宁雪,那个面目黝黑的无盐之女竟会是眼前这个穆家军的少主,召文武百官在祭天台上审一国之君的女子吗?
他不敢相信亦或是不愿相信。
东宁雪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对夜清兰道:“我叫穆子游,夜沙之名为的不过是弑杀你夜氏一族,穆氏一门忠烈遭皇室忌惮功高盖主,欲加谋逆之罪灭了满门,那一日……三十万穆家军浴血奋战平了云川的作乱,不曾想回城之时竟是九族尽诛之祸——”
她一步步走近夜清兰身边,铿锵有力的说道:“你夜清兰,堂堂一国太后阴险毒辣,为逼我父亲穆世怀就范,你下旨将母亲请到了静夜宫,本可以一杯鸩酒将她了结,你却嫉妒她于百姓之中活菩萨的美誉,乱棍将她活活打死弃于枯井之中……”说及此出东宁雪声音有些沙哑,眼中早已噙满了愤恨的眼泪。
听到此处的百官心中也不无震惊,穆夫人心善之名在赤风广为流传,虽为将军夫人却时时一身布衣,广开善堂,百姓受她恩惠之人众多,当年死于宫中,传闻是她毒杀太后为了和自己的夫君里应外合,最后被夜氏暗卫一剑毙命,当时朝中很多大臣虽觉得毒杀一事疑点甚多可是没有一人为穆家多言一句,更不知道这位心善的穆夫人竟是这般惨死于深宫之中,如今听她的女儿一字一句的说出来,诸多大臣不免唏嘘。
随后东宁雪又将目光转向宗政焘,“你初登大宝之时是我父亲力排众议奉你为主,你出宫狩猎落马之时,是我父亲以身为垫将你护下,就连你手中那原本的三军之权也是我父亲以整个穆家军威逼夜氏让给你的,赤风大大小小的战役皆由父亲率军出征为你保得赤风太平,我的姐姐穆子风瞒下女子之身为你宗政皇族沙场拼杀,全身上下共有十六处剑伤,八处刀伤,三次命在旦夕,而你却在他们与云川交战之际,断了他们的粮草又不给他们任何支援,三十万穆家军对阵五十万的云川大军,最终他们拼死搏杀以少胜多为你解了边境之忧,可三十万穆家军疲惫不堪的回城时,迎接他们的不是举国欢庆,不是皇家的犒赏,而是冰冷的箭雨,全力的绞杀,父亲被你乱箭射死,穆府被你火烧干净,就连苦苦逃出的穆子风被你的十八血骑一刀破腹,穆家除我之外倒当真被你灭了个干净,不知夜夜梦回时可曾见过他们。”
宗政焘颓然的退了几步,倒是被夜清兰给拉住,“没出息的东西,你威胁我时的狠辣都到哪去了?”
宗政焘似在想着什么,脸色苍白的说道:“我竟忘了……穆世怀曾……救过我……”
夜清兰不再理他,横眉冷对的看着东宁雪,“穆家手揽军权本就犯了我皇室大忌,手握重兵谋逆本就是早晚的事,杀他为的是保我赤风皇族安稳。”
东宁雪伸手掐住她的脖颈,“手握重兵?若非你夜氏和宗政家都是些胆小怕死的鼠辈,我父亲何必要那军权,时时上阵杀敌,云川之战后,我父亲本是要辞官归隐的。”
夜清兰不相信的摇头,“不……可能……军权在手……你父亲……怎会……轻易……放权。”
东宁雪道:“你们争来夺去的麒零金印在我父亲眼中不过一块破石头。”
东宁雪指着对面的山峰,道:“祭天台和东倾林遥遥相望,我将父母和姐姐都葬在了那里,此刻他们都看着,看着你们三跪九叩,以命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