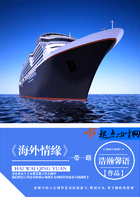五日后,三秦泗水郡,雾隐城。
终日笼罩着泗水湖的水雾中,缓缓驶来一叶轻舟,船夫轻轻摇曳着船桨,划呀划的,向着泗水郡水师大营外港靠近。
旂岳站在轻舟上,望着渐渐显露出来的水师战船,黑色旗帜猎猎而舞,仿佛一座座停泊在湖面上的城堡一般。
远远的地方,似还有飞禽掠过,扑腾着翅膀落到水面之上,昂头向四周张望几下,然后惬意地合起双翅,在水面轻轻游动。
殴冶流云走了过来,把手搭在旂岳的肩上,忽地一笑,道:“这就是三秦王朝的水师大营了,怎么样,很壮观吧!”
旂岳没有笑,也没有说话,因为昨天遇到的一幕情景,让他对个国家的统治阶层有些不耻,他想不通御剑门为什么要去守护这样的统治者。
昨日途径一座山麓脚下时,这师叔侄二人遇到一个怪人,那人衣衫褴楼,满身都是泥污,也不知在深山老林中藏了多久,胡子头发长得老长,把他的脸遮住了。
那怪人疯疯癫癫的,一见到旂岳便问他:“长城筑完乎?秦贤皇还在吗?”
当时旂岳没反应过来,殴冶流云只对那怪人说了句“长城未筑完,秦贤皇还在”,结果直接把怪人给吓跑了。
想来那怪人一定是为了逃避劳役的民夫,由于躲入深山老林,年长日久,就变成了那副模样。
不多时,轻舟已经靠上了岸边,师叔侄二人刚踏上港口的码头,立刻便被一众水师官兵给拦下了。
殴冶流云对眼前情况也并不出乎意料之外,作为州郡水师大营的港口,若没有严加戒备,反而奇怪了。
但港口上的水师将士着实不少,一眼看去,至少也有千百来个精壮男子,或远或近地站在通往城内的道路上警戒着,此时拦住他们二人的是站在最前面的一队水师将士,他们身上穿着盔甲,头盔上插着一支黑色羽毛,手中持着弓弩而非长枪,看来这就是水师将士和骑兵的区别了。
其中一名校尉上上下下打量了旂岳和殴冶流云几眼,然后大声道:“此港渡口已经关闭,任何人不得靠岸!”
殴冶流云朗朗一笑,道:“在下御剑门殴冶流云,还请行个方便!”
刹那间,众水师将士一片哗然。
听到殴冶流云表明身份,那水师校尉更是紧紧皱眉,却是连手中弓弩也拿了起来,面色严肃,对身旁一名士兵道:“快,去把邓都统请来!”
殴冶流云哑然,朝廷对御剑门一向都很尊敬,现在这样的态度,显然是不大友好的,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旂岳还是不知世事的少年,但也知道此刻万万不能冲动。
如此,他们二人被围了半响,正心中烦躁无比时,殴冶流云都想直接出手打翻这些人了,忽然看到一队轻骑朝这边飞奔过来。
为首的是一名年轻的女将军,一身战甲好不威风,周围的士兵纷纷行礼,她一边打量着旂岳和殴冶流云,一边听着校尉的禀报:“副都统,这两个人自称是御剑门的修真弟子,要不要把他们拿下!”
殴冶流云一怔,旂岳也颇为不解,他们自打上岸以来,什么都没做过,也没得罪什么人,可这些水师却要把他们拿下,却不知这是什么情况。
虽然这些将士根本拿不住殴冶流云,但他也不想和他们发生误会,只得对那名女将军道:“我们只是路过而已,想请将军行个方便,如果将军不方便,我们自己走便是!”
这名女将军听到殴冶流云说话,突然眉头一皱,上上下下又仔细打量了他们二人几眼,忍不住又确定似地问道:“你们真的只是路过,不是朝廷派遣来的?”
殴冶流云已察觉这里很可能要发生一场兵变,他不动声色道:“御剑门是江湖势力,朝廷对我师门有所倚仗,但也未必就任由驱役,皇帝连请都请不动,又何来派遣一说!”
女将军和水师们都是一惊,随即大喜,然后,她对殴冶流云和旂岳也解除了敌意,连忙对校尉吩咐道:“去准备两匹最快的马!”
殴冶流云抱拳道:“多谢了!”
女将军端坐在马背上,手握着一支银色长枪,向身后的城池一指,道:“一会儿本都统也要进城,正好可以送送你们,以免我的兄弟们对你们产生误会!”
殴冶流云点点头,什么都没问,这时校尉已牵来两匹战马,他当先翻上了马背,旂岳没骑过马,也学了师叔的样子翻身上马,那马儿悠悠地踏了两步,旂岳只觉得坐在马背上竟十分舒服。
女将军一仰首,道:“二位请!”
殴冶流云也客气地道:“将军请!”
说着,他们二人便引马向城池走去,只是才走了没多远,殴冶流云忽然发现后面的旂岳没有跟上来,回头一看,不禁莞尔,只见自己这位师侄正骑着马在原地绕圈子,已经急的满头大汗了。
女将军也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当下催马掉过头去,对旂岳道:“这位小少侠,想来是高来高去惯了,不通骑术吧!”
旂岳面色一红,没有作声,也不知为何,自己身下这匹马儿仿佛诚心让他出笑话一般,就是不肯走直线,绕得他头都晕了。
女将军笑了一阵,忽地双足一点镫子,直接从自己的战马上飞身而起,眨眼间就已落在旂岳的身后,与他同乘一骑。
仿佛一种异样的温柔,在他的身后,散发了出来。
旂岳有些微微的紧张,只见她身子一倾,便抓住了自己握着缰绳的手,马儿立刻不再转圈了。
他定了定神,只听女将军道:“要想马儿听话,其实并不难!”
女将军说罢,双腿一磕马腹,马儿便迈开了步子,随着她缰绳向右一偏,马儿就向右边走,向左偏,马儿就转左,猛地一拉缰绳,马儿立即四蹄皆定,旂岳恍然大悟,原来骑马是如此简单的事。
女将军为了让旂岳更快的领悟骑术诀窍,索性与他同乘一骑,纵马狂奔,一路沙土飞扬。
旂岳在驰聘中回忆起童年时候,他依偎在爹爹身前,于马背上不停地颠簸的情景,一时触动情怀,忍不住向身后靠去。
女将军起先还不觉得什么,可渐渐地,她察觉到身前的少年有些不太安份,不过对方毕竟只是个少年,而且还穿了一身僧袍,似乎也没有特别过份的举动,就不动声色地忍了下来。
很快众人奔到城门口方才停下,后面的殴冶流云也追赶上来,他看到眼前的情景,更加证实了心中猜想。
此时的雾隐城如临大敌一般,有上千名水师将士戒严城门,许多百姓都背着包袱,或推着小车向城外逃命,一场州郡割据的兵变,一触即发。
女将军刚跃下马背,不远处一名骑兵快报而来,慌慌张张地道:“副都统,朝廷的黑旗水师已经开来,不下十万之众,战船七百余艘,我们很多兄弟拖家带口的,不愿意跟着我们一起造反,您看怎么办啊!”
旂岳心里一紧,向身旁看了过去,只见女将军却没有什么反应,身影一动不动,也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
部下的战马不停地踏着步子,似乎情势已经十分危急,那种大祸临头的气氛旂岳也能感觉得到,只是等了许久,却依然不见女将军开口说话,那名骑兵这才有些迟疑地道:“副都统,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不如封锁城门,挟持这些百姓,朝廷必然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
女将军依旧沉默着,一句话也没有说。
旂岳和殴冶流云也不禁为她着急,良久后,女将军似乎也是在经过长久复杂的思考之后,才慢慢说出了话。
“这是我们邓王府和朝廷的恩怨,没必要连累这些无辜的人!”
殴冶流云在一旁,眼光落到女将军的脸庞上,看着这个隐隐凄凉和穷途末路的女子,没想到她就是邓世荣之女——灵风郡主。
他轻轻叹息,奉劝了一句:“灵风郡主,本来在下不便介入朝廷纷争,但在下还是希望郡主能悬崖勒马,毕竟朝廷兵强马壮,以一国之力敌一郡之变,自然不在话下!”
女将军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却又摇着头,苦笑一声,道:“朝廷无义,官逼民反,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殴冶流云也不再多说什么,道声“后会有期”,一引缰绳,策马入了城池。
旂岳静静地注视着女将军,曾几何时,这样的处境自己也曾面对过,他不由抬起头,望着城池上“雾隐城”三个字,此刻仿佛也变成了“陨君镇”。
他清澈的眼中蕴含了些许无奈与惆怅,轻轻道了句:“明知结果而执意为之,称之为勇,明知不该为而为之,称之为罪!”
女将军正黯然伤神的时候,同时心中不知怎么,回味着旂岳刚才话里意思,这“勇和罪”两字慢慢回荡在心头,她望着眼前如霜一般的僧袍少年,一时茫然。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旂岳听到殴冶流云催促的声音,他默然了片刻,脸上风云变幻,终于慢慢摇头,挥起马鞭,不再看身后的女将军。
生命,仿佛是无数次的相遇和邂逅的星空,当四年之后,他们再次相遇的时候,他已经是朝廷的二品军机刺史,但她却已沦落为匪。
欧冶流云和旂岳这师叔侄从天龙寺出发,一路御空向西北,所过之处的名山大川无数,风景如画。
欧冶流云虽有闲心去游山观水,但旂岳对此毫无眷恋,一心急着赶路,对师门中事也不曾问及,一路上沉默寡言,才十日时间就已到了秦淮郡汉阳城附近的一处小镇。
在此处滞留,其实是为了避嫌,因为旂岳身上还穿着僧袍,若让人看到御剑门有个穿僧袍的门人,恐对两派名声不利。
这师叔侄二人便暂且停留,为旂岳购置了新的衣裳,这才继续向汉阳都城方向赶路,距离咸阳城还有一二里地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疑是龙卧于陆的百丈城墙,城池上兵甲卫立,王旗飘卷,巍严壮观。
反正到这里也离御剑峰不远了,天黑之前定能到达,正好可以在这天下第一繁华之都游玩一番。
旂岳虽然还没见识过人间人口最密集的都城,不过他并没有这等闲情逸致,又不好扫了师叔的兴致,只得默默地骑马跟在后面。
欧冶流云望着前方巨大城墙的轮廓,口中滔滔不绝地向他介绍着汉阳城:
“普天之下,三秦王朝的都城是最大最繁华的所在,住在这汉阳城里的百姓少说有一百四十万人,流动百姓也有二十万人,就算夜晚也极是热闹!”
旂岳听着听着,心中着实佩服他的博学多识,忍不住开口道:“流云师叔,你怎么什么都知道的这么清楚?”
欧冶流云神色如常,道:“这有什么,你师叔我游厉千山万水,足迹遍布各地,什么好玩的好吃的都见过了。”
这十几日相处下来,欧冶流云发现自己这位师侄性情说不出冷淡,便想逗他一逗,说着面露诡笑,偷偷附耳到旂岳耳边,低声道:“这都城里有许多家青楼,一到晚上歌舞辉煌,美人儿如玉,你想不想去寻一位红颜?”
旂岳只是皱了皱眉,道:“流云师叔!红颜即是枯骨,****之心不可得啊!”
欧冶流云当即怔住,本想看看旂岳惊吓的反应,却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番话,苦笑了一声,撇眉道:“这有什么!男欢女爱本是人之常情,我们修真之人随萍浮沉,自然难绝红尘六欲,你应该多学学师叔我!”
言罢,他放浪形骸的一声畅笑。
旂岳为之哑然。
汉阳商贾不绝,东临九江郡,南依南海瑶池屿,西靠巍峨御剑峰,北达蓟北郡治,富奢甲于天下。
旂岳和欧冶流云走在热闹之中,他们二人都是一袭白衣,天底下绝不多见的风流俊俏人物,不同是后者风清云淡,从容不迫,对这人间繁华淡然视之。
一路行来,周围叫卖声此起彼伏,沿街的摊位周围都围满了人,画舫在湖上游行,一眼看不到尽头的繁华街景。
欧冶流云眼中含笑地看着这个少年俊逸的师侄,正要介绍一些好玩的,忽然一阵鸡飞狗跳的声音,蹄声得儿得儿,从前方处传来。
二人扭头一看,不由惊得失色,只见一蹒跚而行的孩童正站在路中央,而城门外,突然奔进两匹快马,竟然就在这城中大街之上横冲直撞,孩童却对突然其来的冲撞显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竟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不躲也不惧。
也不知是谁家大人这般粗心,放任幼童一个人在街上游荡,欧冶流云来不及多想,正要上前施救,但此时街上行人自顾奔走,都唯恐避祸不及,使得道路更加拥挤,眼看幼童就要命丧马蹄之下,他竟是无法突出。
千钧一发之际,却听到一阵马匹的长嘶,那马蹄就在幼童面前半尺蓦然昂起,一个少年已抢身护在了幼童身前。
马上的蓝衣女子控缰而立,急忙调转马头,但已然已经来不及了,马蹄踏下,蹄铁踩在少年的肩头,硬是把他踏倒在了地上。
经过这么微微的一滞,欧冶流云立刻飞身而起,将受伤的少年连同幼童拉出马蹄范围少许,但此时马儿也受到惊吓,前蹄再次跃起。
便在这时,一个衣袂胜雪的身影快速奔闪了过来,在马蹄即将对少年造成二次踩踏的时候,旂岳迎身而至,挡在了铁蹄之前。
他有九龙真气护体,马蹄踏在他胸前的无形气罩上,竟是被反弹开来,几乎呈直立之姿,鞍背垂直倾斜。
只听得一声娇呼,女子已从马背摔落,却是身如轻燕,从容不迫的落地,在站稳身形后,她满面怒色地用力瞪着旂岳。
而那匹通体雪白,仿佛一团云花似的白马能在巨大反弹之力下调整身姿,四蹄稳拔地面,端地神骏异常。
蓝衣女子身侧是一个骑着枣红大马的羽林护卫,腰佩跨刀,此刻正挥舞著马鞭,指著旂岳破口大骂:“大胆!竟敢冲撞国师千金的白龙驹,你小子找死么?”
旂岳神色一扬,神情傲然冷漠,看也不看那护卫一眼,转身去查看少年的伤势,道:“你没事吧!”
“没事!”
少年嘴上说没事,揉了揉被马蹄踩踏过的肩背,还是疼得皱眉,倒吸一口凉气,但当他看到被自己护住的幼童安然无恙时,脸上不由露出了笑容。
那护卫似是想不到居然还敢有人在他们面前一副不屑的样子,忍不住再次挥舞著马鞭,便欲上前问罪,不料身边那蓝衣女子忽然伸鞭隔住他,道:“且慢动手,容本郡主问问他们再说。”
女子冷颜道:“你们可是御剑峰上的人?”
欧冶流云回身去看那肇事的国师千金,见她二十五六岁年纪,非但没有丝毫愧疚之意,反而凤目凝霜,正要代替凌正钦教训一番时,又看到了她腰间的银色铃铛,那宫铃正是瑶池宫所佩之物。
欧冶流云似乎突然之间想到什么,又变得平静下来,只淡淡道:“正是!”
不料女子伸出马鞭,指著欧冶流云道:“御剑门又如何?我爹是三秦王朝护国国师,秦淮郡郡王,我师傅是瑶池宫九缨仙子,你们惊吓到了本郡主的爱马,还不快过来赔礼?”
欧冶流云摇头一笑,道:“真是跟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也不知九缨的凌波剑法你学了几成下来,她那一身傲气你倒是学了七八分,如此傲慢无礼,将来如何嫁人?”
“你...”
女子一时羞愤难忍,手捏法诀,一把紫青长剑夺鞘祭出,被她握在了手中,剑锋所指,紫气萦绕。
周围围观百姓虽然不知其厉,但也看出这是仙家法宝,一阵惊呼连连。
欧冶流云微一凝目,脱口道:“神兵紫霞!”
女子面冷似霜,道:“看来你还有点见识,你不是想知道凌波剑法我学了几成吗?今天就让你开开眼!”
这时四周众人都纷纷避开唯恐不及,因为生活在汉阳城中的人莫不知道,得罪三秦国师凌正钦不要紧,因为以他的身份地位,是不屑与寻常百姓为难的,但千万不要惹上他的独生爱女凌馨儿。
这凌馨儿自小即是非常顽劣,请了多少老师都被她整得面目全非,从来没有能待上半个月之久的,为此凌正钦费尽心机,不知请来多少饱学大儒,可最后再也没人敢来教这位任性郡主的功课了,那些知名儒者一听到是请他们去国师府教授语月郡主功课,俱是如避蛇蝎,便是千金相酬,也绝不敢应。
凌正钦无奈,只得自己教授女儿功课,发现她对四书五经兴趣索然,却对舞刀弄棒情有独钟,整日里缠着自己要上阵杀敌,有时缠得紧了,连他都被自己这个女儿弄得哭笑不得,但他又如何肯放任自己的宝贝女儿去征战沙场?干脆送她去拜师修真算了。
就这样,凌正钦开始四处为女儿求师拜山,御剑门是他看重所有修真门派中的不二之选,奈何御剑门从不收女弟子,天龙寺就更不用提了,而七绝殿行事诡异莫测,逍遥阁也有欠妥当,剩下的就是瑶池宫了,九缨仙子虽性情孤傲,却也没有拂了他的面子,便将凌馨儿收于了门下。
凌馨儿这一走就是十年,今天正好是她回家探亲的日子,离别十年,思亲之切,这才做出白日纵马狂奔闹市的事情,但因一贯争强好胜的性子使然,她宁愿是错,也要错得理直气壮。
何况,对方还是御剑门的人,她可是记得清楚,十年前天极真人把自己婉拒于外的情景,而瑶池也一向与御剑门有互相较劲的意思。
御剑门这天下第一御剑大派的名号,瑶池宫可是一直都不服的,刚才又被欧冶流云出言激恼,她便要在今日为师门争一口气,为自己也出上一口恶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