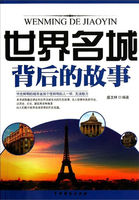楚宣王熊良夫边下楼梯边说道:“不知无强遗身安放何处?寡人正好去祭奠一番。”
郑圆答道:“先王新去,未至祖庭之所,故未及设立灵堂,不便楚王祭拜,还望楚王见谅。”
熊良夫不置可否,微微转了转身子,把客栈四周打量了一番,看向了陈嵊,眼睛一眯,随口道:“陈子别来无恙?”
陈嵊只好站出来,拱手道:“陈嵊见过王上,多谢王上挂念。”
熊良夫哈哈大笑道:“若陈子能归我楚,寡人愿以九江之地相托,封龙野君,赐赏金万两,美女百名,不知陈子意下如何?”
站在熊良夫身后的郑圆脸色一下变得冰冷,恨恨地盯了熊良夫后背一眼,却听陈嵊道:“陈嵊不过是溪流里的一条蛞斗,岂有能力在宽大的江河里畅游?王上应该去找那些在江河里的鱼虾才是。”
熊良夫愣了愣,拍手叫道:“好,好,既然陈子无意,本王亦不强求,陈子好自为之吧。”
郑圆感激地看了陈嵊一眼,心中却不由有些悲哀,越国的脸面竟然需要一个外人来保全,不得不说是一种巨大的羞辱,她愈想愈悲,差点当场落泪。
熊良夫又看向黄歇,笑道:“黄爱卿琅琊之行万分辛苦,功劳甚大,此次便随本王一道回郢都休养受封,后续之事就交由景合处理。”
黄歇心中一喜,拱手道:“谨遵王命。”
熊良夫又转过头对景合说道:“将军此行任务重大,务必替本王照顾好越夫人,若日后本王在夫人口中听见你的半点不是,本王必有重罚。”
陈嵊听见熊良夫居然口呼郑圆为越夫人,心中一颤,他突然有些明白这熊良夫在打什么主意了,不由瞧向郑圆,只见郑圆轻咬嘴唇,眼圈微红,放在腰间的双手紧紧扣握在一起,情绪激动却又不得不隐忍起来。
景合躬身道:“王上放心,末将愿立下军令状,誓死保护好越王后,王后,若有任何差遣,只要末将能办到的,绝无推脱。”
郑圆深吸一口气,顿了一会,才缓缓道:“未亡人季郑,多谢楚王及将军费心了。”
熊良夫哈哈一笑,转过身子,说道:“那本王便告辞了。”
紧走了几步,又返还身子,一把抓住郑圆之手,说道:“本王盼夫人能早日替越国立下新君,到时本王一定亲来朝贺。”
郑圆的手被熊良夫冷不防抓住,脸色顿时变红,渐有怒色,陈嵊看得大惊,竟一步上前,抓住熊良夫手腕,厉声道:“王上还请自重!”
黄歇没想到陈嵊如此大胆,景合与周围的士兵亦是惊色,纷纷拿起武器对准陈嵊,熊良夫悠悠地看着陈嵊,缓缓道:“若陈子此时放手,本王念你旧情,必既往不咎。”
陈嵊哈哈大笑,环顾左右,丝毫不惧周围士兵的怒色,说道:“楚王此来,若只为祭奠无强而来,越国上下必谢王上圣人仁义,亦必对王上心存感激,楚越亦将世代交好。若想以胜者之姿而强人所难,迫人不愿,越国上下众人心中亦有死志。王上,你我相隔无间,我腰有州句,即便身死,亦必弑之,再者,越国尚有数百百战精兵在客栈之外,若众志齐心,亦有于万军阵前取敌首级的机会,王上是否要试一试?”
熊良夫盯着陈嵊,眼中露出一丝阴色,继而脸色带笑,放开郑圆的手腕,说道:“本王此次确实是为祭奠无强而来,可惜王后不便,本王甚感遗憾,不过无妨,本王回宫,自当日日向东遥祭。”
陈嵊淡淡一笑,说道:“多谢王上美意,王后不便送客,便由在下相送王上出去,王上,请。”
熊良夫哈哈一笑,两人牵着手,并列走出门。
两人来到车前,陈嵊这才放开熊良夫,淡淡说道:“王上,楚越已然和盟,楚得到越的千里之地,必将雄绝天下,若善加经营,仁义不输周武,取周代之指日可待,而越却将陷入分裂内战之局,不须外力亦将渐弱消散,王上雄才大略,自该把眼光放在需要警惕的对手之上。”
熊良夫死死盯着陈嵊,面无表情,让人无从知晓他在想些什么,陈嵊从路边扯过一根树条,奉于双手,说道:“适才多有得罪,还请王上责罚。”
熊良夫沉吟半响,接过树条,冷声说道:“这根树条,本王会好好保管。”说罢登车而上。
黄歇来到陈嵊身边,指着陈嵊,却只是摇头,说道:“没想到陈兄……”
陈嵊把手放在黄歇肩头,语重心长地说道:“楚王此次前来,黄兄当真不知?”
黄歇苦笑道:“陈兄,此事我真不知情,我实没想到王上他会……”
陈嵊缓缓收回手,紧皱眉头道:“人谋比不过人心的变化,黄兄此回郢都,必是众望所归,还望好自为之。”
黄歇怔道:“若有机会斡旋,在下自当尽力。”
陈嵊说道:“多谢。”
黄歇看了陈嵊愁苦的脸色,说道:“此事的结局是否与陈兄预想的相差太大?才令陈兄有此感叹?”
陈嵊看着黄歇,说道:“在我原本的预想里,并没有使景舍让出令伊之位的计划,而你的出现使事情的转向出现了很多的偏差,我无意与你相争,你出任令伊对楚而言并无坏处。”
黄歇躬身道:“在下还要多谢当日在琅琊城,陈兄的托信不杀之恩。”
陈嵊这才淡淡一笑,说道:“如今越已定,楚需避免卷入中原纷争之中,致力向西攻略巴蜀,方为长远上策。”
黄歇道:“我亦正有此想法,必会尽快敦促王上,以成此事。”
陈嵊点点头,告辞回到客栈,想寻郑圆,却被告知郑圆把自己关在摆放无强棺木的房间,不许任何人进去打扰,陈嵊叹了叹气,想要回去自己房间,却又不放心郑圆,不自主地走向郑圆所处的房间。
“士子留步。”
一人在旁边叫道,陈嵊听得出来,是那位叫景合的将军,回头笑道:“将军叫住在下,有何事情?莫非是为刚才之事而来?”
景合看着陈嵊,说道:“既然王上饶恕了士子无礼之举,末将岂敢再论,末将是来多谢士子的,若不是因士子的关系,家父岂能被迫向王上辞官回乡,安享晚年。”
景合说这话时,表情倨傲,面无微笑,陈嵊也听出了他话中的反义,淡淡道:“将军不必客气,老令伊对楚勤政数十载,功莫大焉,如今虽然让贤身退,但有将军为续,只会留名青史,受万世敬仰。”
景合道:“末将现在身负重责,不便抽身,日后若有机会必定重谢士子。”
陈嵊拱手道:“将军盛情,陈嵊实不敢当。”
景合呵呵两声,转身离开。
陈嵊也没把景合的话做一回事,放在了一边,来到郑圆房间,轻敲了一下房门。
门里郑圆问道:“何人在外?”
陈嵊答道:“王后,陈嵊求见。”
门里一阵沉静,半响才听郑圆悠悠说道:“我想在此屋内静一静,士子请回屋去吧,晚些时候我会遣人来请士子。”
陈嵊在门口静静站立片刻,才道:“还请王后保重身体。”
隔了一会,郑圆才说道:“士子放心,我自有分寸。”
陈嵊只得回到自己房间,却更加无法静下心来,好不容易临到傍晚,一位婢女在门外叫道:“王后有请士子。”
陈嵊内心一颤,站起身,整了整自己衣冠,走出门去,对着婢女道:“请小妹引路。”
这里是一间客栈,二层楼,呈口子型,郑圆在二楼,陈嵊住在一楼,他随婢女穿过一道楼梯,在左转了一道弯角,来到一间房间,婢女站在门旁,对陈嵊笑道:“王后已在屋中备好酒席,士子请进,奴婢先告退了。”
陈嵊点头,上前敲了敲门,道:“王后,陈嵊来见。”
门里传来一声,说道:“士子请进。”
陈嵊这才推开门,走了进去,刚踏入屋内,一股清幽之香扑鼻而至,让陈嵊心神一恍,竟有些迷糊起来,再抬头往前望去,只见郑圆坐在案前,盈盈朝自己招手。
此时郑圆已经换下那一身轻甲,穿上了淡红丝绸纱衣,妆花素面,逶迤拖地宫裙,云鬓轻拢慢拈,整个人显得艳美绝伦,好一个绝世佳人,灿如春华。
这才是属于郑圆真正的美丽,妩媚人心,芳华绝代,与先前那个身着轻甲,持剑轻舞的那位佳人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极致的魅力。
郑圆指着案前一位,对着有些失神的陈嵊说道:“士子请坐。”
陈嵊失魂地坐下,却不敢再抬头看上一眼郑圆,他怕自己再多看一眼,便将永远沉浸在那绝世的美丽之中。
郑圆为斟上一杯酒,递给陈嵊,说道:“士子请饮酒。”
陈嵊接过酒杯,低头看着酒杯里尚还在荡漾的酒水,沉声说道:“王后,今日熊良夫突然微服到来,不知有何企图?”
郑圆顿了顿,勉强一笑,说道:“我不过是一个死了夫家的未亡人,早已将世事度之身外了,熊良夫纵有什么企图我亦不会如他所愿。”
陈嵊一饮而尽,才说道:“王后你……?”
话未说完,却被郑圆打断,斟满酒,对陈嵊说道:“今日多谢士子了,我敬士子一杯,多谢士子这些时日为越奔走相助。”
陈嵊也不说话,接过酒杯,又是一饮而尽,轻声道:“多谢王后。”
郑圆轻轻一叹,说道:“大王身死,只余下我一人,若非士子在旁分忧,我早已难以为继,只是士子之才,在七国之中,已属冠首,若至楚齐魏等大国,也当位冠群臣,声施后世,而越经此一役,已失国威,郑圆也不知,越国还有什么能够让士子的脚步停留在此,我只希望,越国真的还有值得士子留下的事物,那么不管是何代价,郑圆也会为士子办到。”
陈嵊双手一颤,手中的酒杯差点掉了下来,诚惶道:“王后,权利与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陈嵊并非是那些世间迂腐之人。”
郑圆看着陈嵊,说道:“士子既不为权,亦不为财,那便是为了美人了。”
陈嵊狠狠捏了捏大腿的肉,说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过陈嵊自知并非君子,亦不会妄逑淑女。”
郑圆愣了愣,随即笑说道:“饮酒烦闷,不如让郑圆为士子舞上一曲助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