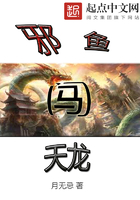张三独自一人走着。
那四个废物已经被赶回家了。
家里有药房,不过是点皮外伤,还没演武场里对练伤得重,敷点药,没几天就好。
张三今天出来本是准备去看马戏的,江湖艺人的小把戏有时候比平日里见的灵修手段还要神鬼莫测。今天这场马戏是火遍大江南北的师徒三人所表演,什么上刀山下油锅都不在话下,特别是那压轴的大戏身首分离,一刀切下血如泉涌,徒弟还捧着师父的头跟你聊天,看着一颗头口若悬河喋喋不休真是要多惊悚有多惊悚,有哪个灵修能做到?
张三忿忿不平地想,灵修也不过如此嘛。
其实要怪也怪这马戏,那师徒不像其他江湖艺人一般在白日里出演,非得等到日落之后才开始。害得他找些乐子打发时间找到灵修身上,触了一身霉头。张三一想到这就忍不住想到那姑娘,真的,长这么大从没见过如此漂亮的,美得如梦似幻。江陵出美女,可就算加上历史上有名的那几个也不见得比得上她。恼人的是怎么会有这么个不讲道理的师兄,论样貌定是要差自己三分,且不论修为,自己好歹还能吟诗作对,看她师兄那样怕是不行,左右算算自己定也差不到哪去。
张三本来是没什么心情去看马戏的,但一想到回家就又要被逼着念书,看些枯燥无味的生意经就改了主意,还是去看看马戏调整一下情绪的好。路上自己开导自己倒也有点效果,越想越觉得自己命苦,小小年纪却承担着不该有的帅气与机智,毕竟集美貌和才华于一身,处处招人嫉恨针对也是应该的。
※※※
一个小巷里,四个身影鬼鬼祟祟。
“老大,这才刚找了个安身之地,还没安生几天,你又要动手,万一事情败露,我们岂不是又要亡命天涯。”老四啃着鸡腿,也不知怎么还能利索地说话。
这话刚才动身宴上怎么不说,吃饱喝足了才想着缩头?老大暗自腹诽,嘴上却说着,“上次只是个意外,要不是那女的是县令相好,我们怎么会被通缉,那些官差又怎么会花这么大力气来寻我们。”
老三一个大老爷们却操着娇滴滴的口音,“嗨,什么大风大浪这不都过来了,这地界已经没我们的通缉令了,大不了干一票就走啊。”
老二捏了捏钱袋,明明没啃鸡腿却磕磕绊绊,“是是是…是啊,最最…最后一点…一点钱,刚刚刚…都吃了,不不不…干干…一票,就就就……”
老大看老二说两句话就涨红了脸,他不累自己都累,连忙打断道,“行了,这次我们早已精心谋划,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老四,别吃了,干活!”说着抢过老四手上的半个鸡腿,两三口啃得七七八八,随手扔在地上。
老四看那还余着些肉的骨头,略有些心痛。
所谓的精心谋划便是今晚的马戏了,白天演的街头戏艺不过是些穷苦人看,没什么劫头,光天化日也不方便。而这晚上就不一样了,富家少爷在家待一天了,难免会跑出来透透气,富家千金更是少有露面,但就爱这种新奇玩意。到时候围着看马戏的里三层外三层,只要注意外面有什么衣着华贵鲜艳的人,一闷棍下去,拖走便是。
这个时候马戏正到高潮,或蹲或坐或站还有骑脖子上的围了一大片,场间有大红布盖着的半人高的长桌,桌上是一口大箱子,师父被五花大绑塞进横着的大箱子里,只露个头。有一徒弟取了把明晃晃的弯刀,耍了几手,张口一吐,三尺长的火舌舔着刀尖。还有个徒弟拿了块长长的布条,展示一番后,双手平举,单膝跪于拿刀徒弟身前。拿刀的也不客气,大喝一声,当头劈下。布条立断,看上去是真家伙。
在一片喝彩声中,徒弟虚晃几手,猛地一刀利索切过师父脖子,血溅三尺高,吓得众人惊呼不止,可那满是花白发须的头颅却跟没事似的,笑眯眯说着些走江湖求捧场的话。另一徒弟上前,拿起一木方盘,展示了下没什么机关暗秘,捧起师父血淋淋的头颅,放进盘中,就这么走下台,让师父和看客聊起天来,而拿刀的那位就换了个铜锣当盘子,跟在后面讨银钱。
一声凤鸣,接着有火光冲天而起。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加的烟花节目,纷纷鼓掌喝起彩来。
反倒是师父吓得够呛,再也顾不上表演,从徒弟衣服中钻出来,大喊着:“下雨啦,快回去收衣服啊……”
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师徒三人就这么溜了。
然而下一刻所有人都跑了,乌云眨眼而至,万里晴空瞬间乌云密布。而那火光破天处,就像天被捅出个大窟窿一样,不知谁喊了声,天塌了,快跑啊。一下子场面就变得极为混乱,谁也顾不上谁,天都塌了,哪还有人管你是哪家小姐谁家少爷。
张三也不知人被挤到哪里,要说天塌他是不信的,然而漫天惊雷直接把他信心粉碎,管它塌不塌,跟着跑总没错,结果头上一痛就没了知觉。
那伙劫匪待要动手才发现,这黑灯瞎火的根本看不清哪个是布衣哪个是锦袍,兜兜转转半天没个下手的目标。也不知怎么的就火光冲天,紧接着所有人都跑了,乌泱泱一大群就这么作鸟兽散,乱成一锅粥。那也就顾不了锦袍还是布衣了,见有人凑过来,一闷棍就带走,这么乱都不用塞麻袋里了,两人一夹就拖着走,谁也不会注意到。
※※※
一缕曦光透过破败的窗扉照在张三的眼皮底下,张三眼睑动了动,睁开了眼,“嘶,头怎么这么痛,”想抬手揉揉才发现自己手被反绑在身后,“这……”
抬头一看才发现这是间破旧的屋子,看上去好像是有点年头的荒废小庙。
旁边有个肚子都能高过下巴的大胖子抱着把刀,倚柱嘟着嘴酣睡。
张三心思百转,想着脱身的办法,然而遗憾的是,脑子里有十万草泥马奔腾而过,完全无法正常思考,反正思考也没啥用,手脚都绑着,还能上天不成?
破旧的幡布一撩,进来一个普通庄稼汉模样的人,头上还扎着常年浸汗发黄的布条,一脚踢醒正酣睡的胖子,“好你个老四,吃你最能吃,睡也你最能睡,人跑了怎么办?”
“啊啊啊,人跑了!”胖子老四一骨碌爬起来,看张三还好好绑在那,松了口气,嘟囔道,“哎呀,我的海参鲍鱼都还没吃呢就被吵醒了。”
老大踹了老四屁股一脚,“还海参鲍鱼,做什么美梦呢!”
老四揉着屁股,不满道,“吃不让吃,梦都不让梦了!”
“嘿嘿,”老大突然喜形于色,“谁说不让吃了?”从怀里摸出一块通透翠玉,“这回可是捞到大鱼了。”
老四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昨晚只是借火光粗略扫了下,就找到这上佳的玉佩,还有那精致的裤腰带,公子哥就是不一样,咱们就粗绳随便一系,人家非得穿金戴玉才行,正好,便宜了咱们,这下可有银子吃些山珍海味了。”
老四撩起幡布,乐滋滋地出去,轮老大来看守。
张三听了这对话感到有些高兴,不就要钱嘛,家里什么都缺,唯独不缺钱,要多少有多少。随即不再装死,热情地打起招呼,“劫匪大哥?”
老大心中一阵烦躁,怎么又一个跟老三一样的娘娘腔,当下语气不善道,“身上还有什么值钱的家物什赶紧交出来,省得爷爷我搜身。”
张三嬉笑道,“哦,我身上还有把扇子。”
老大不满意道,“扇子值得几文钱,在哪呢?”
张三倒不知道那扇子值几钱,但是看那样子也知道价值不菲,只是,“呃,好像丢了。”
“你拿老子寻开心呢!”老大恼道,看那嬉皮笑脸的样子是想挨揍。
“别别别,”张三急急讨饶,“不就要点钱嘛,别伤了和气。”
“谁跟你和气!”老大踹了好几脚才解气。
“只要你们放了我,要多少钱我都给你们。”张三一脸的财大气粗。
“哼。”老大不屑道,“我们要一百两纹银你也能给?”
张三被一口气堵得不轻,一百两!我的天,一百两算钱?
实际上以一两银为一千文钱算,昨天劫匪那顿动身宴不过花了五十文,有鱼有肉,五碟小菜,外加一壶酒。也就是说一两银就可以吃上二十顿这样的大餐,一百两那是可以吃上两千顿啊。一般开销不大的农户,一家三口一年花不过一两,一百两确实不少。
老大也不知道张三心里在想些什么,犹自说道,“谅你也拿不出来,我们求的也不多,让你家里人送二十两过来就放你回去。”
“行行行,大爷高兴就好。”张三满口答应。心里却想,我那玉佩就不说了,就那玉带钩少说也要数百两,而我居然就值二十两!这都什么世道!
“那大爷让我写封信,我让家里人马上把钱送过来。”
老大有些欣赏张三的上道,但是呢,“呃,这个嘛,老三!”
“大哥呀,怎么了哟。”老三蹙着眉,一脸厌烦的小表情。
老大忍着恶心,“去去去,赶快把笔墨买来。”
老三跺了跺脚,还没说不去就被老大一脚踹出门
张三有些无语,这劫匪竟连笔墨纸砚都没有,那还绑个什么票,难不成现在的劫匪都是大摇大摆登门拜访,文质彬彬地说贵公子在寒舍小住,特此来讨些住宿费伙食费?
老三出门没多久,老二结结巴巴地说可以拿个信物去府上直接说人在他们手里,省得麻烦。
于是老四拿着张三的裤腰带也去了。
张三瞠目结舌,真提莫登门拜访,可你们也没问我住哪啊?
过了小半天老大才反应过来还不知道张三住哪,“哎,不对啊,老四都不知道他住哪,去哪说啊?”
张三一阵无语,满脸都是黑线,不行,士可杀不可辱,我不能栽在这帮人手里,就这么被赎回去太窝囊了。
张三一番考量,试探道,“我说,这手绑这么久了,都麻了。要不给我松个绑,活络一下筋骨,待会好写信啊。”
老大一脸狐疑,“你莫不是要逃?”
张三呼天抢地喊冤枉,“哎呀,我怎么会逃呢,我脚这不是还绑着,再说有你们看着,我插上翅膀也跑不了啊。”
老大凑近了点,哼了一声,警告道,“劝你少动歪脑筋,敢跑我腿都给你打断掉!”
接着还真给张三松了绑,弄得张三都到嘴边的一堆说辞又咽了回去。
张三也不急,不知谁偷懒,脚上绑得根本不紧,表面上装模作样活动身体,偷偷挣开了脚上的麻绳,心里乐开了花,那就对不住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本少爷现在是个自由身啦。
瞅准机会一个箭步就冲了出去,跑出老远也没见人追出来,心情无比的快慰,总想唱个小曲,张口就是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老大眼瞪得跟铜铃似的,“老二?你怎么没看住门?”
老二也是无辜,“我…我我…没反反…反应过来。”
老大长长吐了口气,“那你还站这干什么?”
老二摇摇头,“我…我我…我不不…不知知道啊。”
“还不去追?”
“噢噢噢!”
老二冲出门又折回来,“早早早…早说啊!”
老大一口气差点没上来,几欲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