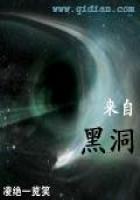这季节出了毛病/我们丧失了夏天的百万富翁/他仿佛从一个货物单上逃走了/我听到每个细胞中都有恶神在啜泣/好像我被卡住了喉咙/我自己就是座地狱;这是多次想自杀而自杀未遂的洛威尔的最后一首诗《黄鼠狼的时辰》中的诗句。在诗中,他毅然断言:“我的头脑不正常。”一方面,世界以及人类如此凄然、孤寂和堕落,另一方面,又时刻呈现着理智、超然的戏剧性结果,而他也把自己放在堕落的生活中一起加以谴责,痛感人性的衰微破败。安妮·塞克斯顿以及西尔维娅·普拉斯,都是洛威尔在波士顿大学诗歌研究班的学生。安妮·塞克斯顿生于1928年,未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她是一位漂亮的女人,接受过模特职业的培训,并偶尔当过模特。1960年出版处女诗集《去疯人院又半途而返》,曾获得美国文学艺术院、福特基金会奖等多种奖项,1967年因诗集《生或死》获得普利策奖。安妮·塞克斯顿一生多次因精神病住院,并数次试图自杀,但均未成功。
1974年10月4日她在自己的车库里以一氧化碳中毒方式成功地实现了自杀的夙愿。安妮·塞克斯顿的诗句,以深刻泰然、几乎是令人难为情的直率、对人生的经历作着比同时代人更多的自白:
“我走了,一个迷幻的女巫/黑夜的勇士,出没在漆黑的天空/我排除了这些简陋房舍的障碍/梦想着罪恶;光,一束接着一束/孤独的东西,十二根刺破灵魂的手指/一个喜欢完全不是女人的女人/我已是她的本质。”(安妮·塞克斯顿《她的本质》)
“我生来就和罪恶打交道/生来就在忏悔罪过。”这是安妮·塞克斯顿《对贪婪的仁慈》中的诗句,更是她的自白。她认为自杀是对生活最有力的指责。她把意象说成“诗歌的心脏,意象从无意识中来。想象和无意识合二为一。”塞克斯顿的诗歌,全部主题都与精神错乱、性裸露、堕胎、死亡、家庭解体、信仰矛盾有关。她是20世纪中期的唐吉珂德,总是与个人的梦魇而不是风车反复格杀、抗争。西尔维娅·普拉斯是自白派诗人中最声名卓着的,她的诗取法洛威尔,但又超乎其上,她着意挣脱逻辑和文法的束缚,以简略的口语和怪诞的象征,坦率地将个人隐私、内心创痛、犯罪心理自杀情绪甚至性冲动等融入诗歌里,把艺术与疯狂柔和在了一起,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难能可贵的是,普拉斯对宗教、道德、战争以及法拉斯主义等有着深刻的哲学思辨和尖锐的批判精神,使读者从诗里感受着诗人的内心世界,同时更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堕落、污秽、混乱而真实的罪恶世界。作为现代主义诗歌歇斯底里的极端狂热者,普拉斯将自身的一切都融入了诗的世界,她的海妖般的阴冷、女巫般的感觉与体验、极端的顶峰造极般的敏感,让后人不由得感叹诗歌的残忍与冷酷。当生命与个体发生分裂、时代与自身发生悖离的时候,诗人尤其是自白派诗人,也许,别无选择。1963年2月11日,在极度的心理压抑和精神错乱中,曾几次自杀未遂的普拉斯吸煤气自杀而死。
“阴郁的舌头,是守护冥府的三条肥狗/趴在门口呼哧呼哧地喘气/但想舔掉邪恶的跟腱是徒劳的/罪恶。罪恶/火绒呼叫着/一支掐灭的蜡烛”(西尔维娅·普拉斯《高烧103°》)
在自白派中约翰·伯里曼是和洛威尔几乎齐名的着名诗人,评论家们甚至将他的诗作的深度、光度、大胆与技巧与荷马、但丁、惠特曼相提并论。约翰·伯里曼于1914年10月25日出生,家庭对他不是一个温暖的象征,父母不和经常争吵,12岁时其父竟当着他的面用手枪自杀,其惨景深深地印在诗人幼小的心灵里,使他的一生都处在精神紧张的状态中,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但他将绝望作为自己的艺术负担,面对绝望并与之搏斗,用毕生的精力寻找一种解脱巨大的心理负担的方式和风格,英雄般的告诉我们怎样在这个充满恐惧的世界里生活。诗人的感伤和痛苦不仅仅是个人的灾难,同时更证明了时代的感情气候对诗人的压迫。1972年1月7日诗人终于精神崩溃,从100米高的密西西比河岸以任何一个优秀的跳水运动员都无法比拟的勇气跳入封冻的河中,永远停止了他的歌唱。
生活,朋友都使人腻味。我们不能这样说,毕竟天空在闪闪发亮,大海在思慕渴望,我们自己也闪闪发亮,思慕渴望那宁静的群山和杜松子酒,看来都讨厌,不知怎地,一只狗把自己的尾巴一古脑儿带走,带进群山、海洋、天空。留在身后的只是我,小丑。人们使我厌烦,文学使我厌烦,尤其是伟大的作品(约翰·伯里曼《梦歌》)悖离,就是这样发生了。而死亡,不过是悲剧的必然结局。
在这个喧嚣的令人恐惧的世界的阴影里,我们看到了诗的阴影,而在诗的阴影里我们的诗人——追逐死亡的诗人是那样的决绝和果敢,却又是那样的无奈和悲哀:念宇宙之浩淼,而人间天堂何在?心惶然而无泪!其实,有泪又如何?故去的已经故去,故去的将永远沉默,自白,并不为着那惨淡的理解和掌声。
5.无望的悲歌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大地经济大潮汹涌澎湃,它无情地席卷着一切,人们或欣然或无奈地为金钱和物质而忙得不亦乐乎,欲望就像大雨中的伞一样无所不在地绽放着。在这个尘世间,欲望好似黑洞一样,贪婪地吞噬着巨量的天体与光线。围困我们的浮躁与喧嚣,仿佛无数在我们心灵和耳畔不断煽动的翅膀。文学方舟从狂热过火的巅峰跌入冰冷的低谷,一切都翻了一个格,“文学贵族”的精神支柱轰然倒下,昔日的辉煌已成为永久的历史,在边缘化处境的虚无冷漠和内在灵魂冲突的双重夹击下,少数诗人只好以生命的代价凄凉地吟唱出一曲无望的悲歌。
中国自孔孟以来,便在知识阶层中倡导“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魏灵公》),“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身而取义也”(《孟子·告子上》)。正是由于这种“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死亡观的染濡,数千年来中国知识精英才甘于“生与忧患而死于安乐”。在中国知识阶层长期所崇仰的生命观中,作为理想人格来显示的死亡方式不外乎是四种:
一是面对侵略,战死疆场。所谓“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陆游《夜读兵书》)、“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文天祥《正气歌》);二是身逢乱世昏君,直谏至死。所谓“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见过即谏,不用则死”
(《臣执·匡谏》);三是直面强暴,可杀而不可辱,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忠臣宁死而不辱”;四是国破乱世,自杀殉道。所谓“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屈原《离骚》)。不可否认,这样的死亡观确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的知识精英,使他们直面强横,寸步不让地坚持真理,留下了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然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还有民间流传的“好死不如赖活的”庸俗生命观占据着人们的头脑,因此中国自古像屈原那样以生命的终结发出没有答案的“天问”的诗人实在是罕见的。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才迫使诗人们以生命的代价进行了一次集体的“政治大逃亡”,无论是迫害至死还是被迫走上绝路,诗人的死亡率(包括自杀率)都是空前的。在那样一个对传统文化无情毁灭,对知识、对人格、对精神肆意践踏的年代里,诗人的斯文彻底扫地,诗人的尊严和精神自由被彻底剥夺。而要摆脱这专制的压迫,维护自己的尊严,那就只有以死抗争。当代作家史铁生道出了这一时期中国诗人自杀密集的原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