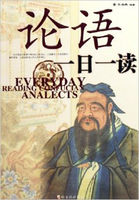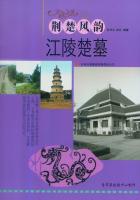每个民族都有一种具有一定能量的集体力量推动人们去自杀。乍看起来,自杀者所完成的动作似乎只表现他个人的性格,实际上是这些动作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社会状态的继续和延伸。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
请原谅我毫无诗意地直奔主题——假如我们先验地假设诗人自杀需要两个必备的条件:外部的压力和内在的动力。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在那些诗人自杀相对较为集中的时代和国家探讨一下诗人自杀的社会心理,这虽然有些乏味,却是跨向诗人自杀迷宫必经的门坎。在这道必须跨越的生死门坎里我们到底会看到怎样的一双无形的强有力的推动诗人走向死亡的“上帝之手”呢?这和马拉多纳在世界杯上拯救了阿根廷的“上帝之手”可不是一回事啊!
1.“英国病”在欧洲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所提出来的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问题,但在这之前在欧洲其实人们也一直关注着,自杀是争论的焦点。
基督教社会形成后,自杀就被正式禁止,而且认为是一种罪过,不仅财产被没收,尸体还要被游街示众,甚至被烧掉。1789年法国大革命废除了所有这些做法,然而法国人所信奉的各种宗教继续禁止并惩罚自杀,公共道德也谴责自杀,自杀成为道德上的一个污点。英国在10世纪时把自杀者视为杀人犯盗贼一样的罪犯,直到19世纪20年代还将自杀者的尸体游街。“自杀”这个用以指代一种罪恶行为的名词也来自英国,诞生于17世纪。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英国,一些名人包括战时国务秘书约翰·汤普、着名的浸礼会传教士约翰·柴德、巴特伯爵父子、大富翁乔治·爱德华、牛津大学着名学者托马斯·克立奇等绝望中相继自杀,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特别是克立奇之死,是一个难解之谜,传说他死前还在阅读剑桥大学理论博士多恩勇敢地突破专制和偏见、为自杀平反写于1610年的《论暴死》,他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自尽用的绳子。1经过报刊的广泛报道和评论,这些自杀事件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国病”之谜因此诞生了,在英国自杀的事件层出不穷,“英国是自杀的国度”成为人们公认的事实。
“可以肯定的是,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是自杀数量居高不下的重要背景。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之上的冒险、竞争和赌博是造成不稳定和不安全的重要因素。”
使得破产者加入了传统自杀者的行列,疾病、战争、生活的极度贫困也大大加快了人们自杀的步伐。在这个时期,英国贵族自杀的人数也出奇的多,自杀甚至被当成真正的时尚。17世纪中叶英国的宗教斗争渐渐减缓,贵族和上流社会出现了宽容对待自杀的潮流。威廉姆在一本绅士的读物《绅士的伙伴》中表明了对自杀者的同情:“我们不应该谴责他们”,“因为即使是上帝选出的精英,如果因为精神病而失去正常的思维和理智,就有可能导致沉重的忧郁,接下来还会被各种疾病所侵袭,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刽子手。”1而对名人自杀的大肆传播,自杀的流行也让世人相信:自杀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荣誉,并跟决斗相近。因为自杀或者决斗,使用的工具都是手枪或者是刀剑,不过如果是上吊自尽会遭到人们的蔑视。所以皇室成员中的剑客、骑士、绅士自杀70%使用了火枪,而随着被人们奉为尊严而自杀的楷模加图的知名度的不断增长,更促进了从18世纪初开始使用的匕首或刀剑的自杀。加图是古罗马帝国恺撒大帝的政敌,他因不肯屈服于恺撒用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独裁统治,便选择了自杀的道路。在这之前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没有获得成功,但由于他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而自杀,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因此在他死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他都是恺撒独裁政体最可怕的敌人。人们对加图的赞誉比任何异教徒都要高。1713年约瑟夫·阿迪森的悲剧《加图》将加图之死奉为神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人们对加图的推崇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1737年诗人乌斯塔什跃进泰晤士河,于河神为伴,他自沉之前不无痛心地说:“加图的所作所为和阿迪森对他的大肆赞颂都只能是罪恶。”2这句话很快就传播开来了。威廉姆曾以辛辣的讽刺和幽默建议写一本关于自杀艺术的书用以指导上流社会的自杀。对自杀持宽容的态度更使英国蒙上了自杀之国的名声,而在英国对自杀持同情支持宽容的人越来越多。1680年自然神论者查尔斯·布伦特高度赞美了《论暴死》一书,4年后也突然自杀身亡。1695年自由主义思想家查尔斯·吉尔顿为他死去的朋友查尔斯·布伦特辩护,认为布伦特作为哲学家死去并没有违背自然与理性的箴言,他被不可能的爱所折磨,与其永远忍受心灵的痛苦,不如一了百了。这是伊壁鸠鲁主义的原则。这让宗教哲学家们对“英国病”迅猛蔓延的势头感到担忧,于是纷纷诉诸笔墨,极力维护传统道德。但已无法改变人们对自杀采取宽容的态度,也无法阻挡一股新思潮的风行——人们对加图、伊壁鸠鲁、卢克莱修英雄主义的自杀的赞誉。
“英国病”很快在欧洲大陆蔓延,深入人心。18世纪初巴黎流行的时尚就是摆脱生命,文学作品对古代自杀大加赞赏,特别肯定卢克莱修自杀的伟大,而自杀在贵族阶层仿佛成了不足为奇的事情,甚至好像成了贵族的一项特权。他们有因政治野心得不到满足的,有因欠债破产的,有因婚姻爱情失败的,有因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有因厌世绝望的;或投河自沉,或饮弹身亡,或跳楼自尽,或匕首自戕,或绝食而死。在公众眼里,卢克莱修是他们的榜样,一些人的确真正表现了无所畏惧的气概。有一位深受教区人们爱戴的教士因对抗教皇的罪名被关进巴士底狱,他其实是无辜的,但当局却剥夺了他的自由,于是他绝食而亡。他的死使他远近闻名,有一首赞美他的诗写道:“他的生命在临近死亡时绽放;在生命结束时灿烂。”3这位教士的死也使得自杀病在监狱里蔓延,因为面对暗无天日的终生监禁和严刑酷罚,绝望中的犯人们更喜欢自杀。正因为如此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不再对自杀反感,对自杀事件抱着比较开明的态度。据拉辛说,有一天,布瓦洛、莫里哀和夏培尔一起愉快地去投塞纳河自杀。1可见自杀的风气已经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英国病”同样传染给了德国,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虽然比英法两国要晚一些,但它的文学的发展却在歌德时期达到了辉煌的一个阶段。1774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时,歌德才25岁,当时他的一位好朋友自杀了,这引起他的极大的关注。这位好朋友是布伦斯维克公使馆的秘书,因为被一位他心仪已久的已婚妇女拒绝而绝望自尽,恰好歌德也正在与一位已婚女子热恋着。这就构成了维特的人物雏形。小说发表后在德国和欧洲引起的“维特热”或“维特癖”使歌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谴责他把无耻的人的举动美化成了英雄之举,抨击这本小说是“公众的毒药”,它“造成的自杀人数比世界上美丽的女人还要多。”
并认为歌德是不可原谅的。其实歌德并没有创造一种时尚,他只是描述了德国18世纪中后期的一种社会风气,并给了这种抽象的风气一种具体的形态罢了。
这个时期在德国人们对于自杀的合理性的呼声日益高涨,维特的出现恰好赶上了这一时期。一位多情的年轻男子与他心仪已久的圣洁的女子之间不能发展的爱情故事以动人心弦的自杀为结局,它所表现出来的青春年华、爱情、道德、死亡、不可抗拒的命运等涉及到这一时期人们敏感的话题都能在维特身上找到缩影,找到充满诗情画意而又流露着感伤氛围的描述。所以欧洲的年轻人都喜欢引用维特的语言,效仿他的自杀。针对“维特热”的现象,歌德一再奉劝读者:要想做个真正的人,就不要效仿书中的人。并声明要上帝做他的证人,他再也不写任何“维特”了。后来歌德研究了哲学主义自杀,创造了浮士德的形象,回应了哈姆莱特的“生存还是死亡?”体现了不同于维特的自杀观念。浮士德由于无法成为全才像上帝那样睿智而非常失望,他感到一切对他都已经失去了意义,当他终于参透无所不能的生命不过是虚无而已时,他做出了抉择:不再苟活于世。他选择了自我毁灭,不畏惧地狱,不畏惧死亡:
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人类是有尊严的,决不会因为上帝的强盛而屈服!不要惧怕这幽暗的无底洞,无谓的想象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在这条崎岖的道路上地狱之火正熊熊燃烧着!迈出你的脚步,勇敢地踏上征程,哪怕是碰上死神也别回头!
但自杀的年轻人更多的仍然是效仿维特而不是浮士德,不过这时他们又有了另一个模仿的对象,这个人不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而是年仅17岁的青年诗人托马斯·夏戴尔东。夏戴尔东是个天才,从10岁就开始创作诗歌,他的作品具有中世纪的风韵,开始很受读者欢迎,但由于无法在短时期内得到自己一心向往的辉煌成就而变得消沉起来,成了一个可怜的穷光蛋,终于在绝望中将自己毒死在伦敦宏波一个街区的一间房子里。夏戴尔东死后,文学家艺术家纷纷用自己的方式描述他的死,将夏戴尔东几乎刻画成了一个神话人物,使夏戴尔东成了与维特一样受到青年欢迎的偶像,那些罗曼蒂克的年轻男女在绝望的夏戴尔东面前擦拭着他们感伤的泪水,如果生活上失意,或是心灵受到重创,他们的自杀便成为夏戴尔东或维特的又一个版本。这一时期自杀在德国愈演愈烈,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谈论自杀,完全成了一种时髦的社会风气。而让人觉得可怕的是有人过了30岁时,大家便希望他为了大家的幸福早些死去,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活着不过是让他自己和大家逐渐衰老腐败。在这样一个浸淫着死亡阴影、流行着自杀危机1参阅[法]乔治·米诺瓦《自杀的历史》第八章,第226页。
的社会环境里,诗人的心灵怎能不受到冲击?他们的神经即使是特殊的材料做成的,心理张力也是有限的,有谁没有闪过自杀的念头?出生于法兰克福贵族军官家庭的着名剧作家亨利希·封·克来斯特,人称德国浪漫主义的最后一名战士,最初登上文坛时曾以揭露普鲁士司法制度腐败的喜剧《破瓮记》(它与莱辛的《明娜封巴尔姆》,霍普特曼的《獭皮》并称为德国的三大喜剧)名声大噪,但随后因为创业的艰难,爱情生活上难言的遗憾,国家和人民所受的灾难和耻辱,使得感时伤世的克来斯特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所幸未能真正实行,而在这之前他还嘲笑过维特的自杀。不久他结识了州府会计师的夫人亨里特·福格,她的正直、善良、知书达理使克来斯特将她引为红颜知己,双方心心相印。而福格却以为自己得了绝症(恐病症),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克来斯特与她商定一起离开人世。1811年11月21日黄昏时分在波茨坦附近绚丽多姿的万湖畔,克来斯特和福格倒在浪漫而又荒唐的“义举”——两声清晰而凄厉的枪响中。诗人安东·莱奥纳尔·托马这样感慨地召唤着死亡:
“如果我感到我的心必将衰竭,啊——时间!我会对你说:——预知我的最后一刻吧,你行进得快些好让我死去;我宁愿死去也不想活着受人鄙视啊时间,暂停你的飞逝,尊重我的青春吧。”1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悲剧是:1837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塞戈维亚街的一所古旧的住宅里,被誉为西班牙文学史上的一代宗师,浪漫主义作家马利亚诺·何塞·德·拉腊以维特的方式自杀,年仅28岁。上帝创造的生机勃勃的欧洲大陆就这样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一眼望去令人颤栗的死尸的骸骨的阴影遮蔽了宇宙明丽的阳光,虽然这不是永久的,但暂时的现象也令人窒息,这不仅会让诗人迷失诗魂,也有可能使那些神经脆弱的诗人永远沉入黑暗之中。
2.与帝国对峙的诗人
从普希金开始,俄罗斯诗人就是拉着苦难俄国艰难前行的纤夫。在俄国文学的队伍中,总是圣徒牵着天才的手,殉道者扶着歌者的肩头,哲人劈开诗人脚下的荆棘。如果说19世纪俄国诗人的“放逐、牺牲和死亡”,居于世界各国之首,那么20世纪俄国诗人的死亡率(包括自杀率)则达到一种整体的、纪念碑群的程度。20世纪的俄罗斯诗人带着富有诗意的悲痛和引人同情的维特式的忧郁,付出了比前辈更沉痛的血的代价,成为与超级帝国相对峙和抗衡的道德和精神的力量,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奇观。
20世纪初在俄国的革命和内战,使俄罗斯的文化和文学的基础遭到粉碎性的打击,一夜之间知识分子发现他们已身陷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曾珍爱的一切:
精神自由,温文尔雅,忏悔自省,蔑视专制,痛恨庸俗,珍视生命,反抗苦难,尊崇艺术和宗教顷刻间都变得分文不值。布尔什维克无情地宣布,将挥动历史的铁扫帚清除资产阶级文化和一切残渣余孽。“军事共产主义”和“集体化”的艰苦岁月使世世代代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和诗人向往的诗意消失殆尽。在工人中享有崇高声誉的无产阶级的海燕高尔基愤怒地抨击道:“我特别怀疑地、特别不相信地对待俄国的执政者——这不久前的奴隶在他获得了充任别人的主宰的可能性之后,就变成了最肆无忌惮的专制者。”1他甚至再一次以预言家的勇气石破天惊地指出:“列宁是‘领袖’,也是俄国贵族,这个已经消失的阶层的心理品质列宁并非没有,而正是他认为自己有权拿俄国人民做一次预先注定要失败的残酷的试验。”2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遭到了猛烈的批评,他主办的《新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不断发生冲突,结果被指责是“在为反革命服务”而被彻底查封,他被迫到意大利呆了10年,而且之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