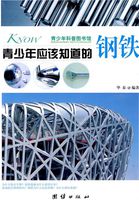“因为我看不见自己的脚,一开始我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第一次下楼时我就绊倒了两次;用看不见的手去拉门闩,也感到特别地别扭。不过到了平地,只要眼睛不往下看,还是走得挺好的……
“我心中十分得意。我就好像是一个眼睛看得见,脚步声很轻,而衣服没有窸窸窣窣声的人,在一个眼睛全都瞎了的盲人城市里走动一样。我有一种狂野的冲动,老想捉弄人、吓唬人,拍拍他们的后背,扔掉他们的帽子,觉得自己比别人特别优越而扬扬得意。
“可是我刚走到波特兰大街(我的住所就在那边一家大布店附近),就听见一声响,后背被猛地撞了一下。我回头一瞧,只见一个人提着一篮苏打水瓶子正惊讶地注视着自己的篮子。虽然那一撞撞得不轻,可是看到他那副惊奇的样子,我实在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篮子里有鬼。’我说着就一把夺过他的篮子。他不由得松了手,我就把一整篮的苏打水向空中抛去。有一个愚蠢的马车夫站在一家小酒店门口。这时突然冲过来接篮子,他张开的手指头猛然戳到我耳朵下面,使我痛得要命。我就把整篮子东西砸到他身上。于是,满大街的人都奔跑起来,到处是惊叫声和纷乱的脚步声,马车也停止不前了,我这才明白自己闯了祸。就一面咒骂自己的愚蠢,一面把背贴在商店橱窗上,打算从骚乱中脱出身来。可是,我差一点被挤到人群中去,要是这样,就必然被人发现了。我把屠夫的徒弟推到一旁,他幸亏没有转过身来看看把他推开的竟是空空洞洞的乌有之物。我躲到那马车夫的四轮马车后面,也不知道这场纷乱是怎样解决的。我匆忙越过马路,幸而这时马路上行人稀少。我怕这次事件被人发现,便慌忙择路钻进了下午在牛津街上闲逛的人群里。
“我想挤入川流不息的人群里,可是人群实在太挤,我的脚后跟很快就被人踩着了。我只得沿着路边的水沟走,可是水沟粗糙不平,走了不多久就磨痛了我的脚。一辆双轮马车这时正好缓慢地驶过,我的肩胛下面被车辕猛撞了一下,真被它撞坏了。我跌跌撞撞地闪过马车,又用一种痉挛的动作躲开了一辆儿童车,这时我发现自己正好站在马车后面。我灵机一动,就紧跟在这辆慢慢行驶的马车后面走着,一面庆幸自己时来运转,一面发抖,不仅发抖,简直是在战栗了。这是正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路面上的泥浆已结起了薄薄的冰,而我却赤条条一丝不挂,浑身不停地发抖战栗。当时我怎么会意识到,不管我的身体是否看得见,我还得服从气候的摆布。真是愚蠢透了。
“忽然我想起一个好主意。我绕上前去,钻进了马车。我受到了惊吓,身子哆嗦着。鼻子呼哧呼哧的,那是感冒的先兆,腰背上的乌青也越来越烦人。马车载着我沿着牛津街慢慢地向前驰去,经过了托坦汉法院路。我这时的心情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与十分钟以前我从房间里突围出来的时候可大不相同了。这个隐身术,真是的!我现在所想的只是如何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了。
“马车慢慢地驶过穆迪图书馆。那儿有一个身材很高的女人,拿着五六本贴着黄色标签的书,招呼这辆载我的马车。我正好来得及跳出马车来躲开她。逃跑时差一点撞上铁路货车。我沿着马路向布隆斯伯雷广场奔去,想赶到博物馆的北边去,这样就可以进入僻静地区了。我这时冻得要死,这种不习惯的处境使我十分气馁,在奔跑的时候,不禁呜咽起来。广场西角的药学协会办公室跑出了一只小白狗,它低垂着鼻子,自然而然地尾随在我后面。以前我从来不清楚这一点,原来狗的鼻子如人的眼睛一样。狗能嗅出人的足迹,就像人能看清对方的外形一样,这畜生边叫边跳,竭力证明它已经发现我了。我一面横过罗索尔大街,一面还回头看了一眼。我已经沿着蒙泰格街跑了一段路,可是我还不知道是在往哪里跑。
“这时传来一阵奏乐声。沿街望去,我看见许多人从罗索尔广场走出来。走在前面的人,穿着红衫,打着救世军的旗帜。这么一大群人,有的在路上放声歌唱,有的在人行道上嘲笑,我休想钻过去。我又怕走回头路,离家更远,就仓促地作出决定,跑到博物馆栏杆对面一所房子的白色台阶上去,打算站在那儿等到人群走过去再说、幸亏那只狗一听见乐队的声音就停住了,它犹豫了一下,掉转尾巴,又向广场奔去。我这才算摆脱了窘境……“乐队过去了,人们高声唱着赞美诗‘何时得见主面’,真是无意的嘲弄。人群沿着人行道在我面前走过,人山人海,好像没完没了似的。咚、咚、咚,大鼓震响着,也过来了。这时我没有注意有两个小淘气在我身旁的栏杆那里逗留着。‘瞧,’其中一个说道。‘瞧什么?’另一个说。‘嗨——脚印——光脚印,就像你脚上带着泥踩出来的。’
“我向下看去,看见两个孩子站在那里,呆呆地注视着我留在新刷白的台阶上的泥脚印。过路的人推挤着他们,可是他们的机灵劲儿已经被脚印吸引住了。‘咚、咚、咚,何时,咚!我们得见!咚!
主啊!咚、咚、咚……’‘有一个赤脚的人走到台阶上去了,我要说的不对,就算我是傻瓜。’一个说,‘他还没有再下来过,他的脚上还流着血呢。’
“人群的大部分已经走过去了。‘瞧这儿,泰德(Ted)。’那年纪较小的孩子突然指着我的脚高声惊叫道。我往下一看,地上果真是有一双模糊不清的脚的轮廓,那是由一摊泥浆形成的。
“‘呃,真奇怪!’大一点的孩子说,‘简直太奇怪了!难道这是一只鬼的脚吗?’他犹豫了一下,就伸着手向我走过来。一个男子马上停了下来,想看看孩子正要抓什么东西。接着又来了一个好奇的女孩。眼看那男孩就要碰到我了,我急中生智,向前跨了一步,那孩子惊叫一声。吓得直往后退。我趁机一跃,迅速地跳到旁边一幢房子的廊下,不料那年纪小一点的男孩却机灵地紧盯着我,我还没迈下台阶来到人行道上,他就从瞬间的惊讶中清醒过来,并且叫喊起来,说那两只脚已经跨过了墙!
“他们赶紧绕过来,看见我的新脚印先出现在下面台阶上,然后又出现在人行道上,‘出了什么事?’有人问道。‘脚!瞧!两只脚在跑!’除了追我的三个人以外,其余在路上的人全都跟着救世军走。这走动着的人群不仅挡住了我,也挡住了追我的人。人群中掀起了一阵惊讶和询问的旋涡。我一拳打倒了一个小伙子,才借此钻出人群,顷刻间我就沿着罗索尔广场的环行路向前猛冲。有六七个人惊奇地跟在我脚印后面追着,他们没有来得及向大家解释,否则整个人群都要向我追过来了。
“我绕了两圈,横穿了三次马路,又回到我的老路上。这时我的脚变得燥热起来,泥印也渐渐消失了。我总算有个喘息的机会,用手擦干净了脚,然后溜之大吉。我最后看到的是,大约有十几个人聚成一堆,极其困惑地研究一个逐渐变干的脚印,那是从塔维斯托广场的一个泥潭那儿带出来的。对他们来说,这脚印就像鲁滨逊发现的那个脚印一样,孤零零地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次奔跑使我的身子暖和一些。我鼓起勇气穿过附近纵横交错的偏僻马路。我的腰背现在很僵很痛,扁桃腺被车夫的手指戳得痛极了。脖子上也被他的指甲抓破了皮,双脚痛得很厉害,一只脚上割破了一个小口子,使我的脚跛了。我看到一个盲人向我走来,就赶紧跛着脚躲开,我怕他敏锐的直觉会发现我。曾有一两次意外地撞上了人。人们听到我的咒骂,都十分惊奇,简直莫名其妙。当我越过广场的时候有东西静静地落在我的脸上,雪花已像一层薄纱一样地飞落下来。我已经着了凉,尽管我拼命忍着,有时也禁不住打个喷嚏。用尖鼻异样地闻来闻去的每一条狗,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恐怖。
“这时跑来许多大人和男孩。一个人跑在前面,其余的人在后面跟着,一边跑,一边叫。失火了。他们向我住处的方向奔去。我回头一望,看见沿街的屋顶和电话线上空升起一大团黑烟。着火的地方肯定是我的住处。除了我的支票簿和三个备忘录还在波特兰大街待领以外,我的衣服、我的仪器,我的一切财物全都在那里。正烧着哩!我把我的船烧了——不管过去有没有人破釜沉舟地把船烧掉,我反正把自己的船烧了。那儿已经是大火熊熊了。”
隐身人停下来默默思索。肯普神经质地向窗外瞥了一眼。“是啊!”他说,“请继续往下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