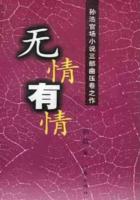安阳的夏天越来越热了,热得人们眼里都冒火星子,就连平日里热闹的展春园的生意都寡淡下来。两个大茶壶陪着窑姐们在厅堂里嗑瓜子、吃西瓜,就是懒得说话。晌午过后,一位客人走进展春园,当即搅动一池春水,老鸨、窑姐、大茶壶一齐起身请安问好,来人竟然是久未在展春园露面的罗宝驹。罗宝驹进门,抓着一把钱挨个打赏,惹得众人困意顿消。
罗宝驹能在这个时候走进展春园,起因还得从樱子说起。樱子最为熟悉的男人是哥哥井道山,井道山木讷寡言,说话行事彬彬有礼。打小与这样一个无趣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因此,樱子更喜欢那个狂浪不羁的罗宝驹。自打老梁头走后,樱子便开始打理罗宝驹的起居饮食,一日三餐不重样伺候着。樱子在大热天里跑来跑去,且有身孕,罗宝驹甚是心疼,每次接过食盒都会念叨,你不要做了,又不是没钱请下人,累坏身子怎么办?罗宝驹看似不经意的体贴话,让樱子心头一热,她扬起一双杏核眼温柔地看着罗宝驹,说道,别人料理你,我怎能放心?只要你不嫌弃我做得不好,我愿意天天伺候你。罗宝驹这时会忍不住伸手把樱子抱在怀里,嘴里说,你真是好婆娘坯子。而此刻,罗宝驹的心却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这份恐惧正是源于他对樱子与日俱增的情分。他害怕和龟田次郎之间的恩怨仇恨,有朝一日会伤害到无辜善良的樱子。万一自己的计划落空,万一自己深陷万劫不复,樱子孤苦伶仃地带着孩子怎么办……
是日晌午,樱子与往常一样,提着食盒走进罗家老宅子。这一次,罗宝驹故意拉着脸,自顾自地想心事。樱子把食盒端到桌子上,催促着罗宝驹趁热吃饭,他却不理不睬。樱子似乎没有在意,她轻巧地走到罗宝驹身边,突然发现罗宝驹头上有一根刺眼的白发。樱子仔细挑选着那根白发,一使劲把白发拔下来。罗宝驹一激灵,一甩手把樱子推出去,呵斥一声。樱子颇感委屈,手扶着墙边的条案,眼泪扑簌簌地跌落下来。罗宝驹没有理会,他腾地站起身来,对樱子说,以后不要送饭了,俺去展春园吃。樱子心里一寒,问道,展春园哪里是吃饭的地方?我是哪里做得不好?罗宝驹说,展春园的姑娘们不会像你这般婆婆妈妈惹俺心烦。说罢,罗宝驹甩手出门。樱子眼泪夺眶而出,叠着小碎步追出来,一路跟随罗宝驹到展春园门口。罗宝驹在门口站定,回过身来对樱子说,俺以后就在这里吃饭,你不必给俺送饭了,你怀着身孕就不要跑东跑西。看到樱子似乎有跟着他进展春园的意思,罗宝驹又说,你怀着孩子,不要进这种不干净的地方。望着罗宝驹的背影,樱子站在展春园门口伤心欲绝,哭了半晌。
罗宝驹不再理会樱子,他叫来一桌丰盛酒席,点了一个有口臭但是会说宽心话的老鸨作陪。老鸨在一旁叨叨地说个不停,罗宝驹就着她的絮叨,一个人闷头喝酒,一直喝至深夜,才回家睡觉。
邱连坤来敲门的时候,罗宝驹正在熟睡。老梁头不在,罗宝驹只好亲自去开门,他一边开门一边骂街,哪个信球,不让老子睡个囫囵觉。邱连坤嘴上不肯吃亏,站在门外说,做贼的才大白天睡觉哩。罗宝驹敞开大门,看到邱连坤和孙发贵,还有一小队日本宪兵。罗宝驹说,不知道是邱局长挠门,您现在都给日本宪兵带队哩?邱连坤笑道,怕你这个日本姑爷挟洋自重,所以,俺邱某只好带几个宪兵一起来。罗宝驹也调笑道,挟洋哪能自重,挟仁挟义才自重哩。邱连坤收起脸色,说龟田司令请罗爷把那个物件亲自送到宪兵司令部。罗宝驹搬来梯子,登上老槐树,抓起白色麻绳,把裹着毯子的鼎耳,从树洞里面拖出来。邱连坤看得啧啧称奇,说你真想得出来,宝贝都塞进树肚子哩。
罗宝驹怀抱鼎耳,鼎耳被一条破毯子裹着,因为被邱连坤和一群宪兵押送,路人纷纷猜测毯子里面包着什么。安阳城里大多数人都认识罗宝驹,大多数人也知道罗宝驹平日里干的勾当,亦正亦邪,虽然摆不到台面上,但至少不祸害百姓。相反,对那些偷鸡摸狗的盗墓贼,还起到震慑作用。近些年,安阳周边盗墓的少了。安阳城有七八家铁匠铺,各个铺子里掌锤的师傅,都快忘了如何打制洛阳铲了。因为知道罗宝驹的背景营生,街上看热闹的人,大都猜测他怀里抱着的是稀世珍宝。警察局邱局长亲自带队,日本宪兵武装押送,这珍宝十有八九是送给日本人的。罗宝驹长得高大魁伟,抱着怀里的物件相当吃力,这物件莫不是金佛金船或是金山?听见路人议论的热闹,邱连坤突发奇想,带着罗宝驹拐弯去了通宝街,他想让通宝街的东家们看看,平日里不让他们跟日本人做交易的罗宝驹,今天亲手捧着宝物送到日本宪兵司令部。罗宝驹明白邱连坤的用意,他往上掂了掂怀中的鼎耳,一脸坦然地走在通宝街上。
进了安阳宪兵司令部,罗宝驹把物件放在桌子上,对龟田次郎说,把俺兄弟放了。龟田次郎没有理会罗宝驹,他冲着井道山点头示意,让其验明真伪。井道山走上前去,把毯子打开,掏出一只放大镜和一个小手电,仔细看了会儿,然后卷起毯子,抱着鼎耳出了龟田次郎的办公室。罗宝驹知道,井道山这是抱着鼎耳找铜鼎对接茬口去了。茬口对上了,十有八九是真的。茬口对不上,肯定是假的。龟田次郎盯着罗宝驹的眼睛,用低沉的声音说,你利用女人盗取铜鼎,你是一头卑鄙无耻的支那猪。待翻译译毕,罗宝驹咧嘴一笑,说:“樱子是俺老婆,怎么能说是利用?还有,俺们是中国人,不是猪。”
龟田次郎脸色有些铁青:“你们中国人只知道房事和生孩子,跟发情的猪有什么两样,你们知道爱情吗?你们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吗?”
罗宝驹说:“展春园的窑姐才需要爱情,俺老婆樱子只要俺跟她睡觉。”
龟田次郎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日本有个作家叫川端康成,他说过一句话,女人在未坠入情网前,是不知道男人下流的。”
罗宝驹说:“你们日本是不是只有一个作家?樱子也总是提他,他说得不假,可樱子坠入情网后,又迷上了俺的下流。”
龟田次郎嗖的一声拔出太刀,对着罗宝驹劈过去。罗宝驹心中一惊,他觉得龟田次郎不应该此刻对他下杀手。念头至此,他觉得腹部一阵剧痛。龟田次郎双手握刀,做的是劈刀状,却只是用太刀刀柄狠狠砸在他的腹部。罗宝驹一口气没有喘上来,疼得他弯下腰来,双手按住腹部。此时,井道山走了进来,把那只鼎耳放在桌子上,对龟田次郎说,是真的。井道山说完,看都没看罗宝驹一眼,甩手肃立一旁,脸上竟无半分悦色。罗宝驹的额头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他忍痛问道,俺兄弟在哪儿?龟田次郎说,现在还不能放罗良驹。罗宝驹问为何?龟田次郎说,你们兄弟二人炸掉皇军的地下军火库,这笔账咱们还没算呢。罗宝驹撇了撇嘴,说划个道道吧,怎么着才能了账。龟田次郎说,看在井道君和樱子的情面上,让罗良驹把铜鼎修复,咱们之间的账就一笔勾销。罗宝驹说,那得看罗良驹是不是愿意。龟田次郎说,用你们中国话说,你兄弟就是粪坑里的石头,又丑又臭还又硬。罗宝驹说那没办法,只有他会修这玩意。龟田次郎说,据说罗良驹最听你的话,你来劝劝他,他若还是固执,我只能翻旧账了。罗宝驹说,我试试看吧。
罗宝驹被两名宪兵搜完身,带进牢房,由一名负责审讯的少佐陪同。少佐把兄弟俩见面的地方安排在牢房审讯室,罗宝驹坐下不一会儿,罗良驹便被两名宪兵带进来。罗宝驹上下打量着弟弟,见他浑身完好没用过刑,这才放心。罗宝驹说:“俺把另一只耳朵送来了。”
罗良驹:“换俺出去?”
罗宝驹:“还得让你帮忙修复铜鼎。”
“修个信球!”
“给都给了,修就修嘛。”
罗良驹抬起丑脸,看着哥哥的眼睛:“哥说修,俺就修。”
“估计只能在这里面修鼎,可得挑个风水好地哩。”
罗良驹似乎读懂了哥哥的眼神,便顺着他的话往下说:“风水不好,毁了物件可不关咱们球事儿。”
罗宝驹:“还得找几个挺妥的帮手。”
罗良驹:“没有好帮手,谁都修不成。”
罗宝驹:“你一个,俺一个,再加上吴庆德和吴宝才,咱四个差不多吧?”
罗良驹:“嗯,够使唤了。”
罗宝驹走出宪兵司令部,宋小六早就候在门外。看到罗宝驹无恙,宋小六才算松了口气。罗宝驹让宋小六赶往文官村找吴庆德,前来帮忙修复铜鼎。
吴庆德自洛阳悄悄潜回文官村,本想处置家产,再回洛阳安身。把后母戊方鼎从宪兵队军火库里鼓捣出来,他知道自己闯的祸有多大,安阳肯定待不下去了。盗鼎之前,罗宝驹找到他,让他与林枫交接铜鼎前,砸掉一只鼎耳带走,即便是铜鼎再次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们也拿不到一个完整物件。吴庆德原本有些犹豫,罗宝驹劝他说,事已至此,带着鼎耳岂不多个护身符。吴庆德觉得已无退路,索性依计行事,抱着鼎耳连夜奔了洛阳。洛阳的住处早前就寻好了,是宋小六亲自跑到洛阳,本想托他舅舅帮忙租赁,赶巧舅舅家有一处闲置房,肥水不流外人田,便租给吴庆德。至于必须“有自己的亲笔信和安顺子送信”才能找到吴庆德,完全是罗宝驹自己编造的,想帮安顺子从囹圄脱身。临回文官村前,吴庆德琢磨如何安置鼎耳,思来想去又回到自己的拿手营生——木匠。他到街上买来刨子、凿子、刻刀几样简单家什,一晚上工夫,把鼎耳镶嵌进八仙桌桌面底部。第二天,吴庆德挤上回安阳的火车,一路上打起精神,生怕被人盯上。从安阳到文官村没有多少路程,他一直挨到天黑才敢进村,直接去了本族一位信得过的堂兄家,托他把祖屋卖掉。吴庆德想尽快卖祖屋,要价不高,两天就找到买主,是本村开醋作坊的吴掌柜。重修房契,签字画押后,吴庆德回家收拾了几样珍爱物件,原本打算半夜去一趟向水屯,看一眼秀娥。结果,他人还没出门,宋小六就到了。听明白宋小六的来意,吴庆德连忙摆手,说宪兵队比地狱还作贱人,打死也不去。宋小六说,吴宝才也被宪兵队抓了,你若不去,罗良驹和吴宝才在劫难逃。吴庆德问,干吗挑俺,你怎么不去?宋小六说,你会木匠活儿,大哥说要让你做一个“鬼关门”的窑炉。吴庆德说,俺这辈子倒霉就倒霉在会干木匠活上了。宋小六掏出银行支票,说是罗宝驹给他的。此前去洛阳,罗宝驹已经给吴庆德和吴宝才每人一万块钱,这回又给三万块,这么一大笔钱,他干两辈子木匠活儿也挣不来。吴庆德手里攥着支票,心里还在权衡:若是去,上下嘴唇一碰就能定下来;若是去了,还能回来吗?宋小六说,我大哥提前谋划好了退路,保你和吴宝才平安出来。吴庆德说,你给俺念叨念叨,怎么才能平安出来?宋小六说,俺大哥说到时候就告诉你,李守文和林枫负责护送你们出安阳。吴庆德还是犹疑不定,宋小六说,自从我家大哥掌舵以来,凡事都做得入情入理入丝入扣,你还有什么信不过的?看到吴庆德还不表态,宋小六又说,只要是花钱的地方,全部由我家大哥垫钱,所有股东哪里出过一分钱的本钱?吴庆德还是没有吱声,从腰间掏出烟斗,蹲在地上“吧嗒吧嗒”抽着。宋小六接着说,日本鬼子悬赏铜鼎三十万,我家大哥变卖所有宝贝和房产,按三十万给每个股东分了钱,他却变成了穷光蛋。吴庆德仰起头来,说罗宝驹眼光远,他盯着铜鼎上的藏宝图哩。宋小六叹一口气,说没错,罗大哥生怕日本人找到帝王宝藏,据李守文讲,日本人因为打仗,把国内的钱都糟蹋没了,就等着挖帝王宝藏扩充军费买枪炮呢。吴庆德说,事儿办砸了,罗宝驹可以拍拍屁股,跟着日本娘们去东洋享福去,俺们只能在这里等死。宋小六也蹲下身来,从吴庆德手里拿过火柴,给自己点燃一根纸烟,接着说:“罗大哥根本就没想去日本,他给俺留下一笔钱,是给樱子和孩子日后过活的,你想想,他若是打算去日本,把钱留给俺做什么?他这是要以命相搏,保全铜鼎哩!”
修鼎的人手备齐了,龟田次郎让邱连坤调查每个人的背景来历。邱连坤拿到名单之后,禁不住起了疑心,罗宝驹、罗良驹、吴庆德、吴宝才,这四个人从一开始就绑在一起,挖鼎、疑坟、造假、凿洞、盗鼎、毁鼎、分鼎、藏鼎,如今又合在一起修鼎,难保不出幺蛾子。邱连坤给孙发贵两天时间,把四个人的身世背景、技艺专长,查个底朝天,汇总成一份报告,交到龟田次郎手上。这一次,邱连坤没敢再冒失进言,规规矩矩立在一边候着。报告上已经列得清清楚楚,而且报告是孙发贵搞出来的,即便出了纰漏,也跟自己无关。龟田次郎戴上眼镜,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报告,让翻译官把罗宝驹带进来。罗宝驹进屋后,大剌剌地坐到龟田次郎对面的椅子里。他似乎是故意坐给邱连坤和孙发贵看,顺势还跷起二郎腿,冲着他们俩上下晃着脚。龟田次郎看了罗宝驹一眼,眼光中露出几分厌恶,他忍住没有发作,问道:“为什么要挑选吴庆德和吴宝才来修鼎?”
罗宝驹说:“吴庆德擅长造窑炉,能顺着风水地形造出好烧的炉子。”
龟田次郎冷笑道:“吴庆德是木匠,怎会造窑炉?”
罗宝驹说:“安阳匠人大都一专多能,俺兄弟罗良驹是修补瓷器的,他也能修补铜器。”
龟田次郎又问:“吴宝才能干什么?”
罗宝驹说:“吴宝才会看风水,选窑址就靠他哩。”
龟田次郎说:“窑炉就修在宪兵队大院里,不用看风水。”
罗宝驹说:“任何一处地方都有风水讲究,就算是在这间屋子里修窑炉,兴许北墙根合风水,就能修复铜鼎,南墙根没准就毁了铜鼎。”
龟田次郎捻着下巴颏儿,说:“你们中国人最会故弄玄虚,明明很简单的事情,偏偏说得复杂无比。”
罗宝驹说:“你若是不信,俺让吴庆德出个图,你们来修造窑炉,想修在哪儿就修在哪儿,俺们只管按工艺走过程,铜鼎弄成个啥球样,别怪俺们。”
龟田次郎最终同意吴庆德和吴宝才参与修鼎。罗宝驹前脚出门,孙发贵便撅着屁股向龟田次郎建言,说自打铜鼎出土以来,这四个人就抱团跟皇军对着干,咱们还用这四个人来修鼎,风险是不是太大了?龟田次郎冷冷一笑,说,就算罗宝驹有通天彻地之能,在宪兵司令部大院里、在皇军的眼皮底下,他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在龟田次郎面前,孙发贵屡屡抢先说话,让邱连坤很不高兴,他早就窝着一肚子火,便没好气地揶揄道:“孙队长,你以为皇军是你们侦缉队,一听枪响就尿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