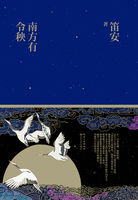龟田次郎用轻蔑的眼神看了一眼井道樱子,怀着一股复杂的忿恨,声音低沉地说:“希望你不会丢了我大和民族的颜面!”
罗宝驹被褚大奎绑架上山后,没想到能巧遇吴宝才。他问吴宝才,帝王宝藏可有眉目?吴宝才摇头,说是跟随线索到了林虑山下,拓片上的线索就断了。
原来,把铜鼎从宪兵司令部军火库弄出来第二天,罗宝驹就派宋小六给吴庆德和吴宝才各送去一万块钱。罗宝驹让吴庆德带着鼎耳前往洛阳藏身,让吴宝才暂时离开文官村,按照鼎耳拓片上的提示,结合自己的风水经验,寻找帝王宝藏。吴庆德无牵无挂,收拾个褡裢,当晚就上路了。上路之前,吴庆德顺路去了一趟向水屯,向李东家提亲,说要跟秀娥先把亲事定下来。李东家说秀娥是黄花大闺女,让吴庆德明媒正娶,回去找个媒人来提亲。吴庆德说来不及了,自己得罪了日本人,当晚就得离开安阳。李东家说,自家闺女不愁嫁,你跑到外地躲避日本人,一去十年八载,俺闺女干啥非在你这棵树上吊死?吴庆德没有言语,从随身的褡裢里掏出两千块钱,前后数了三遍,又掏出一把狗牌撸子手枪,对秀娥他爹说,你今天应了亲事,这两千块钱就是彩礼钱;若是不应这门亲事,就拿这两千块钱办丧事。秀娥他爹见到这么多钱,也不好意思动怒,说自古有强买强卖的,没听说有拿着枪强迫老丈人应亲的。吴庆德听秀娥他爹自称是“老丈人”,等于是变相应了这门亲事,便把两千块钱扔到炕上,说,娶你家闺女,安阳城任谁都不会下两千块钱的彩礼,俺就是要娶你家秀娥,别说等十年八年,就是等二十年三十年,秀娥也是俺的人。吴庆德说罢,抓起狗牌撸子塞进裤腰里,头也不回就去了。李东家在后面嚷嚷道,真让秀娥等上十年,两千块钱也就够饭钱……
跟吴庆德一样,吴宝才也是光棍一条。跟吴庆德不一样,吴宝才还有一个老娘、兄弟和弟媳妇。吴宝才反复掂量,自己躲起来容易,可日本人势必要拿老娘或兄弟顶包。于是,吴宝才把五千块钱分成两份,他娘三千,他弟弟吴宝贵两千。吴宝才对吴宝贵说,俺把日本人惹了,文官村算是待不下去了,你跟你媳妇带着咱娘,一起去西安投奔四舅去吧。吴宝贵两口子,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钱,两千块钱揣进裤腰里,就算让他们去阴曹地府,也决不会皱一皱眉头。吴宝才他娘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可她一点高兴不起来。她知道儿子肯定犯了大事,她也知道自己一走,这辈子再也回不来文官村了。思量至此,吴宝才他娘仰天大哭,直至泪水鼻涕灌满两个耳朵眼,这才坐起身来。于是,鼻涕眼泪又顺着两个耳朵流下来,样子甚是滑稽。吴宝才没有理会他娘的眼泪和鼻涕,正在给他娘一层一层缠着裹脚布,把三千块钱全部裹进两只小脚,最后小声叮嘱老娘,别让吴宝贵和他媳妇知道她身上有钱。吴宝才他娘捏了一把鼻涕,甩到了炕沿下,指着吴宝才的鼻子骂道:“娘个屄,你把你娘这把老骨头扔到西安,看你爹会回来找你算账不。”
吴宝才全然不理会他娘的心思,催促三口人趁着天不亮赶紧上路。吴宝贵两口子乐滋滋地推着独轮车,独轮车上坐着他们干瘪的老娘,咿咿呀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吴宝才打发走他娘和兄弟,一颗心才算踏实下来。他把洛阳铲的铲头藏进褡裢里,扛着杆子随后出了门,一路往西北走去。罗宝驹给他的鼎耳拓片,一块清晰,一块模糊,毫无头绪的枝枝叉叉令人费解。其实,就算是拓片全都是清晰的,吴宝才也看不明白。罗宝驹说这块拓片像是安阳的地形,还说有一个地方肯定是文官村,不然井道山兄妹也不可能找到北洼地。吴宝才的专长是探墓和打洞,探墓和打洞最早不是为了钱财,而是为了寻一把能够“迎风断发、削铁如泥”的宝剑。为了早日寻得宝剑,吴宝才就得不停地探墓和打洞,在哪里下杆子探,在何处下铁锹打,这需要眼力,也就是俗称的风水。安阳地界上,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有新的盗洞出现。吴宝才不放过任何一个盗洞,绕着盗洞周围一转就是一天,暗暗记下地形地貌、沟河走向、阴阳分隔,甚至连夯土颜色和味道,都烂熟于胸。对于风水,吴宝才属于无师自通,全凭道听途说来的几点要领,加上自己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水观。凭着风水经验,吴宝才从拓片上找到一处标记,近似于文官村北洼地,接下来有一条枝蔓往西延伸而去,所以他扛着洛阳铲一路西行。往西延伸也不是一直往西,有时候也往北。往北也不是全然往北,有时候还折回头来往南。跟随拓片指引,加上自己的风水经验,吴宝才在安阳地界上,曲折迂回了大半个月。待他来到一座山峦处,拓片上的枝蔓也到了尽头,至于帝王宝藏,仍是一无所获。望着眼前的山川巨石,找个下探杆的地方都不容易,此处又怎会是埋藏帝王宝藏所在呢。就在吴宝才暗自沮丧之时,突然,从巨石后面涌出几个持枪的土匪,把他连人带铲绑上了山。被绑上山之后,吴宝才这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林虑山,绑他的土匪正是褚大奎的手下。土匪们绑票之后,搜身时候下的工夫比绣花还细心。饶是如此,土匪们竟然没有搜到吴宝才身上的五千块钱,因为钱压根就不在他身上,在洛阳铲的探杆里面。
吴宝才对罗宝驹说,土匪们本来要拉俺入伙,可有个土匪认出俺了,他们就把俺关进了这个石洞。吴宝才接着说,土匪们把那张鼎耳拓片搜去了,褚大奎掂量了半天,就认定是铜鼎鼎耳的拓片。吴宝才又说,拓印的时候,把整个鼎耳的轮廓都拓出来了,识别起来一点都不难。罗宝驹点点头,对吴宝才的说法表示认同。吴宝才撸起裤腿,才想起洞里光线昏暗,他起身一瘸一拐走到洞口,从洞口的石龛里端来一盏小煤油灯,放在地上。重新又把裤腿卷起来,让罗宝驹看他腿上的伤痕,说是褚大奎对他用了两天大刑,最后实在熬不过去了,这才承认拓片是帝王宝藏的藏宝图。罗宝驹说没关系,你精通风水,大半个月都找不出一点头绪来,他们得到藏宝图也是瞎子摸黑。吴宝才说,若是再拿到另一个鼎耳拓片,或许会有一些眉目。罗宝驹皱起眉头,说文官村距离林虑山足有一百里的脚程,一个鼎耳指引的路程就有上百里远,若是再加上另一个鼎耳的路程,这帝王宝藏恐怕到山西地界了。天色已经完全黑了,狭窄的山洞里只有一盏花生米大小的油灯。一时间,两个人都闷着头,不再作声。罗宝驹盯着油灯上摇曳不定的小火头,似乎想起了什么事,他问吴宝才,你可曾记得“后母戊”三个字,在铜鼎底部的上下朝向?吴宝才说记得,若是正着看“后母戊”三个字,应该是右边的鼎耳缺了。罗宝驹说,对哩,这块拓片就是右首的鼎耳。
吴宝才嘴里念叨着:“左右,左右……右边的拓片是第二张藏宝图?”
罗宝驹点头:“左上右下,中国自古都是这个习惯。樱子说,他哥哥参考了小屯村挖出来的龙骨(甲骨),结合着右首鼎耳的纹饰,才找到文官村的。若真是一幅藏宝图的话,右鼎耳的纹饰应该是藏宝图的最后部分,指引的就是帝王宝藏的所在呢?”
吴宝才眼前一亮,问罗宝驹,帝王宝藏就在林虑山?
罗宝驹说:“左右,先左后右,东西,先东后西,从古沿用至今。鼎耳右首拓片应该是藏宝图的后半部分,它把你从安阳往西指引到林虑山,帝王宝藏有可能就在林虑山。日本人不用左右、东西来分上下,井道山先得到右首鼎耳,习惯性地从第二块下手,再往左首鼎耳上伸延,弄拧巴了,所以迟迟不得要领。”
吴宝才说:“林虑山方圆几百里,到处都是巨石,就算咱们知道帝王宝藏在林虑山,也无处下探杆,这个帝王宝藏,兴许就是以讹传讹哩。”
罗宝驹说:“且不管帝王宝藏是真是假,反正铜鼎不能让日本人弄走。”
一时间,两个人无言以对。沉默了许久,吴宝才问罗宝驹如何上得山来?罗宝驹就把自己被绑架的经过,跟吴宝才讲了一遍。吴宝才骂道,褚大奎真是想钱想疯了,要钱不要命,竟然敢绑罗大哥的票。罗宝驹叹口气说,早年间盗亦有道,劫道的土匪劫下钱财后,都会问问事主家乡何处,若是关里的就给足关里的盘缠,若是关外的就给足关外的盘缠,生怕事主半道上饿死,自己背上人命,背上人命倒不是怕官府追究,主要是自己良心上过不去。吴宝才说,青松岭的李二黑绑了安阳一家张姓屠户的儿子,张屠户把五千块钱如期如数送到了青松岭。李二黑见张家吐钱吐得容易,就又把张屠户给绑了,让张屠户家人再送一万块去青松岭赎人。张屠户的老婆七拼八凑,凑足了一万块钱,赶去青松岭赎人。李二黑听说张屠户的老婆亲自上山送钱,又起了邪念,非要亲眼看看人家婆娘俊不俊。张屠户的老婆又黑又胖又丑,李二黑一见大倒胃口,就把一家三口全撕了票,原因是张屠户的老婆看见自己的脸了,怕她去告官,不撕票不能自保。罗宝驹感慨一声,说等到人人都不讲道义的时候,就该变天了。
深夜时分,林虑山中一片死寂,野狸发情的尖叫声与栅栏外土匪看守的鼾声,此起彼伏。罗宝驹从地上端起煤油灯,把油绳从油海里挑出来一截,火头大了许多,石洞里顿时明亮起来。吴宝才说,土匪们不让把火头拨亮,说油海里这点煤油要用完三个月,才能再往里添煤油。罗宝驹微微一笑,说,你还真打算在这里待上三个月?
趁着灯光,罗宝驹打量着石洞四周。虽说是个天然石洞,可洞口居然有两根“石柱”形成支撑,究竟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罗宝驹没有看出来。石洞里面的石头,时不时有一两处闪光,罗宝驹把油灯凑上前去,用另一只手擦了擦石壁上闪光处,发现整块巨石竟然是一块火石。洞壁两侧还算光滑,有一个人工凿砌的石龛,正好用来摆放煤油灯,石龛上方是一大片黑色污迹,应该是烟熏后留下的。罗宝驹举起煤油灯,隐约看到洞顶上有很规则的纹饰,且觉得这些纹饰似曾相识。从未舍得把煤油灯拨亮的吴宝才,也瞧出洞顶的蹊跷,他站起身来,用手细细抚摸着洞顶的纹路,用肯定的口气说,这是饕餮纹。罗宝驹说,怪不得如此眼熟,跟后母戊鼎上的纹饰相同。吴宝才点头称是,说后母戊鼎鼎口是饕餮纹,下衬三周凹弦纹,底部是云雷纹。两个人端着煤油灯,继续往石洞里面探看,在石洞尽头有一条裂缝深不见底,勉强能钻进一只瘦狗去。石缝的走向,对应的是石头山的山体,即便是能够钻进去,也无意义。罗宝驹端着煤油灯临近石缝时,油灯的火苗突然跳动起来,似乎有一股很大的吸力,拽着火苗往石缝里钻。罗宝驹生怕煤油灯被风拽灭了,急忙把煤油灯撤回来,藏在身侧。吴宝才也暗自吃惊,说他晚上睡觉时,也能感觉到风,还以为是从洞口吹进来的。罗宝驹端着油灯,对着石缝反复试了几次,确定石缝里有风穿过。吴宝才说死穴无风,这里难道是个活口?罗宝驹没有应声,他怔怔地盯着石缝一侧的石壁发呆,因为石壁上恰好刻着三条凹弦纹,靠近地面的石壁上,则是云雷纹。石洞中,自上至下的纹饰,竟然与一百多里外出土的后母戊鼎上的纹饰,完全一致。一时间,罗宝驹和吴宝才呆立住了,侵入石缝的丝丝凉风,令二人身上的汗毛竖立起来。
突然间,洞口栅栏处的鼾声止住,接着传来土匪看守的喝骂声:“把火头拨这么大,不怕烧死你俩,赶紧吹灯睡觉!”
第二天大清早,褚大奎哼着“靠山吼”,溜达到山洞前,隔着栅栏问罗宝驹,写不写信,要不要赎金?罗宝驹说写,你给俺笔墨纸砚伺候。褚大奎如同变戏法一般,右手一扬便多了两样东西,纸和笔。褚寨主接着上一段靠山吼韵味,朗声念道:“林虑山,褚家寨,乃一穷乡僻野;文无房,学无书,岂能样样齐全。”
罗宝驹隔着栅栏接过纸笔,学着褚大奎的强调,说:“有纸笔,无砚墨,如何修得家书;知饥饱,无道义,乃一寨子蠢猪。”
“褚某人占山为寇,是个不会咬文嚼字的粗人,不跟你逞口舌之快。”褚大奎说完,冲着远处一挥手,两个土匪忙不迭跑过来。一个土匪手里拎着一只活鸡,另一个土匪手里端着一个黑瓷碗,来到山洞栅栏前,一刀割开鸡脖子,一股黑红色鸡血喷射到黑瓷碗里。待鸡血流干,土匪将半碗鸡血递给栅栏里的罗宝驹。罗宝驹站在栅栏前,冷眼旁观瞧着褚大奎演戏,并没有伸手接碗。褚大奎盯着罗宝驹,说这就是褚家寨写字的墨水,罗大爷就凑合着用吧。罗宝驹明白了褚大奎的意图后,方才伸手接过黑瓷碗,笑着问他,褚寨主整天脱裤子放屁,你累不累?褚大奎说,闲着也是闲着,好歹憋个屁,怎能容它是个空响。罗宝驹在一张缺条腿的破桌子上,摊开一张皱皱巴巴的宣纸,执笔蘸饱鸡血,顿在半空中,问褚大奎:“俺的兄弟们收到此书,便知道俺身困林虑山,接下来的后果,褚寨主都想好了吧?”
褚大奎说:“就算罗大爷的弟兄多,就算罗大爷的弟兄们人人都是两把自来得,恐怕也扛不过日本鬼子的正规军吧?日本的正规军都拿俺褚某人没办法,你们个把安阳城里的小混混,又能把俺如何?”
“日本人压根就没有把你当盘菜。”罗宝驹说罢,运笔修书,让弟弟罗良驹为他筹备两万块钱赎金,即刻送上林虑山。书信写好之后,褚大奎高呼一声:“来人呐!八十里加急文书,速速送到安阳城的罗家老宅。”
望着褚大奎一步三晃的台步背影,吴宝才对罗宝驹说:“这玩意儿真把日子当戏来演吧。”
罗宝驹点点头:“褚大奎快谢幕了,他这是自寻死路。”
三日过后,褚大奎又早起练嗓子,今天唱的是《背靴访帅》中寇准的一段儿:
西风急,斑竹摇,如泣如怨。
清风池,水叮咚,似弹哀弦。
寇平仲,哭忠良,难止泪点。
大宋朝,折柱石,谁来擎天?
将星陨落汝河畔,从此国运更艰难。
北国又把边疆犯……
就在此刻,一声尖厉的啸声由远而近,罗宝驹急忙把吴宝才推倒在地,自己也迅即趴下身去,只听到“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正好落在洞口,击中支撑洞口的石柱。紧接着,便听到连续二三十声爆炸,褚家寨顿时变成一片火海。
石洞中硝烟弥漫,罗宝驹和吴宝才几乎同时感受到地面在剧烈震动,并且从石缝中传来石头摩擦的刺耳声,整个石洞即将坍塌下来。就在此刻,又一颗炮弹击中石柱,连同洞口的栅栏轰了个粉碎。罗宝驹拉着吴宝才,一头钻出石洞,只听到身后传来震耳欲聋的碎裂声,声势之大远胜过炮弹的爆炸声。两个人压根就没敢回头观望,只盼着别被落下来的石块击中,两条腿撒着花儿,死命往山下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