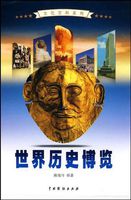进了吴王宫,我们被集中在小房间里,跪地听太监训话。
“你们这帮越国女奴,你们的勾践是我王的奴隶。白天充当马夫,任我王鞭打踩踏。晚上身处石室,内有牲畜作伴。勾践尚且如此,你们又算什么!从今往后,有不从者,先杖打二十。”
我们这帮歌舞伎被任意驱遣,身兼数项杂役。头天被叫去扫地,打扫宫中所有的庭院。打扫期间,有人看管,动不动就吆喝训斥。”正处夏季,烈日炎炎,没过多久我们就汗流浃背。翌日被吩咐去照料花草,拿着木桶就着池塘汲水,再一瓢一瓢地给草木浇水。干完之后,太监又说,某些花草需要光照,要我们把它们搬到太阳底下。日落时分,又吩咐把花草搬回原处。之后是洗衣服,擦洗林园中的桌椅等。稍有差错,立即遭打骂,骂我们是“该死的女奴”,更拿越王来讥讽我们。夜深回破屋时,人人浑身疼痛,都想着,还不如一死了之。
最恶心的莫过于洗粪桶。王宫上下,多少个臭粪桶,齐刷刷聚集在一处,臭气熏天。刚到门口,别说我等越女,连管事太监都呕吐不止,却命令我们不准呕吐。我和郑姐说干就干,撕下袖子,搓成布条,捂住鼻子,再拿起竹刷,拼命洗刷。白天一场恶臭,夜晚仍在堵心,面对食物,谁都难以下咽。可第二天,饥肠辘辘,浑欲虚脱。到了开饭时间,人人狼吞虎咽。管饭的太监们讥讽道:“你们这等食粪的家伙。”
后来,他们索性要我们专管刷洗粪桶。一个月后,有三人倒下,在刷洗粪桶期间。有人胡言乱语,说是瘟疫。管事吓得心惊肉跳,一声令下,要把我们统统烧死。郑姐抓着我的手,说:“姐妹们,我们跟这些鸟人们拼了。”终于忍无可忍,我和郑姐本来就是村姑,本来就有些蛮力,举起粪桶乱砸人,捞起竹刷乱扔人。管事太监破口大骂:“该死的越国女奴……”未待其骂完,我们高声大骂:“你不该死吗?你这断子绝孙的。”我们本来就是村姑,骂人的本领无师自通,只是平时不愿意骂。人群涌来,把我们团团围住。两个村姑带头使出蛮力,和他们扭打成一团。终究寡不敌众,被收拾得鼻青脸肿,之后被关押起来。
有个小太监跑到王宫,火急火燎地报告大太监。恰巧吴王也在,当面问责,于是事情暴露无遗。吴王责问某位夫人,她反唇相讥道:“勾践尚且为奴,她们还能享福。”吴王一时无言以对,却把管事太监杖打得皮开肉绽。
有医人被派来,一经查实并非瘟疫。可三个姐妹还是悄然离去,因为无休无止的劳作,如影随形的恐惧,兼之非人的居住环境,糟糕的饮食。想起入宫来的遭遇,人人以泪洗面。
当我们康复后,有位太监说,伯姬夫人有令,要我等明日拜见。我们被带到一座楼阁前,室内装潢甚是考究,有一丽人艳若朝霞映雪,正迎风舞袖,婀娜多姿。太监说,他就是伯姬夫人,要我们下跪。
夫人说,今晚大王会来,我等人要以歌舞助兴,吴王还要选一人侍寝。夕阳西下,吴王果然来。甩袖,转身,举手,投足,我们献上华丽的越国宫廷舞,脸上媚态百生。堂上的吴王,双手搂抱宠姬,双眼直视舞姬,欢笑不止。
“大王,你要哪个?”伯姬夫人问他。
吴王选了郑姐和我。也许我们是幸运的,还能住在伯姬夫人的寝殿里,当体面的奴婢。有宫娥告诉我们,想在王宫里有立足之地,必须依靠某位主子,自然是要我们向伯姬夫人投诚。
可过了数日后,郑姐说:“西施,我们暗地投靠伍姬夫人吧。伍姬夫人的爷爷是相国,整个吴国,除了大王,就属相国最大。”
我问:“那伯姬夫人又是什么背景呢?”
郑姐压低声音说:“听说伯姬夫人原是太宰的舞姬,有一回大王到太宰家做客,她负责伺候,就被大王相中。听说相国和太宰的关系不太好,所以二位夫人的关系也不好,彼此间又互相争宠。”
我哀叹着:“这里怎么和越王后宫一样呢?我还记得越王宫里的尸体,夫人争宠,最先死的是办事的奴婢。”
“谁叫我们生来卑贱呢?早晚都是死,投靠主子还能多活几天。”郑姐这么说。
“可我们目前住在伯姬夫人的寝殿里啊。还是走一步看一步为好吧。”我对郑姐说。
深宫里总是歌舞连连,因为吴王及其公子,无不喜好歌舞。有一回献完歌舞,在回寝室的路上,我看到一位妇人,上着短袖衫,腰间系着没膝盖的裙子,脚踏草鞋,头发凌乱,正拿着大扫把,埋头扫地,有宫娥太监们对她嗤之以鼻,甚至谩骂她。看那身影,似曾相识,我靠近一看,竟然是勾践夫人。难以置信,曾经尊贵的夫人,而今像个乞食婆。夫人尚且如此模样,越王和范大夫又该是什么模样呢?我轻轻地唤她夫人,她热泪盈眶,说我心眼好。才不是呢,我自我否定。
她先问我公子的事情,我说不知道,从入吴宫起,我们就被分开。我问她范大夫的事情,还没回答,她就掩鼻而哭,说他们夫妇和范蠡等人被囚禁在石室里,那石室不但阴冷潮湿,还难以遮风避雨,里头甚至还养马,总是臭气冲天,一到夜晚,蚊虫成群,根本就不是人住的地方。看她的脖子和手臂,明显有蚊虫叮咬的痕迹,我不禁流泪,为范大夫心疼。勾践夫人还说,一天所食,皆为不堪入目之物,却还不能填饱肚子,身上所穿,尽是破烂的粗布麻衣,石室附近连个像样的东厕都没有,更别谈洗澡,所以每个人身上都很脏。
由于身处王宫,行动不便,可我只能见缝插针式地向勾践夫人询问石室的事情。她说石室附近有个水池,水池底下是吴国先王的陵寝,住在陵寝边,夜夜听那鬼叫声,简直要吓死人。看夫人的神情,一脸恍惚,我猜想范大夫也该如此吧,心愈发疼。他们每天都要从事繁重的劳役,上山砍柴,割草料,打扫马厩,洗马,喂马等等。越王最惨,吴王外出时,经常令他当马夫,为其鞍前马后,任其吆喝踩踏,引来吴国百姓围观看热闹,人人极尽揶揄嘲讽之能事。勾践夫人说起这些事,都快泣不成声,我也跟着泪如雨下,心想着范大夫等人恐怕连乞丐都不如。
有一回傍晚,乘四下没什么人,夫人跟我说了很多。“可最难受的还不是这些,是那帮吴国马夫无休无止的鞭打和羞辱。草料没有割好,他们就棒打我们。马槽里的水没放满,他们就鞭打我们。收拾马粪时,如果铲子坏了,命令我们用手抓。你可知道,那些马夫还时不时地对我动手动脚,说一些猥亵的话语,搞得主公和范大夫等人和他们起冲突,可最后呢,挨打罚跪的还是我们。每到用饭的时候,那些混蛋马夫总要挖苦我们,说你们吃的是人饭吗,你们简直就是畜牲。是啊,他们简直没把我们当人看。”勾践夫人又哭成泪人,突然有太监吆喝她快点干活,所以我们不得不分开。
听了她的讲述,我夜夜为范蠡大夫流泪,心想着:“这可怎么办啊?”
可有一回,勾践夫人竟然说,范大夫是他们的支柱,若没有范大夫,他们难以活到现在。“不论发生什么事,范蠡总要尽力安慰我们。当马夫鞭打主公时,大夫甚至挺身而出保护主公。大夫时刻都在提醒主公,要学会忍耐,要想着越国今后,想着世子。”
突然间,我懵了,我不敢相信世间会有如此之人。
我私下里会见勾践夫人一事,被郑姐知晓,她责怪我,不该去理会她,是他们夫妇把我们往火堆里推。可我说,是为了范蠡大夫。郑姐说:“西施,他自身都难保,又岂能救你?现实点吧。不要想他,想一想如何伺候好吴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