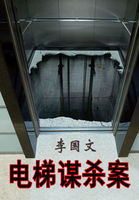心中供奉两朵花:一朵梅花,一朵雪莲。
女儿娒琪用一年半的时间念完高中,凭她的聪明和勤奋如愿以偿地考进了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一接到通知书她就迫不及待地要我去接她来重庆,说和我以及弟弟在一起是她梦寐以求的。等到我去接她,她又哭哭啼啼地放不下爷爷,说她走了爷爷会很孤独,
父亲是个一生有许多故事的人,年轻时曾走南闯北,见过些世面,也明白一些大道理。他安慰娒琪:“乖孙女,你就放心走吧!去闯你自己的未来,想到你们我就不会孤独,只要你们有出息,我就会觉得我也活得很精彩,何况达川还有你两位姑姑,她们会常来陪我。我也准备再找个婆婆,相互陪伴。”
娒琪破涕为笑,“爷爷你找得到吗?要那样真是最好不过。”
父亲说:“你就放心吧!我年轻时喜欢我的人可多哩,为了你走了的婆婆,我从来就没花过心,直到今天都还有人等着你爷爷哩。”
听着一老一小的对话我眼中未掉泪,可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恍若看见年轻美貌的母亲,活力四射的父亲,他们的年轻时代已远了,远得父亲硬着头皮说狠话去激励自己的后人,到远方他乡去追寻他们曾经的梦想和前途。
告别总是在车站,父亲牵着孙女的手走在前面,娒琪长大了,从背影看去已和身子佝偻了的爷爷一样高。临上火车时她把一万元钱硬塞进爷爷兜里,泣不成声地要爷爷保重,多保重……
父亲老泪纵横地看着我们,嚅动着嘴一个字也讲不出来,对经历了人间风霜的老人来说,泪珠饱含着千言万语,颗颗让人柔肠寸断。
我背转过身来,不忍也不敢再看眼前的这一幕。我和火车就这样将女儿接走送往她未来的前程,无数的车轮像父亲脸上滚动的泪珠,沿着女儿未来人生的路愈走愈远,愈走愈快。
女儿把头放在两只手掌上,任迎面的风吹拂着脸庞,她圆圆的脸庞珠圆玉润,大眼睛水汪汪的。
无数的山峦和村庄从车窗外一一掠过,朝身后家乡的方向跑去,女儿心事重重地望着窗外一言不发。
我摸了摸她的头说:“在想爷爷哈!重庆离达川近,往后你随时都可抽空回来看望爷爷。”
她回过头来直盯着我,用从未有过的那种目光,热切而专注得让我有些不自在。她说:“爸,我从小的事爷爷都给我讲了,谢谢你把我从小领过来,让我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长大成人,将来等你老了我也会陪着你一天一天地老去。”
看着她惹人怜爱的小模样,我有些不自在地摸着自己的胡茬儿说:“你今天怎么啦?命中注定你该是我的女儿,养大你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要如此感怀。”
“爸,我长大了,从此以后我要像一个大人一样。很认真地说,今后你可不许还当我是小孩。”
我乐呵呵地说:“好,爸爸往后把你当大人就是了。你考上大学已经为两个弟弟做了好的表率,接下来要在学习上多帮助他们,鼓励他们。”
“往后我能不能不叫你爸,叫你琪哥哥行吗?”
“为什么?”娒琪突然这么对我说,我有些意外。
“哪里有你这么年轻的爸爸?我拉着你走出去,谁也不会相信你有这么大的女儿。”她说完狡黠地笑了笑。
“这也可以,大作家汪曾祺写过篇文章就叫《多年父子成兄弟》,你想这么叫就这么叫吧,只是要注意场合。”
“好啊好啊。”听我这么说她高兴坏了。我接着告诉她,这些年爸爸做得不顺,生活的环境不好,难免会吃些苦头,让她有过艰苦生活的心理准备。
女儿小鸟依人地把头靠在我肩上,轻轻地抚摩着我的手说:“这些年你太不容易了,我明白你心里的苦和酸。你放心吧,我什么苦都能吃!你平时给我的钱我都积攒着,现在有十几万,即使将来钱用光了,我也可以去打工赚钱。爷爷常说,人受天意被地养,天无绝人之路。琪哥哥你别想多了,只要你愿意,你的人生随时都可以从头再来。”
听娒琪说话的大人口气,善解人意,我心中感到慰藉。只是她叫我琪哥哥,让我感到有点不适应,有点怪怪的。
火车到达重庆已是晚上,娒琪睁大眼四处张望。我说:“女儿,这城市也像你一样,长高了,长漂亮了。爸爸跟着变老了!”
“在我眼中你是永远不老的爸爸,不,是永远不老的琪哥哥。”说完女儿调皮地给我扮了个鬼脸。
回到家我觉得累,赶紧去睡觉。睡到第二天中午起床,娒琪早已把零乱的家收拾得井井有条,四处擦得一尘不染。
她叫我陪她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做饭。我说不知道菜市场在哪里,不如去外面馆子里随便吃点什么。她说不行,往后只要她在家就要自己煮饭烧菜。无奈我只好陪着她去找菜市场。
这天是星期五,该接子栋和子梁回家。吃完午饭我们早早地去了张老师家,两个儿子见了姐姐真是喜出望外,回家的路上他们一左一右牵着姐姐的手蹦蹦跳跳,有说有笑。我走在背后看着他们三姐弟,心中既高兴又酸楚。三个远离妈妈的孩子在一起时他们彼此就成了对方的欢乐和依靠,而自己这个做他们父亲的人又不争气赌得倾家荡产,三个孩子不知要历经多少坎坷才能长大成人?
这个四分五裂的家因为娒琪的到来才显得有了家的气氛,比起平时父子仨待在家中大眼瞪小眼显得柔和生动多了。我们平时懒惰的习惯也被娒琪一一纠正,每人睡觉前必须洗澡、刷牙,早上按时起床,我是最赖床的一个,每次都是娒琪点上一支烟放在我嘴上,把烟灰盅放在我床边,这是她催我起床的方法,不过这方法也真灵验,几口烟一抽人就清醒了,再赖在床上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只好乖乖起床。
两个年少的儿子,刚刚开始青春的女儿,加上步入中年的我,就这样在异乡相互搀扶,相互依赖地生活。
我不想再经营夜总会,觉得以我的才华和智慧,在年富力强时更应该去做一些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我将夜总会转手给周乃恩做,交接那天他请了很多朋友在一起喝酒,中途我一个人悄悄走了。
我独自徘徊在南坪街头,往暂称为家的东路而去。走到一家发廊门口我犹豫了许久四处张望,见没人就像贼一样钻了进去。
我知道这些深夜都还不关门的发廊是做什么的,在重庆随便走过一条街,这种发廊少说也有三五家。不止是在重庆,可能中国的许多条街道都如此,它们是为嫖客提供发泄欲望的场所,里面坐着一大堆来自各地的暗娼。此时,我正以一个嫖客的身份走进了这间发廊。我还是第一次进这种场所,平时除偶尔有过一夜情外,一般都是自满自溢。趁着酒兴,我硬着头皮还是走进去了,我的身体本能需要这种发泄。
老板娘对我说今天刚来了一位下岗女工,还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价格要高五十元,全套要两百五十块。我一言不发点了点头,随着那所谓的下岗女工走进了后面的按摩间,
我在里面抽了五根烟,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这个女的真是下岗女工,我听她说她的家庭,她的孩子,她的无奈和羞愧……最后我给了她双倍的钱,埋着头匆匆走出了发廊。
事后我向矮子说起这件事,他笑得捂住肚子蹲在地上,“你再找一个什么下岗女工,看她们是不是说的一样?”
我换了家发廊,矮子的话得到了验证。老板娘和所谓下岗女工所说的,和我前一次听到的如出一辙。
我和一个对我说谎话的年轻女人——所谓的下岗女工,像动物一样地交媾,带着些许的鄙视。对她,也对我自己。
我觉得自己有些脏,随即我又原谅了自己,我最多也只是看不起自己的肉体,无可奈何的肉体。我相信自己的精神只是附在肉体上陪同去嫖了一回,在这个得过且过,一切都在蒙混过关的年代,人和法制一样都是先骗了自己,让自己都觉得就应该这样、只能这样,然后再去骗其他的就不觉得是在行骗,就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顺其自然的。对于那些遭到惩罚和报应的人来讲,他们也只认为自己运气不好,因为人人都知道根本就没有一个真正的道德行为准则,尽管人人都想有,可它的确不存在,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残缺、不健康的。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后来每当我的肉体被欲望点燃时,我都会先喝点酒,为自己找个借口,走进那些不同地方的发廊,和那些素不相识的高矮胖瘦的女人抱成一团,然后付费走人。什么百年修来共枕眠,简直就是屁话,付钱上床想怎么眠就怎么眠。只是每次事后我都后悔,会对自己说,今天又喝醉了,乱七八糟的。
和我有过同样经历的人,大家都不必自责,因为一个正常人都需要正常的性生活,当你离了婚又没有情人,你就只能这样做,通过交易。……如果去搞有夫之妇,那是破坏人家家庭;强奸,那种代价更不敢想象。所以性和谐其实也应该是社会和谐的一部分……
平时我也常去白镜泊办公室坐坐,可他的确太忙了,旗下十多家公司,有两家还是上市公司。他成了重庆商界的领军人物。但他对我的态度仍旧没变,总是关心着我的发展,说我要是有好项目差资金他会不遗余力地帮我。我有时只想和他在一起坐坐,见他忙我就悄悄地走了,他也习惯了。我每次去过他那里,心情都很沉重,原来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如今他已跑得很远,而自己不但没有前进还在后退,而今这个时代又不像从前,似乎不再给我以前那样的机会。在一个比拼实力的年代,我除了有三个相依为命的孩子,其他什么也没有。
娒琪开学那天我专门从后门把她送进了学校,她问我为什么?
我对她说:“当年我从这所学校出来时,同学们都是兴高采烈地从大门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而我则是被当作一个病句被校方从后门删除的。今天我从后门把你送进去,是希望四年后你从大门昂首挺胸地走出去,只有那样我至今憋在心中的那口闷气才能出。”
娒琪望着我,自信地点了点头。
望着校园里雀跃的带着幸福感的新生,我陷入了回忆。
我指着左前方的七舍对娒琪说:“我当年就住在那栋楼的515房,在靠窗右边的下床睡了整整四年。而你今天还是住进了你毓娒妈妈曾经住过的四舍,当年我们称它为熊猫馆。你看,它四周围了一面小围墙。”
娒琪贴近我,小声问:“琪哥哥,听说你当年是为了给一位女同学送情诗而惹祸,被开除的,是不是?”
我侧过身,望着至今仍在的二食堂点了点头。
“你可是个诗人加情圣哦!”娒琪撇了撇嘴自言自语地说。看着她我也撇了撇嘴,仍旧点了点头。
三个孩子平时都在学校,我仍旧闲着,日复一日无所事事。周乃恩给我策划了一个大的项目,叫我研究老鼠避孕药。他说鼠是灭不完的,繁殖力又强;但如果它们失去生育力,数量会大幅减少。他认为我做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出名堂,就将这件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分给我做。他每每说起,我总当成玩笑。
周乃恩将夜总会接手干了不久就交回了承包方,这个生意在我手上还有些盈利,到他手上便净亏了。这一来周乃恩和苏雷也闲着无事可干,平时有事无事他给我打电话,约我去茶楼闲坐,听他漫无边际地乱侃,什么现在他坐的车越来越大,房子住得越来越小;衣服品牌越穿越大,全是佐丹奴等等。满腹牢骚,好像谁夺去了他该有的好日子似的。
一天下午,周乃恩很神秘地对我说:“琪哥,走,我请你去玩。”我问他去玩什么?他保证是我从来没玩过的,是最有意思的。
我说,不说清楚我就不去!他就告诉我,是请我去看棒棒嫖娼。我差点呸他,“那有什么好看的?”
周乃恩长长地吸了一口烟,压低声音说:“这你就不懂了,自己嫖有什么意思?完事后就后悔。我请我们楼下的棒棒嫖,我在旁边看,那才有意思,才真叫过瘾。婊姐的尴尬样子,棒棒的虎狼状,特别的刺激。”
周乃恩说他有一次找了个卖的到家里,开始还有兴趣,后来她讨价还价,一下子就不想再搞了。他对她说:“甭说了,我再给你加两百元,请个人来嫖你好不好?”那女的一听多加两百元当场就答应了,她只要有钱,给谁搞都一样。
周乃恩于是下楼去请了一个棒棒上来,对棒棒说了意图以后,那个年轻棒棒还有些不好意思,说:“大哥,你就甭拿我开心了,我还要去找活干呢。”直到给了棒棒二十元钱,对他说,只要跟婊姐做一回,这二十元钱就是他的了,他才相信。结果他爬上去才两分钟就完事了。完事后棒棒看周乃恩给女的拿了五百元,委屈地说:“大哥,这不公平,你给她都给了五百块,我可是出力气的,才给了我二十块!”
周乃恩说他哭笑不得,又加了十块钱给棒棒才打发走他。后来他回家时又在楼下碰上那个棒棒,棒棒笑着对他说:“大哥,又请我去吧!这次我不要钱了。”周乃恩没好气地骂了棒棒一顿,他才笑呵呵地走了……
“你要知道棒棒也是人,也需要,我这等于是在扶贫,做好事。”
听完了他讲的性扶贫,我才真正有些哭笑不得。我说:“这种玩法我就不去看了。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以后少干点这种无聊的事。”周乃恩听后不服气地说:“哼!啥子老哦,跟那些大佬比我还只是个儿童。”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笑得前仰后合。
后来我终于清楚了,我为什么喜欢听周乃恩瞎吹,是他吹的事虽然玄,但多少还有点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