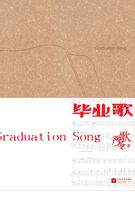从此地到彼地的漂泊才是我的宿命。
从北京我取道去了成都,路上我反复地想一个问题,我能给江嬅想要的生活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不会囿于书房,呼朋唤友,行走江湖,虎啸山林大概才是我的生活。从此地到彼地的漂泊才是我的宿命。
旅途中我收到江嬅一则短信:你以后可以到北京来发展,北京有很大的空间,我也想离你近点,更近点!
我回短信:我会来的!一定会!
到成都去是应过去的诗友尚仲所邀,他贵阳的朋友杨米干所做的一家公司即将上市,欲启动的一个项目需两千万元资金。说这事情已经有一阵子了,在订下赴京见江嬅的机票以后,我即通知尚仲,一两日以后我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去成都。
杨米干早一天从贵阳飞成都等我,见面以后我们谈了一阵子。他的合作方式很特别,想以证券回购的形式引入这两千万元,我问他能否开出两千万元的国库券代保管单,他一口应承,说没问题。我叫他回贵阳,待把一应手续办妥以后我即到那边。我给广州打了电话,问大哥陈大林两千万元是否能够抽出来,大哥说这个数字没问题,他们投资公司账上有五千万元的资金在找下家,关键是贵阳那边的操作要符合程序才行。
成都这个位于川西北高原山地和川中丘陵之间的城市,历来被称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明珠,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聚集之地。在成都我几乎天天和诗友们在一起品茶论酒,这些哥们儿大多摇身一变成了商人,做得最多的是书商。他们在晚上喝酒的时间想一个选题,再花上一个白天,在喝茶的同时做一个封面,接着就去开订书会。他们做的书都是迎合读者口味的,订单源源不断,钱也随之大把大把地先打到账上。钱到手时他们才去买书号,再把书印出来发出去。
张大水和当年就这样出了一本啥子可以说不的书,一下子就赚了两千多万;孙瑜文只一张订单就收了一拉杆箱的钱,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朱肱帮助谁跑跑腿,一单也分了两百万。
有了钱的诗友和书商们就开始没日没夜地享乐,酒喝得没有顿数,妞泡得没有路数。他们也讲一点义气,崇拜《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把女人不当回事,把荣华富贵当粪土。他们觉得什么都可以拿下,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以不同的方式一批批拿下,因为他们是诗人,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他们谁也不相信自己会受穷,即使兜里分文没有,也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富有的人,财富就在自己的脑子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他们目空一切,行事偏激,既然大地都在脚下,那么一切都在脚下。在他们看来,赚钱只是为了满足精神和灵魂需要的一种手段,否则才懒得去沾那些铜臭。
在成都陪他们过一阵子这样的生活后,回到达川我便觉得自己的生活了无情趣了。
你想,窝在丛山之中的小城,即使有钱也仅仅是个土佬肥。没有诗友,没有灯红酒绿,没有一日暴富,没有一夜穷愁潦倒,这样的生活算什么?诗意的生活应该是激动人心、跌宕人生的!
我计划着将来走出这个大山环抱的城市。世界很大,容得下他们,也容得下我!我渴望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向往他们那样的生活。
临近春节杨米干从贵阳打来电话,说他那边事情办妥了,希望我能马上过去,争取在春节前完成这笔资金交易。我与陈大林落实,他那里没有问题。我盘算了一下,事情成了我能有三十万元的利润。
听我说要马上动身去贵阳,石莲很不高兴,说她眼看临产了,这个时候我外出不是时候。说来也是,女人生孩子时谁都希望丈夫能在身边,医生说丈夫在身边能充抵掉产妇分娩时的一大半疼痛和不安。我答应石莲,会以最快的速度办完事回来,让她有什么事就打我的大哥大。
我在贵阳机场撇下杨米干公司接我的人,打了一辆出租车去他公司,一路上我与司机聊了聊,得知这家公司在贵阳是无人不晓,三天两头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他们的广告。到了公司所在地,贵阳很有名的一家宾馆,在总统套房改成的董事长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正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的杨米干,他一副春风得意的模样,面对镜头畅谈公司即将上市的美好前景。他拉着我当了一回嘉宾,我被他介绍为来自重庆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是他们重要的合作伙伴。
结束采访以后,杨米干给我看了当地一家银行国债服务部开具的两千万元国库券代保管单。
第二天我们就动身去了深圳,陈大林的投资公司在核实了杨米干的代保管单真伪后,马上就划了两千万元的资金给贵阳的杨米干公司。
我见事情大功告成,便想从深圳直接回达川。杨米干非要我陪他回贵阳,到那里以后才给我三十万元的中介费,还说我刚好可以考察一下他们公司。陈大林也劝我去贵阳,要我到那里看看能不能与杨米干他们进行更深度的合作。这么一来我就不好意思说家里石莲临产的情况,心里合计到那里只待一两天,拿了钱,看了他们的公司就走。
到贵阳后杨米干兑现了给我的三十万元中介费,晚上办了庆功宴,喝了酒以后硬拉我去夜总会唱歌。不知道为什么我拒绝了,回宾馆刚进房间就接到石莲从达川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她叫了我一声“琪”就开始哭,哭声不是悲痛的那种,是带着无限思念、呼唤以及喜悦的诉说。
我知道,是我们的孩子来到了人世。
我没打断她的哭声,想在这哭声中一直倾听和沉浸。
好一会儿她说:“琪,生了,我为你生了个儿子,我正看着儿子,给你打电话,我好想你,我好想你就在我身边……”说着说着她又哭了起来。
这是让我手足无措的声音,我醉了,从头到脚全都醉了;我笑了,对着璀璨的夜灯我流着泪笑。我傻傻地说:“老婆,你等着,我马上回来,马上!”
我打电话给杨米干,向他辞行,告诉他我又添了个儿子。我说,我得马上走。杨米干很是为我高兴,叫来司机开车送我去火车站,让我搭上了夜间十点多开重庆的火车。
一路上我都在想象儿子的模样,我希望火车快点,再快点,在我还没想完时就到重庆车站。
到达川时已是第二天下午一点多,我一口气跑上医院的五楼,抱起襁褓里的儿子就在产房跳起了探戈,放下儿子我又去拥抱还躺在床上的老婆。石莲的姐姐在一旁眼都看直了,笑得合不拢嘴,她本来就是这家医院的医生,出于感谢她对我老婆的关照,我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石莲姐姐说:“你还不快给儿子取个名字。”我说:“没问题,他哥叫子栋,他就叫子梁,再取个小名叫小二。”大家都乐了。
就这样,家里人叫开了“子梁”“小二”。
子梁满月以后我和石莲搬出了宾馆,住进了我新买的一处房子里。在达川城居住条件比较好的地段我给父母也买了一套,让他们从乡下搬到城里来住。
我觉得真正的家庭生活,像在重庆时的有家、有老婆、有孩子的生活开始了,不过也因为子梁的出生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多的变化。
石莲从前都是抱着我睡,可自从有了儿子,她就一直背对我睡,身子弯成一张弓,我扳都扳不动她,她说要时时抱着儿子。
考虑到石莲有了孩子以后对子栋照顾不过来,就让他也跟着婆婆、爷爷住去了。从来不愿和石莲见面的娒琪,几乎天天放学后都和子栋一起过来看一次小弟弟。
娒琪会在石莲不在面前的时候和我说一些悄悄话,告诉我生宝宝子梁的时候,石莲阿姨在医院里骂我了,骂畜生,骂没有人性。
石莲临盆住进医院时,因为我不在家,父亲和我妹妹赶到了医院。问一直照顾石莲的妹妹有没有这件事?她告诉我,石莲在产房里因为阵痛,将她的手都抓青了,怨我不在身边,骂几句也正常,不过当时父亲的脸很是挂不住。
想到父亲的难堪我心里很不好受,扪心自问:我没有人性吗?
我是为做生意,为赚钱而在妻子临产时出门的,我不能看着到手的钱不赚。或许,我错了。
小二被剃了光头,活像个小和尚,长得十分灵气,人见人爱。那时最为流行的一首歌是《回到拉萨》,每当他哭的时候我们就放这首歌,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出现他就不哭了,安静、专注地听歌。每每这个时候,他灵光浮动的神情让人不由得想到西藏的灵童。
自从做资金生意尝到了甜头,我对其他的生意便没有了兴趣。做这种生意干净利落,不求人反被人求。我卖掉了所有的项目,凑了两千万资金专门做这种项目。
我的生意做得轻轻松松。几千万的汇票揣身上,哪里需要就开着车去了,赚了钱便打道回府。1997年这一年我几乎就只做这种业务,开开心心地赚了不少钱。在达川很多人都知道我有钱,来找我合作做其他项目的人络绎不绝,我都不屑地一一拒绝。我常常在心里说:像你王琪这样的聪明人太少了,实在太少了!
不是我妄自尊大,放眼当地商界谁又能像我这样轻而易举地赚钱?那些呕心沥血成天忙忙碌碌的人,不是入不敷出就是欠银行贷款暂时撑着,说崩盘就崩盘。
这样的日子里我就有很多回忆的时候,想过去自由自在的日子,想过去那帮同甘苦共患难的朋友。
一天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从梦中惊醒。是谁这个时候来敲门?我怨气冲天地从床上爬起来,开门一看,吓了一大跳,是苏雷和一个满身是血的人站在门外,我忙把他们迎进来。
我问苏雷怎么成了这副模样?他笑嘻嘻地、满不在乎地对我说:“运气不好,又出事了。”我赶紧问又出了啥事了?苏雷说他在广州砍了人。
苏雷在广州开的“家乡远”川菜馆生意不好不坏,每月还能赚些小钱。前段时间广州当地一位道上混的,叫“一指宽”的大哥常带人去吃饭,每次吃了都不买单,一副横吃竖喝的样子。小本经营是经不起这样折腾的,苏雷每次见他这样,扇他耳光的心都有,可想了想还是硬生生地忍住了。总说和气能生财,百忍能成钢,他苏雷再也不想出错了。
大前天“一指宽”又带了一大帮人来,摆了两张台子大吃大喝,完了又想拂袖而去。苏雷实在忍无可忍地拦住他,请他买清单子再走。哪知他反手就抽了苏雷一个耳光,还问他馆子想不想开下去,说老子没收保护费算是给足面子,吃顿饭居然还敢收老子钱,真是吃了豹子胆。
苏雷本来还想忍的,“一指宽”临出门又冲他身上踢了两脚,这两脚踢出了苏雷的火气,他从身上拔出了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