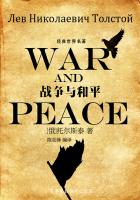一位端庄、漂亮、落落大方的年轻女人在陈总办公室里等着我们,一看就知道她是陈总太太陶姐。寒暄了一番后陶姐重重地叹了一声气,愁容满面地告诉我,陈大林不争气,前段时间到澳门赌博,输了两千多万,还欠了大耳窟(放高利贷的人)一千八百多万,加上驴打滚的三分天息,想尽一切办法现在还欠他们八百多万。七八个澳门过来收账的就住在公司附近的宾馆里,天天到公司里来闹。没办法陈大林只好先躲起来了,我的货也被陈大林低价贱卖了去还债。
“公司一下子弄成这样,太难了……”说着说着陶姐的眼泪就掉下来,哽咽着告诉我,陈大林专门吩咐过她,不能对不起我。眼下没钱,但他们公司有一辆凌志车,买时花了八十多万,才开了不到一万公里,就把这辆车给我,抵我的货款。
我一时语塞讲不出话来。首先我在内心里认定他们不是骗我,这种情况下好歹让我拿到样值钱的东西,是看在刘萍面子上善待我。
看着陶姐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心中顿时生发出侠义之气,想不要车子。苏雷看出苗头,在边上向我使眼色,我愣了一下,口中勉强挤出了一个“嗯”字。
最后我还是说要回去想想,明天再给电话。陶姐说我想好了随时过来办手续,立即就可以把车交给我。我连声说,“再说吧!再说吧!”
陶姐以为我不满意,说实在对不住我,请我包涵。给我的车现在能卖六十多万,要不是她不方便找买主,卖了车给我现金才对。
我知道陶姐误解了我的意思,想要解释什么,苏雷忙在旁打圆场:“仁义值千金,绝对值千金。我们会考虑将车收下。”
回到宾馆,苏雷劝我说:“人心隔肚皮,社会非常复杂。你的货50万可不是小数目,非亲非故的,没必要一冲动做仗义的事情。”
我说:“这违背我做人的原则,我于心不忍!”
“原则?钱才是原则,没钱的时候什么辙也没有。”苏雷提高了嗓门。
我知道苏雷这么和我抬杠子是为了我好,但还是拿不定主意,就想等花红回来商量了再说。花红给我留了张字条,说她出去转一转。
左等右等还是不见花红回来,我和苏雷就出去喝下午茶了。
喝了整整一下午的茶,直到吃晚饭的时候花红仍没回来。苏雷说,花红是不是找不到路,走丢了?我想不可能,心里猜测她为什么还不回来,吃完晚饭后更是替她担心。
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看电视,快到十二点花红才回来。我有些生气地问她:“咋个这么晚才回来?”她支支吾吾地说,“在外面玩,玩久了,忘了时间。”
我一听就知道她是在撒谎,见她不愿说,也就没再追问。心里想,她的模样是男人一看就动心的,出去勾搭了什么人也说不定。勾走就勾走吧,我又能怎么样,她又不是我老婆。
第二天上午花红找了个借口出去,依然是到很晚才回来。再三追问,她才说昨天认识了一位李哥,是广东本地人,开服装加工厂的。她说李哥对她实在是好,只是年龄有点大,四十几了。李哥给她买了很多东西,她从包里拿出来给我看,有戒指和金项链。
“下这么大的血本讨好你,你百依百顺了吧?”我有些酸溜溜地说。
花红说她昨天一个人在商场里瞎转,那个李哥上来和她搭话,要请她吃晚饭,她看他没什么恶意,就答应了。
“社会相当复杂,你个女娃儿也不知道自重,他要是坏人你咋办?”我一生气竟然用了矮子、苏雷他们的口头禅,说起社会复杂来。
花红说:“李哥是好人,我能感觉得到。他对我一点都不轻薄,给我东西也没要我和他立即做什么。他老婆去年死了,家里很有钱,就想再找个老婆。”李哥还对花红说,广东人很迷信,妻财、妻财、有妻才有财,想发达就要先娶老婆。
看起来花红对她的李哥非常中意,我再反对她的交往又算什么呢?花红总要嫁人,她在原籍名声不好,在这里能认识一个对她好的人是缘分,何况这个人开了爿厂,家境好、有钱。女人嘛,俗话说得好,“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花红能嫁个正经人,将来也就有了个依靠。
我认真起来,对花红说:“如果那人好,你倒真的可以和他好好接触。只是不要在外面上了坏人的当,我也是对你负责,怕你有什么意外。”
花红说:“李哥绝对是个好人,这一点我心里清楚。社会并没有苏雷说得那么复杂,就说殷哥吧,人家都称他赖死皮,觉得他是个坏人,其实他心地好得很。”说完,她心事重重地站起来,慢慢走到窗边。
背对着我,花红自言自语地说:“做牢、劳改的日子不堪回首。两个管教干部看上我,就想法把我糟践了。我能怎么样?姐姐被人糟蹋我替她动刀子,谁又能为我出头?毕竟是三年的日子啊,为了在里面能好过些,我只好忍受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出来后我是个坐过牢的女人,不仅仅左邻右舍的人知道,社会上的人很多也知道。好点的正派点的男人,都不会把我正儿八经放在心上。我心里很喜欢你,每次心里想到你,就有一种说不清的快乐和兴奋,我甚至觉得一切都开始变得美好,可你嘴边常挂着你的老婆、儿女。你一讲到她们就乐滋滋的,我心里不是个滋味。我知道你是个好人,琪哥,你和其他人不一样。你还有你的家,我随便找个人嫁了算了。我们这样下去,我会受不了的……”
我走到窗边扶着花红的肩,伸手擦去她脸上的泪,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个能让男人欲仙欲死的女人,历经坎坷,心里有散不尽的阴影,她该有自己的追求和生活呀。但一想到她和其他男人连在一起,我心里仍旧不是个滋味。
我一把将她抱起来放在床上,迅速脱光衣服,迫不及待地扑上去,近乎疯狂地在她丰腴而充满弹性的身上发泄着。
这个过程她没有像以往那么兴奋,她平静地对我说:“过了今夜,从明天开始,你就当我是妹妹吧!无论将来如何,我永远都会对你这个哥哥好,我本来就没有哥哥,你就是我的亲哥。”
我停下动作,紧紧地抱着她,一言不发。
夜里花红枕着我的手睡得好香好香,梦中死死地抱着我,生怕我突然就不见了。是啊,人不仅仅有欲望,更多的需要是情感和慰藉。
第二天下午我们才起床,花红打扮了一下去见她的李哥,我带着苏雷到陈大林公司去找陶姐。我想无论如何先收下车再说,反正苏雷会开车,我们就开着车回重庆。
到陈大林办公室刚坐下,突然就有一拨人气势汹汹地鱼贯而入,领头的那人粗壮、剽悍,身后的人喊他森哥。
陶姐忙不迭地站起身来说:“森哥,请坐。”
我一看就猜想这帮人是澳门赌场派过来找陈大林收账的。果不其然,森哥往办公桌上一坐,一巴掌拍在桌上对陶姐说:“今天再不拿钱来,你就得跟我们一起走,陈大林什么时候拿钱来,你就什么时候再回来。”
森哥说完斜眼看了我和苏雷一眼,压根儿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陶姐请森哥再宽限她半月,到时一定连本带息全还上。陈大林在操作一单外贸生意,有四千万的信用证马上就会从国外银行打过来,有信用证后公司马上就可在银行抵押贷款,还赌场的钱是可以保证的。
森哥脸一沉没吱声,把脚又跷到办公桌上。他手下有人说,“甭说那些虚的,不拿钱就跟我们走人。”边说边去抓陶姐的手臂。我本能地站起身来把那人的手推开。
“一个女人家,你们何必这样跟她过不去?大家行行好,她说了半月内还给你们,你们就给个机会!”我急不择言地帮着陶姐对森哥求情。
那帮人见我推了他们的人,站出来挡事,有两人立即从腰间扯出把一尺多长的砍刀。其中一人拿刀指着我脸说,“王八蛋,少管闲事,否则连你一起踩。”
我一看情况不妙,手开始有些微微颤抖。身边的苏雷见状开口了,他望着拿砍刀指着我的人,一字一顿地说:“放下你的家伙!”
另一手持砍刀的人见势将刀移向苏雷,说时迟那时快,苏雷怎么拔刀的我都没有看见,他左手一刀刺在拿刀指向他的那人小腹上,右手一刀刺在拿刀指着我的那人右腿上。
苏雷紧接着在地上打了两个滚,站到我身边来保护我。
直到看见苏雷手上提着的两把刀在往地上滴血,那一帮人才反应过来。
我斜眼瞟到那个叫森哥的人有动作,他正伸手从腰间摸东西,手刚露出衬衣我看见他拿着一把军用五四式,上大学军训时我让教官给我摆弄过这种枪。我手疾眼快地猛扑过去,一手一个擒拿动作别住他手腕,另一手将他的枪抢到我手中。
我迅速将枪上了膛,抵在森哥的头上:“谁都不许乱来!”
我故作镇静地暴喝了这一声,心里其实害怕得很,一阵怦怦乱跳。我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但明白绝不能显软相,不然就会吃眼前亏。
他们受伤的两个人蹲在地上,血不住地从伤口流出来。陶姐吓得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森哥脸上可一点惧色也没有,他用命令的口气叫我放下枪,说不放下就要我的命。
这时外面进来一人吼道:“都不要乱来哦!警察马上就到了。”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陈总公司还是森哥的,我知道苏雷祸闯大了,警察一到他必然是逃脱不了。我叫他从窗户跳出去逃跑。
苏雷跑到窗前一看说:“不跑,八楼,跳下去也是个死。”
“那快,快从门口走。”我歇斯底里地叫着,谁敢拦住苏雷,我一定会一枪打死谁。
苏雷正准备从门口走,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冲了进来。“举起手!不许动!”呵斥声此起彼伏。
看见我手中的枪,他们如临大敌,两警察一边一个用枪指着我的头,我生怕他们开枪或者枪走火,连忙把手举过了头顶。
“放下枪,抱着头,靠墙蹲着。”一名警察命令我。
我放下枪后,老老实实地蹲在墙角,双手抱住头。我心里想后果,清楚知道只要他们问明情况,我绝对没事。
所有人都被铐上了,除了两个受伤的人,我是唯一被反铐的。两名受伤者被警车送往医院,我们一行人被押着走向公安局。公安局不远,走一百米远就到了。
广州警察的办事效率很高,我们每个人都被单独带到一处做笔录,陶姐是第一个做的。临到我的时候,我如实将情况说了。警察说我胆子真大,他们让我在做的笔录上按上指纹。晚上八点钟过一点,一名警察过来为我解开手铐,说陶姐为我担了保,我可以走了,但必须随传随到,要我来时他们会通知陶姐。
走出公安局大门,一阵清风迎面吹来,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在门外等着我的陶姐先带我去饱饱吃了一顿。
陶姐对我们今天出手相救很是感激,说我们真义气,要不是我们她这时大概已经被这帮人关到什么地方受非人折磨了。虽然出了事,她会尽全力摆平。广东省公安厅老陈很熟,已经找到他帮忙,要想办法把苏雷弄出来。因为她而让我们背祸上身,她心里很是不安。
我要陶姐不必自责,事情都出了,我们一起担就是。陶姐说要对苏雷负责到底,将来她和老陈还一定要报答我们。
回到宾馆我把事情跟花红讲,她听后十分着急,说要是苏雷出了啥事回不了家,我怎么面对赖哥,又怎么给苏雷家人交代?
我想想也是的,一肚子心思。接下来几天里,我每天都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
我天天都要和陶姐见上一面,她一脸的倦容,每天都在为这事跑进跑出,花钱托人。陈大林在国外谈生意,正是信用证要办下来的节骨眼上,她怕影响他,没跟他讲这边发生的事。
花红也找她的李哥想办法。刚开始时李哥说没问题,一点点钱加上一点点关系就搞定,可是到最后什么也没搞定。
十几天后我们在广州等来的是苏雷被判三年劳教,送到了广东省赤泥煤矿。
陈大林从国外回来了,带回了国外银行出具的四千万元人民币信用担保证明。他听陶姐讲完事情经过很是感动。他说,这年头这种生死兄弟实在难找。他一定要和我结拜兄弟,并说他会找关系让苏雷在矿里不吃苦,给苏雷三十万作为感谢和补偿。
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我和陈大林喝了鸡血酒,按江湖规矩拜了把子。他比我长两岁,成了我大哥,我们对酒当天,稽首面地,发誓将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没隔几天陈大林的两千四百万银行贷款到账,他非要划一百万给我,说是七十万给我,另外三十万带给苏雷的姐姐。
我执意不肯,说只要八十万。五十万作为我货款老本,另外三十万我带给苏雷姐姐,存在她那里等苏雷劳教出来给他。苏雷从小父母就死了,跟着姐姐长大,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四处流浪,曾几次进劳教所和劳改队,一生真是牢役命。
花红和李哥的关系发展神速,已在谈婚论嫁,决定不和我回重庆了。
我回重庆那天,陈大林和陶姐开车送我去机场。在机场,他递给我一张一百万元的银行汇票,我也就不再推辞,想大家既已是兄弟,来日方长。
来的时候我们是三人一道,剩下我孤身一人回去。三人的命运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想到苏雷我非常内疚,大哥虽给了他三十万,可他要失去三年自由,有什么比失去自由更让人痛苦呢?
回到重庆后我找到赖死皮,把广州发生的事如实对他讲了。他听后一言不发,后来重重地叹了口气:“唉,这是苏雷的命!我和他可以说是生死兄弟,你要吩咐陈总每个月都到劳教所去看他,他那牛脾气千万不要在劳教所里犯,但愿他能够三年后平安回重庆!”
看赖死皮难过的样子,我也心痛之极。我让赖死皮宽心,我会交代陈总按他说的去做,陈总是个讲情义的厚道人,会像照顾自己兄弟一样照顾苏雷。说到给苏雷的三十万元,赖死皮的眉头舒展了一点,说苏雷在里面有个想头了,坐一年就有十万,不像以前的牢坐了白坐。
第二天我提了四十万现金和赖死皮一起去苏雷姐姐苏珊那里。那年头四十万可不是个小数目,苏珊哭了一阵把钱收下了。
赖死皮再三吩咐苏珊,这钱一分都不能动,等苏雷出来要如数给他。平时家里有什么急用可找我们拿。
事情总算处理完了,此后一段时间我在重庆连门都极少出。想到广州发生的事,觉得苏雷说社会复杂的话还是有道理的。谁都无法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也不敢保证自己会置身事外,这就是社会的复杂之处。
天天待在家里带儿子和女儿才是最安逸的。
桃花红、春风暖,这已是1991年的春天。这天下午我抱着儿子,带着女儿到公园闲逛,明媚的阳光,盎然的春意让我诗兴大发。我在小卖部买了笔和纸,趴在石凳上奋笔疾书:
春
阳光慢悠悠地针灸着
正在复苏的大地
树枝撑着绿色的伞
一夜长进三月的花
青草顺坡登上山顶
鸟儿在枝头凭空唤出了无中生有的嫩芽
见你无处不在
我心底激动不已
姑娘 我的心性迅速随你长进理想
爱情随风而动
在故事中捕捉蝴蝶
天啊!你一朝变脸
气节就顺脸而变
花和鸟各自私奔
早该离开那冷酷的恋人
去强求火热的爱
在四月定婚
六月睡上夏季的新床
秋后一到就儿孙满堂
写完后我余兴未尽,对着儿子和女儿大声朗诵。儿子听得手舞足蹈,女儿听得若有所思。她望着我说:“爸爸我听不懂,春天和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吗?”
我兴趣十足地对她说,每一年春天来了又走,还将来,还将走;我们虽看不见、摸不着,但能感觉它!在这种感觉中你和弟弟一年年长大了,这就是春天和我们的关系。
看着她似懂非懂的样子,我又对儿子说,“乖儿子,你懂吗?”儿子用小手指指着旁边的花草树丛不住地点头,仿佛在说,我全懂了。
晚上回到家我非要和毓娒饮酒,她平时滴酒不沾,不忍拒绝我浓浓的兴致,陪我喝得满脸通红,听我微醺后的语无伦次。
我说:“亲爱的老婆,我打算以后常在家中陪着你们。钱我们有,养家糊口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