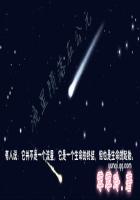《王府》
众人散去之后,济敏回到自己院中,吩咐珊瑚在自己的首饰匣里挑选两件漂亮的首饰,自己又换了一件素净的衣服,重新换了发饰。珊瑚十分不解,挑了一支凤钗和一支点翠送到济敏面前,见其他侍婢皆已下去,便问:“姐姐是准备回去看望阿玛?”
济敏拿起首饰看了看,又命珊瑚装入匣中,摇头道:“去向新侧福晋请罪。”
“她会得宠吗?昨夜王爷撇下她到这儿来,刚刚又因为姐姐听了她们许多冷嘲热讽的话,咱们现在去妥当吗?”
“无论怎样,她如今已有了身孕,万一将来生了一个男孩……咱们要想在这里立足,还是不要得罪太多人才好!”自进府以来,她一直表现得无比顺从知礼,若非如此,又怎能得到佳泰的信任。
“只盼着姐姐早得贵子,这样不仅能够安安稳稳地在府里立足,说不定将来也能帮上咱们钮祜禄家重新富贵起来!”
听到珊瑚的话,济敏又想起昨夜醉酒后的他面对自己时,嘴里却始终唤着另一个人的名字,不由恨意暗生。
合玫早早替济敏向湘雪赔了罪,湘雪这才知晓合玫竟是济敏的亲姑母,自然也知道了珊瑚的身世。湘雪知她一直跟在胤禛身边照顾了多年,便也对她十分尊敬,并未为难,倒是让合玫心里越发喜欢这位年纪轻轻的侧福晋。因顾及合玫的面子,湘雪对济敏以礼相待,并未因自己的身份在她之上而为难。她本不愿接受济敏的礼物,听得济敏提及合玫,只得收了下来,又回了一份礼与济敏。
待到晚间,合玫又前往济敏的院子,将她姐妹二人训责了一番。原来昨晚胤禛喝醉后正要去往倚云斋,珊瑚正陪着济敏在倚云斋附近散心,看到胤禛醉得厉害,便将他扶到了自己的院子。济敏点头认错,珊瑚却满心不服,朝合玫道:“姑姑以往不让姐姐留在府里,是怕姐姐不受宠。如今,姐姐得了宠,姑姑又来说姐姐的不是,姑姑究竟要姐姐怎样?”
“混帐!”合玫打了珊瑚一耳光,气得珊瑚起身跑了出去,济敏依旧跪在原处,一脸平静,合玫又道:“姑姑在宫里待了那么些年,后宫妃嫔的手段可都要高明得多,却也难逃过众人的眼睛。姑姑的年纪虽大了,但还没老到眼花耳聋的地步!想要长长久久的安稳日子,一定要安分守己!四阿哥怕是为了顾全我这张老脸,才没责罚你……”
“万一是因为他爱我?姑姑怎么就肯定王爷是因为姑姑才没有惩罚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姑姑一定要认为王爷不会爱上我?”
望着济敏满眼是泪的样子,合玫也软和下来,不由心疼地将她拉入怀里安慰:“是姑姑错了,你没有错…四阿哥是喜欢你的…”
“他一定是喜欢我的…我那样爱他,他一定会喜欢我的……”
胤祥一边劝慰德妃要保重身体,一边感激她对他们兄妹的照顾,德妃便也含泪嘱咐有了琪雅的消息一定要尽快相告。胤祥坐了一坐便带着沅歆一起离开了永和宫,胤禛还在乾清宫,只剩下湘雪坐在德妃远处的椅子上。少了琪雅和胤禵的永和宫陷入深宁的寂静,德妃对湘雪也忽冷忽热,她只略坐了坐便回了王府。德妃一边感叹有情人终成眷属,一边又质疑爱情的长度,认为只有像赫舍里、佟贵妃那般在红颜未减之际凋零方能有爱无怨。湘雪自己亦不知道胤禛的爱会停留多长时间,却并不因此烦恼,宁愿他忽略自己,这一生便也再无关联。
大夫常常去倚云斋,府中的女子对于湘雪有孕之事也半信半疑。从佳泰处请完安出来,湘雪便准备回倚云斋,路经廊下之时,府中一众女子纷纷闭口不言,朝她投去各种各样的目光,或嫉或恨,或嘲或讽。在她们眼里、口中,年湘雪俨然是一个举止轻浮的女子,凭着一些媚术、手段才得以飞上枝头。各屋的主子虽态度不一,但也都不愿与她相交。在王府之中,说不上四面楚歌,但也如置身牢笼,任人指点。
表面上,她总是置若罔闻、满不在乎,让納其夏、遇茶也不知从何劝起。至夜深人静,那些恶言恶语重又一起充斥于耳,让她难以入眠,便时常抱膝而坐。怕被丫鬟听到,只敢悄声流泪,哭到到累时、困时,方才入眠。
这样孤独的夜晚,她总会不由地怀念蜗居在同顺斋的日子,那些少年强说愁的时光。她还没向琪雅说完的江南风景、盛京风貌……想到琪雅,便又沉浸到更遥远的想象中,想象琪雅坐在高高的马背上,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蔚蓝的天空中雄鹰翱翔。科尔沁纯澈的阳光是否能晒去琪雅的悲伤?
几日过后,府中对于她的议论声突然消失了,但众人的眼神依旧带着原有的轻蔑、嘲讽。她知道这一切定然与胤禛相关,然而胤禛却很少踏足倚云斋,二人互相躲避。整个小院像是沉睡了一般安静、冷清,她不敢去等待胤禛的到来,甚至不允许自己产生那样的念想,沉默地坐在灯下,翻看手边的诗集,暗自嘲笑自己。
纵使反抗,也是徒然,还是坐到了这盏灯下。她把自己定义为政治工具,发誓决不做第二个苏勒,将自己束缚在冰冷的面具下,束缚起她的真实,吝啬笑容和言语。她的冰冷、安静也让府里的女人打消了许多坏念头,众人见她并不得宠,也不再为难。
胤禵送嫁回京后,康熙果然允诺释放了梅沾。胤禵和将梅沾送到宫外,二人沉着脸,在热闹的街市上走走停停。他们走到年府门前,看到大门上挂着锁,都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时至秋日尽头,叶已散落,老槐树上悬着数盏花灯十分显眼,曾经的光鲜亮丽都已被时光、风雨剥蚀尽净。一阵风微微而过,那盏梅花灯忽地滑下枝头,滚落到梅沾脚边。他蹲下身去捡起梅花灯,细细拂去上面的尘埃,嘴角染上浅浅笑意,定是又记起了琪雅。梅沾小心翼翼地提着灯继续朝前走去,胤禵望了望树上的花灯,又望向年府,心里涌起诸多遗憾,终于移步离开。
临近天涯阁,梅沾忽然止步转身问胤禵琪雅可有什么话留给自己。望着梅沾手中陈旧的梅花灯,亦如消失了笑颜的琪雅,胤禵摇了摇头,道:“她最希望的便是你能将她忘了!”
梅沾笑着点点头,顾自离去。看到一队迎亲的队伍,梅沾冰冷的眼中充满恨意,他暗暗发誓,终有一日要让胤禛为当日的自私付出代价。
早朝过后,胤禛急急出宫,将梅沾获释的消息带到倚云斋。湘雪只淡淡地道谢,又命納其夏送茶,便不再与胤禛言语。胤禛也只略略站了站,也未喝茶,便离开了倚云斋。胤禛并不知道,其实胤禵一早便命人暗中将梅沾的消息传递给湘雪,得知梅沾无恙,她也安心不少,又嘱咐送信人让胤禵多加照顾梅沾。
二格格的生辰到了,只是寻常家宴,湘雪让遇茶挑了几件贺礼送到李氏屋里,李氏便又邀她赴宴。近日偶感风寒,她本不想去,又不愿拂了李氏的盛情,且遇茶、合玫等人一直劝着,便着了件家常的淡青色旗装去赴宴,在众人华服锦衣的映衬下越加孤清。
胤禛也在府里,独自坐在主位上,依旧是一袭墨色衣衫,目光恍惚,略显疲惫。既是家宴,并无亲友,只是府中各屋各院的主子。湘雪坐在佳泰左边,李氏坐在佳泰对面,笑语盈盈、神采飞扬,不时软声细语地起身叮嘱身后的孩子几句。湘雪左边是耿氏,对面坐着的是宋氏和济敏,济敏穿着一件品月色的梨花纹样的旗装,发上也簪着梨花式的珠花,半分娇美,半分清雅。佳泰则是暗红色的如意纹样衣装,簪着金制的珠花,余者皆精心妆扮,浓淡不一却都摇曳生姿。
一时众人齐举盏祝贺李氏,一时三两人互相举杯,湘雪接了几杯,并不曾真饮。她本不善饮酒,何况在众人眼里她是有身孕的,便也不用多加应酬,只喝了几口淡茶,静坐在一边,看着众人欢闹、说笑,脸上带着似有似无的笑。
湘雪原本就没什么胃口,待上了一道汤品,便也懒懒地放置一边,依旧喝茶。佳泰见她身形清瘦,面上血色不足,又不曾好好用膳,便劝道:“瞧着妹妹只是喝茶,都未用些吃食,可是不舒服?”
佳泰话音刚落,众人目光皆聚到湘雪身上,胤禛也抬眼看去,案上的食物果然未减,不由皱眉。湘雪一直垂目而坐,自是没有注意到胤禛的目光,她起身朝佳泰福了一福道:“多谢福晋关心!并不不适,只是没有什么胃口。”
众人以为她是因为有身孕,所以饮食习惯变化无常,不由窃窃私语起来。李氏笑着站起身来走到湘雪面前,亲自揭去汤品的碗盖,拿起勺微微在汤里晃了晃道:“如今妹妹有了身子,为了孩子也不能全部任性。这道汤品最是适合妹妹,妹妹且尝一尝。”
李氏一向温和体贴,湘雪不忍推辞,便接过勺浅尝了一口,却忽地犯起恶心,侧身掩口吐了起来,李氏吓得赶忙上前抚背。她本不大吃鱼,加之患了风寒,越加受不住那股鱼腥味,落在众人眼里却又是另一重心思。
李氏和佳泰忙着照顾湘雪,余者或起身相问,或静坐不言,冷眼相看。一直沉默不言的胤禛忽地起身走到湘雪面前,众人纷纷散开。湘雪抬眼看到胤禛,心中百般滋味,还未及言语,却被他打横抱起径直离开了宴席。
众人面前,她虽心有抵触,依旧顺从地任由他抱着。待穿过小花园,离倚云斋近了,湘雪却淡淡道:“放我下来。”
胤禛低头看了她一眼,却将她抱得更近、更紧,一脸沉默的怒气。湘雪知晓他的固执,不得不妥协,不由咬唇,泪意涌动。一直到了倚云斋内室,他方才将她放下,二人复又陷入沉默的对峙,直到遇茶领着乔大夫进来,才打破了满室的寂静。
胤禛离座前便差人去了乔家小院,乔大夫来得这样快,湘雪自然也能猜到几分,心绪越加复杂。问诊后,乔大夫道并无大碍,留下一份药方与胤禛,便又带着遇茶回乔家小院取药。
“这样恨我?要这样伤害你自己?”胤禛的眼里明明满是愤怒,语气却显得十分平静。他以为湘雪久不就医是故意糟蹋自己的身子,以此来反抗自己。
湘雪依旧不言语,嘴角弯起一抹淡淡的笑,静静地看向胤禛极力压制的愤怒。她原先不看大夫只是觉着风寒而已,且素来最厌服药,便不准人请大夫,胤禛却另作他想,不由觉得好笑。她还没想过要这样报复他,亦不想再次卷入是非之中,只想着安安静静地在这府里老去。
面对她的沉默,胤禛越发愤怒,却又极力克制着,几乎要疯了,正要转身离去,却听湘雪在身后淡然道:“我不会糟蹋自己,还请王爷不要迁怒他人!”
等来这样一句回复,胤禛心里满是寒意。他想,她心里已经没有自己了,头也不回地离开倚云斋。
秋雨沙沙,带来许多寒意,湘雪坐在屋里也加了一件坎肩。修养了数日,喝了一大堆苦涩的药,风寒很快便好了。这段时日,胤禛再也没有来倚云斋,乔大夫却依旧日日来问诊,只是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又嘱咐丫头们好好照顾,便速速离去。这日,下着雨,待乔大夫诊完脉后,湘雪便让他日后不必日日再来,乔大夫一面点头答应,一面又嘱咐她多加休息,便撑伞离去。
乔大夫走后,湘雪又坐到书案后抄写纳兰词打发时间,納其夏又端了一杯茶进来,站在湘雪面前久久不离去。见她似有话要说,湘雪便抬起眼朝她道:“每次都是这样,哪天我若是不愿搭理了,仔细闷死你!”
“是、是是,都是奴才的不是!”
“说吧,别白认了这次错!”
“按照原来的说法,也该是两个月了,可格格这样子怎么也不像是有身孕的样子!便是以后要说成早产,可如今……往后是越来越难瞒人了,王爷究竟想怎么办?”
这个谎言使她嫁入这个王府,却也为她带来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还得遵循着孕妇的禁忌过日子。她管不了胤禛打算怎么办,连日来天天见大夫,还要喝一些无关紧要的补药,她早已想好了对策,便停住笔道:“外面还在下雨吗?”
“还在下,只是雨小了些。”
“那正好,等一会儿记得让人去请乔大夫再来一次,若是在路上遇到其他院子里的人,记得得装的伤心些,别还是嘻嘻哈哈的。”
“格格是想……可还没和王爷商量,格格这样自作主张,怕是不好吧……”
“商量了还叫意外吗?”
湘雪正要出去,打算故意摔一跤,结束这个越发难以继续下去的谎言,刚走到门边却见遇茶急急进来。
“侧福晋,有个小公公要见你!”
遇茶话音刚落,小李子又笑又哭地出现在她们面前,納其夏激动不已,上前狠狠拍他的脑袋。“小李子,还以为你被狼叼走了呢!怎么到现在才出来?”
“格格,納其夏——”被納其夏那么一拍,小李子更加激动了,热泪盈眶地看着湘雪,湘雪回过神来,脸上也浮出淡淡的笑。
“还好吗?有没有人为难你?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急死人了!”等不及小李子说话,納其夏噼噼啪啪地问了一大堆问题,让小李子突然破涕为笑。
“有格格和你惦记着,当然过得好!”
“那怎么都不出宫呢?出不来了吗?”
遇茶端来一杯热茶,小李子赶紧捧在手里驱寒。看到小李子,湘雪便想到了琪雅,想到同顺斋的日子。那时她一直都迫不及待的想要逃离那里,此刻却希望那样的日子可以永无止境地延长下去,便也没有如今的悲伤。
湘雪又让遇茶取了些点心过来,让小李子垫垫饥,没了琪雅的庇护,想必他如今在宫里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快活了。望着小李子狼吞虎咽的样子,湘雪倍感心酸,納其夏一边劝他慢些吃,一边心疼地抹泪。
待小李子吃完点心,納其夏又倒了一杯茶塞到他手里,湘雪便问道:“可有公主的消息?”
“送亲的人已经都回来了,公主托人把这个盒子带回来给格格,奴才就求了管事的魏公公,把这件差事揽了过来,这才出来了!”小李子拍了拍脑袋,急急从怀里掏出一只狭长的锦盒,遇茶上前接过来交到湘雪手里。
那是一根绳编的项链,上面缀着鹿角雕成的兰花,精致却不张扬,透着淡淡的兰花香味。一路上,琪雅一直不断打听着京城里的消息。得知湘雪嫁给了胤禛,十分开心,将草原上珍贵的兰草鹿角项链让人带回了京城。那项链本是一对,是仓卓的贺礼,据说能给佩戴的人带来好运,琪雅留下了她的姐姐穆哲戴过的那根。
一路上,腾济格对琪雅体贴入微,不断问寒问饥,滔滔不绝地为琪雅讲述梦中的科尔沁草原。在他的描述下,琪雅早在心里看到了绿草、蓝天构成的温暖画面。他告诉琪雅,已经为她准备好了一匹性格温顺的马,她可以在广阔的草原上尽情奔驰。腾济格直爽而又善良、正直,脸上始终保留着明媚的笑容,晒到心里,暖到心里,使她没有勇气伤害这个草原男子纯澈的心。
一路颠簸,伴随着某一个黄昏的到来,他们终于抵达了辽阔的科尔沁草原。马车外围满了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打起马车的帘子,对琪雅露出温暖、慈祥的笑容,那么亲切,瞬间消解了她心中的陌生、担忧。
腾济格翻身下马,大步走到马车前,打横将琪雅从马车上抱了下来。男女老少都高声欢呼了起来,围着他们又跳又唱,一直将他们送到蒙古包中。躺在腾济格的怀里,他满脸的喜悦印在琪雅氤氲着哀愁的眼眸里,她忽然在那一刹那感觉到了家的温暖,霎那间却又想到梅沾孤单的身影……
热闹的篝火舞会一直持续到黎明,老嬷嬷带着侍女恭敬地向她行礼,拆下了两把头,将长长的头发依照蒙古已婚女子的样子盘了起来,又为她换上了一件华丽的蒙古袍子。再次站在镜子前,她已经是一个蒙古人的妻子,一片草原的女主人,大清公主的身份标志都被统统收藏到箱子里。
对着苍茫的草原,琪雅握着胸前的项链,晨光一丝丝跃入眼帘,泪眼下逐渐浮起越来越灿烂的笑容......
京城的梅府冷清、寂寞,庭院里积了很厚的落叶,在雨水中慢慢腐烂。屋子里的光线很暗,充溢着浓烈的酒气,梅沾斜靠在桌子上,凝视着手中的那盏半旧的梅花灯,身旁歪斜着几只酒坛。数天之后,梅沾突然不知所踪,龙吟多处打探也无果,便将梅茜接入戏班,饱受众人非议。无奈之下,龙吟便带着梅茜离开了京城,心中也满是恨意。
过了数日,待湘雪再打探消息时,却被告知梅沾已不知所踪,胤禵多次派人寻找也一无所获。功名利禄又如何,京城已无思念,他们以为梅沾定然已南下,去追寻琪雅的梦想。
父母不辞而别,湘雪再回去,只看到在门前驻立等待的桑鼎和那棵老槐树。桑鼎要带她回另一处的年府,湘雪却不愿,桑鼎便将她带到郊外散心,直到傍晚才将她送回雍亲王府。
骑了一天的马,虽有些疲惫,心里却分外轻松。納其夏将湘雪扶下马车,看到雍亲王府的匾额,湘雪眼中的神采忽地隐没了。她不愿回去,便轻抚着马儿对桑鼎道:“桑叔叔,我想回盛京。”
看到她眼中的犹豫和畏惧,桑鼎轻轻拍了拍湘雪的肩膀:“格格的家已经不在盛京了,便是要回去,也该再过些日子!”
望着桑鼎诚恳的眼神,湘雪信服地点点头,努力朝他笑了笑。见遇茶迎了出来,桑鼎便催促道:“格格快回去吧。”
湘雪依依不舍地与桑鼎道别,缓步迈入王府中,终是频频回首。她仿佛又成了初到年府的那个小女孩,带着对过去的满满依恋,满眼惶惑地躲闪着陌生的天地里目光。
湘雪坐在窗边看着納其夏和遇茶整理衣物,看到母亲到底还是将那些小孩子的衣服放进了嫁妆里,不觉流下泪来。夜里,她忽然又梦见了梅音投湖前的场景,梦见自己独自回到盛京,却怎么也找不到以前的家,连连呼喊“额娘”,却始终无人应答。梦里,她边走边哭,渐渐哭醒了,正巧合玫听到哭声,便提着灯走了进来。看到合玫,她却哭得更厉害了。
“姑姑,额娘不要我了!他们不会再回来了!额娘答应以后再来看我的......”
合玫将她拥入怀中,像哄小孩子那样细细安慰:“傻孩子,你额娘只是想家了,会再回来的……”
不知过了多久,湘雪在合玫怀中安静地睡着了,满脸泪痕,让合玫看着十分心疼。在她眼里,湘雪不是什么高贵的王府侧妃,只是一个离开、了母亲呵护的小女孩,对这个陌生的地方,内心充满了惶惑和恐惧。她又想起了许多年前,佟妃刚刚离去的时候,她的小胤禛也是这般无助,却藏起了所有的孤独......
王府的日子如同一潭死水,湘雪顾自过着平淡的生活,表面上不喜不悲。胤禛渐渐也常去倚云斋,湘雪却始终冰着脸,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长时间。偌大的王府里只有李氏的三个孩子,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两个男孩,一个七八岁,另一个只有四五岁。大一些的男孩有些瘦弱,很少出来玩耍,李氏也闭门教子,只和耿氏交好。
向佳泰请完安,她们各自散去,李氏和耿氏一起往李氏的院子走了,宋氏也朝自己的屋子走去。看到前院小花园里的百合相较昨日又开出了许多,湘雪便带着遇茶走了进去,忽听得几个婢女往园子里来,边走边说道:“前日里二格格吹了冷风,着凉了,闹了两夜。”
“难怪这两天都没见二格格来给福晋请安!这府里就属咱们院子里应该热闹些,偏偏侧福晋却又是安静的。看那位新进府的,也该比咱们二格格大不了几岁!”
“可不是!这么小的年纪就封了侧福晋,前几年进门的到现在还是‘格格’呢!”
“咱们主子熬了好些年岁才封了‘侧福晋’的名号,偏偏这位一来就栖高枝,一下子就和咱们的主子平起平坐了!可不以后要得宠了!”
“这倒不一定!你想这名号大多是皇上下旨封的,王爷不管喜欢不喜欢都要欢喜地领旨谢恩的。依我看,这原是因为她后面的年家。皇上用得着年家的叔伯兄弟,王爷恐怕也是用得到他们,所以才结了姻亲,未必是真心喜欢这位新的侧福晋呢!”
“照你的话说,这位侧福晋倒成了多宝格里的摆设,要被搁起来落灰不成?”
“不信咱们瞧着!我可听珊瑚那丫头说了,这位新的进门那晚,王爷却去了她们院子里。”
这边湘雪听了却依旧是一脸的淡然,遇茶却有些着急,想劝慰几句,看到湘雪竟无半分恼色,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园子另一边的宋氏刚开始听了还十分高兴,等听到湘雪进门那天晚上的事时却又有些恼了,正巧她的婢女来寻她,被她责骂了几句。
宋氏离开了园子,那些婢女看到宋氏一脸恼怒,立即会意,匆匆散去了。园子里顿时安静下来,一片清幽,湘雪便沿着弯曲的小径绕进百合花丛中,边走边赏,随手折下几支交给遇茶。遇茶见她难得这样的好兴致,也帮着选了几枝花。
花园虽小,却十分精巧,置身于此,湘雪也倍觉自在。她们正在花丛中说笑,湘雪俯身去折花,一抬起头便看到迎面而来的胤禛。她慌忙退后几步,眼中的笑意也瞬间消散,淡淡地问安,不等胤禛说话便转身匆匆离开了园子。遇茶收到胤禛的示意,便携了花匆匆跟上去。
湘雪刚踏进院子,便听到声音特别的“格格回来啦”,她以为是納其夏故意逗自己开心,便展露笑颜朝里走去。走到里间,却看到了她的鹦鹉乐乐,不由大吃一惊。納其夏正为乐乐添水、添食,见湘雪回来了,便上前伺候。乐乐又兴奋地嚷起来,湘雪心想它也懂得久别重逢,忽地笑了起来,走过去逗弄鹦鹉。
“格格早上刚出门,景风就从年大人家里将乐乐带回来了。”納其夏言外之意是提醒湘雪这一切是胤禛的细心安排,湘雪却只略微点点头,并未多问。当初她没有将乐乐带走,便也是希望典华夫妇在京城多留些时日,却想不到他们早已将乐乐送到了叔父府上。如今重又看到乐乐,想到父母的不辞而别,她越发觉得他们不会很快返回京城。
乐乐的到来给倚云斋清冷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生机。闲来无事,納其夏也总爱和乐乐逗趣,遇茶笑言納其夏是乐乐的结拜姐姐,納其夏自是不服,和遇茶闹了起来。湘雪听了,心里的悲戚却更加重了......
午后,湘雪对着瓶子里的白色百合看了半个时辰,又看了一会儿诗词,坐在绣架前绣了几针,只做了半个梅花便又搁下,独自坐到院中的花阴下出神。
第二日清晨醒来,只觉得花香扑鼻,湘雪便披了一件衣服,散着头发一路寻香。走到外间方看到桌上、架上、窗前、地上都摆放着百合,有种在花盆里的,有养在瓶里的,合着宿露,花越发清灵。看着满室的百合,笑意不觉映上脸,越来越浓,却又忽地淡了下去。门外胤禛脸上的笑容也随之隐没了下去,带着几许忧愁离开了倚云斋。
遇茶见了十分奇怪,納其夏却是知道湘雪的心思,但又不知道该怎样解说才能消除湘雪心头的种种防备,烦恼无比。
遇茶捧着一只匣子从倚云斋出来,一路走来,穿过小花园,往南面走去。走到胤禛院子的廊下,正巧云冰出来,便唤住了遇茶,拉她到院子里说话。
“遇茶,这是去哪?”
“云冰姐姐——”
“都好些日子没见着你了!手里拿的是什么?”云冰是胤禛屋里的婢女,比遇茶略大,湘雪未进府之前,二人一同在胤禛的院子里当值,都是合玫亲手调教出来的。
“南院侧福晋问我家主子要的花样,正要送过去!”遇茶打开匣子将花样递给云冰看,云冰见了自是爱不释手,两人便坐在廊下聊起来。
“这可真漂亮!又新鲜又好看,这个用在衣服上、这个用在领巾上……比寻常见到的真要好多了!是你家主子画的?”
“可不是我家侧福晋画的!难不成我们还能有这样的聪明,那也该去宫里给公主当师傅了!”
“还嫌自己不够聪明,不然怎么单单派了你去给新的侧福晋当差?想想以前咱们都在王爷屋里当差,现在你去了倚云斋,大家都难得见面了。你家主子得了宠,我们那里倒清冷了许多,难得见王爷回去。”
听云冰这般说,遇茶不由替湘雪委屈,朝四下里看了看,未见其他人,方悄声道:“姐姐倒是错怪了我家主子!王爷虽然常常在倚云斋里,但一直住在西边,我家主子却是住在东边的。”
“这是为何?”遇茶的话让云冰很意外。近日其他院的婢女、嬷嬷闲聊,都是围绕着新来的侧福晋,想来一定是得宠的。
“说了也难信!王爷和侧福晋是‘相敬如冰’,素日只有王冷着脸,偏偏我家主子也冷着脸,见着王爷了也没个笑脸。”
“你家主子岂不是位冰美人!听说她闺命中也含了个‘雪’字,竟是雪做的了!”云冰翻看着花样,有几幅牡丹、几幅幽兰,余下的都是寒梅、芙蓉。
“倒也不全是。她的确和府里别的主子不一样,‘腹有诗书气自华’来形容再不为过。闲来就读书、写字、作画,针黹也极好。平日里也常常和我们一起说说笑笑,但只要王爷来了,立即又变成冷的、冰的。”
“竟是这样,真让人看不明白!”
“既是这样了,更奇怪的是王爷却一点儿也不生气。昨儿个早上侧福晋在百合园里折花,遇见了王爷,今天清早王爷就派人搬了百合到我们院子里,满满放了一屋子。”
“可见得王爷还是极爱这位侧福晋,只等她暖和了,我们那里就要变成冰窖了!”
“姐姐这话可不能乱说,这是替我们侧福晋招骂名呢!小心王爷责罚!”
“看来她果真是个好主子,这么快就收住了你的心。”
“我也是实话实说,虽然王爷面前没人敢放肆,但咱们侯门宅院的流言蜚语最多了,岂不知人言可畏!”
“行了,我记下了!你快去忙吧,我也该回去了!只可惜你们那边我不能经常去,要不然就可以常常聊天了!”云冰将花样重新装好,递还给遇茶,两人一起站起身。
“不然我去求侧福晋,让她问王爷要你过去?”
“那是再好不过了!”
“不过,要等到冰释雪融才行。”二人又玩笑了一阵,方才散去。
倚云斋院子前面便是当日他们相聚一堂的那片梅林,梅林尽头是荷塘,院子里堆叠着一座玲珑的假山,流水潺潺而下,沿着水道蜿蜒到院中,汇成一处方塘。灵动的流水与典雅的建筑相互环抱,一步一景,精致却不失诗韵。方塘四周便是长廊、走道,围着典雅的木栏,栏边植有数棵大芭蕉,时值秋日,蕉叶色泽自是不及春夏绿的那般通透。塘中有几盆白莲,已过了时节,便也无从寻觅那些绰约风姿。每到晴朗的夜晚,便能倚栏望月,看月光照亮满塘水泽的涟漪。若是雨天,根根晶亮的雨线从天空垂下,在方塘上形成几重水晶般剔透的帘幕,激起朵朵晶莹剔透的水花。然而,无论风雨晦明,湘雪常常倚栏独坐,也不持书,只静静地发愣。
这日湘雪被納其夏拉到前院看戏,不曾料到胤禛会突然回府。他们在廊下相遇,胤禛清冷的脸上飞上几丝笑容,她却依旧一脸平静。“不看戏吗?”
“结局早就出来了,何必还要坐在那里等待。”
“年希尧来了。”
“你们还要把多少人拉进来?大哥没有二哥那样的聪明才智,难道你们还缺少一个教书先生?”
湘雪的话大大刺激了胤禛,他的语气虽重了,却依旧不为自己多加辩解:“你不明白!”
“对,我应该装作不明白,稀里糊涂地活着,不知道自己只是微不足道的棋子,可以被替代。”历经太子、琪雅事件,又听到府中的闲言碎语,湘雪渐渐怀疑胤禛娶自己也是利益使然。
“你是无可替代的。”胤禛的情感依旧浅淡,眼神愈加浓烈,仿佛要融化湘雪身上的那层坚冰。从前的那个她不见了,在胤禛眼里,如今的湘雪恍若一潭深水,表面寂静无波,让他揣摩不到她的真实情感。
“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更合适的。阿玛要报答祖父的救命之恩,我只是替阿玛偿还年家的这份恩情。”她明明看到了他眼中的诚挚,还是自欺欺人,拼命辩解,掩饰自己的向往,不让自己沦陷入他的情感中。
“你的阿玛和额娘已经到盛京了。”得到这样的答案,胤禛眼中的光芒瞬间熄灭,冰冷如旧。
“他们一直想回盛京。”
话罢,湘雪立即离去。一直以来她都身不由己,被动地接受别人选好的路胆战心惊地走下去,猜不到下一个岔路口又会遇到怎样的人、事。从杭州到盛京,她顺从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到了京城,因年家成了胤禛的佐领,她便被视为一件邀宠的礼物,活在他们精心策划的阴谋里。如果说年羹尧对她的怜爱是纯澈的,现在的她应该是快乐的。在家族、仕途面前,她的份量总是单薄的,年羹尧终究作出了应该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