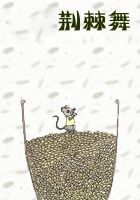自从和秦强一起去清月庵见过善淑后,一连几天,黎敏再也没见到过善淑了,无论早晨起得怎样早,无论在山冈逗留得怎样晚,无论怎样频繁地去峡谷挑水,还是借故去洗脸,善淑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师姐,这几天怎么老是你一个人浇菜?师妹呢?”终于有一天,师姐在山上浇菜,黎敏走过去问。
师姐指了指山冈那边说:“师妹一早就往那边跑,除了做佛课,她几乎都在那里,你去吧,师妹现正在那边呢?”
黎敏想去,但又不好意思马上走,他将水桶提到师姐旁边,无话找话地说:“师姐,这菜长势怎么这样好?”
师姐仿佛理解黎敏的心情,笑了说:“不用你帮忙,你快去找师妹吧。
庵堂围墙边有条小路,顺着那里走,一会儿就到了。”
自从听说善淑在山冈那边,黎敏的心早已飞到那里去了,只是碍着师姐在一边,他不好意思立刻就走罢了。此刻见师姐那么说,于是,黎敏顺水推舟地说:“那我就走了,师姐。”
“去吧。”师姐善良地笑着点了点头。
林中小鸟在叽叽喳喳地叫着,跳着,周围神秘、沉寂,散发出一股潮湿好闻的气息,这是林中特有的泥土的清香。黎敏风急火燎地走着,恨不得顷刻就到海边。
“哗———哗!哗啦啦!”声声浪涛,在这寂静的林间显得格外刺耳。黎敏放眼望去,才知已到林子尽头,呈现在眼前的是别有一番风情,前面压根儿不是大海,而是一片金色的沙滩。
这里真静,这里真美,就像世外桃源,除了这条被柴草覆盖的令人难以发觉的小路,三面都是长满荆棘与灌木的陡壁。
善淑果真就在那里。
黎敏看到她时,她正面朝大海,半蹲着身子在沙滩上划着什么。海浪泛着白沫飘过来,几乎漫到了她蹲着的地方。
在这世外桃源般的意境里,在这泛着碎银般浪花的海边,一位美丽的女子在黎明时分,挺着修长的身材,蹲在黄金般的沙滩上,面对大海默默地沉思……啊,这是一幅何等壮丽的画面!一种何等美妙的意境!
潮水在涨,泛起的浪花几乎就要漫过了她的脚踝,善淑终于站了起来。
她穿着一件素色的碎花外衣,蓝色的裤子,白色运动鞋,手里握着一本书,贴着海浪缓缓地向前走去。
大海你来自何方…
你又去那里流浪…
有谁知道你寂寞…
有谁知道你惆怅…
随着海风,在阵阵哗哗的浪涛声中传来善淑那略带忧伤的歌声,黎敏的心神又不禁为之一振。
善淑一边走着,一边唱着,时而戏耍着漫过来的海水,时而弯腰捡着裸露在沙滩上的美丽的卵石与贝壳,在她身后的沙滩上留下了一连串浅浅的脚印。
浪花溅湿我衣裳…
洗去我心中哀伤…
海浪无垠的大海…
闪耀着迷人的希望…
到沙滩尽头,善淑蹑着脚尖拔下陡坡上的一根芦苇,随着歌声的节奏挥舞着,又轻快地踱回身来。
“啊,她真像婉君。那次在学校的海滩上,婉君也穿着白色运动鞋,也左手握着书,右手挥舞着草干,一边走着,一边唱歌。”黎敏不能自己,忘情地瞅望着善淑,不由自主地朝前走去。一脚踏空,黎敏被跌倒在地。
几块小石子扑落落地滚下坡去,落在善淑的跟前,善淑吃惊地抬起头来,霎时涨红了脸。
“对不起,我……”黎敏讪讪地爬起身来。
善淑什么也没说,只是胆怯而不安地望了黎敏一眼,抬腿就走。
“别,别走。”黎敏猛地想起临来时暗暗下定的决心,鼓起勇气拦住善淑说:“我是找你来的。你在这里,是师姐告诉我的。也许你会问,我找你有什么事。你大概还记得师姐叫你帮助我学习这件事吧?师姐也许是在开玩笑,但不怕你笑话,我确实需要人辅导,因为我想报考军校。”
“这怎么可能呢?我是尼姑。”忽然,沉默着的善淑抬起头来,自卑地说了一句。与聪福之间的那场风波仿佛是一贴清醒剂,使她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处境与身份,不再像以往那么任性。
“请不要这么想,在这孤岛上只有你们和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一家人。我虽是军人,但你我接触是为了学习,是没有什么不好的。”见善淑消失了戒备,终于说话了,黎敏紧张的心这才平静下来。
“以前我好像没见过你?你刚调来的?”善淑已不再惊慌,轻声问。
“是的,我刚从训练团分配到这里,上次是第一次随战友去你们庵里玩,想不到会认识你。听师姐说你上过大学?”
善淑点了点头。
“那你为什么出家?”
善淑忽然变貌失色,打断他的话说:“时间已不早,我该回去了。”
黎敏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这才知道黎明早已过去。海岛上的太阳来得早,虽是冬天,虽是早晨,气温却很高。
“下次欢迎你去我们营房玩。”黎敏望着已走出很远的善淑,挥舞着手说。
“谢谢你!”善淑回过头来,留恋地望了他一眼,消失在灌木丛中。
黎敏没马上离去,他发现平整光滑的沙滩上,清晰地留着一道道几何题的求证与分解,一旁还流利地写着英语。
“如果在学习上需要什么帮助的话,以后你可来庵里找我师妹,她在大学时可是高材生。”想到前几天师姐说的话,黎敏的心不禁突突地跳了起来,脑际里交错地闪现着那几个字:
大学生,尼姑。
尼姑,大学生。
这天中午,黎敏和善淑又在峡谷不约而同地碰面了,那时两人都挑着水桶。
“真巧,又碰到你了。”黎敏笑着说。
善淑也很高兴,回眸朝黎敏莞尔一笑,无话找话地说:“你也来挑水呀。”
“对,跟你一样。”黎敏放下水桶,见善淑汲满水要往上跳,忙过去拦住她说:“来,我帮你挑。”
“行。”善淑没有拒绝,很愉快地答应道。
黎敏很快就将水挑了上去,回到峡谷时,善淑也将他水桶的水汲满了。
“黎敏,今晚你有空吗?如有空,去一下海边沙滩好吗?”
“干啥?”
“现在不告诉你。”善淑调皮地笑了一下,蹬蹬地奔上台阶,回过头来说:
“吃过晚饭后,我在那儿等你。”
“不……”黎敏摇了摇头。
“你不去?”
“不是,只是晚上不太好,明天上午行吗?”毕竟自己是当兵的,白天与善淑在一起探讨学习上的事,也许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晚上在一起,性质就会不一样,一旦让部队知道,轻则挨批,重则受处分,黎敏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善淑沉思了一下,说:“不了,那就现在告诉你好了,你不是说想报考军校吗?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在学习上也许我真的可以帮你一些忙。”
霎时,沙滩上的数学题,沙滩上的英语以及师姐说的话,又像电影一样清晰而逼真地浮现在黎敏的脑海里。
“好极了!”黎敏兴奋得不禁击掌出声。
善淑叮咛道:“记住,明天早晨,我在海滩上等你。”
“好的,我知道了。”
“那我就走了。”善淑又对黎敏妩媚地一笑,挑起了水桶。
“不,你先别走,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你的名字难道就叫善淑?”
善淑犹豫了一下,说:“善淑是我的法名。”
“那你的原名呢?”
“原名叫燕子,可是燕子已不存在了,她已死了。”善淑极其生硬地说着,声音里包含着万般的凄凉,悲伤与辛酸。
“善淑,有些事我不知该不该问?如果问错了,你别难过。”
善淑的头渐渐地低了下去。
“我知道你要问的是什么,但我求求你别问,现在也好,以后也好,人都是以各种方式生活着的,各有各的隐私,当然包括我们出家人。另外,你也该明白,如果没有不幸,没有痛苦,庵堂寺院是不会有尼姑和尚的。”善淑一说完,就挑着水桶急急地走了,留下黎敏一个人默默地怔愣着。
一枝淡淡的蜡烛,映照着一个整洁朴素的房间,善淑凑在亮光下神情专注地边翻着书本,边在笔记本上迅速地记录着什么。
生活的激流将她从洋溢着青春热情的大学校园推落到这宁静孤寂的庵堂,她的心已破碎,她对知识的追求已绝望。偶尔空闲的时候掀翻一些书籍,并不在阅读什么,她只是打发时间。
从佛顶山来到孤岛后,除了想聪福,善淑的生活是平静的。但自从黎敏来了小岛,尤其听了师姐让她帮助黎敏的玩笑,她宁静的生活才开始出现波澜,她想了许多,想过去的那些生活,想自己的那些遭遇,那些不幸,那些创伤。对师姐那天说的话,她有点怨恨,有点不快,因为她意想不到,也就接受不了。但师姐的话,她记在了心里。
往日一到那个属于她的神秘的海滩,她的破碎的心就会复原,她就会重温到那些失落的梦,快乐地自由自在地做她想做的一切。可是,从那以后,她再也不那么欢乐了,她常常会呆呆地一动不动地望着小路出神。她失落了什么?她在想什么?抑或在等什么?没有一种清晰的概念。直到黎敏出现在海滩,善淑在震颤中才知道自己烦躁的原因,自己失落的是什么。以前她不敢承认,也不敢想像,但在那一会儿她再也否认不了自己是在等黎敏。
从海边回来后,整整一个上午,善淑坐在窗前没有做过片刻的事。她不想欺骗自己她愿意帮助黎敏。虽然离开学校已久,但她还是有能力有把握辅导好黎敏。
人往往是这样,一旦决定自己想做的事,就会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时机。
一个人如果对某个人产生兴趣,那么就会每时每刻地注意他,千方百计地借故接近他,与他在一起。为了见到黎敏,明知道缸里的水满满的,善淑还是挑着水桶去峡谷。到了那里,善淑完全可以马上汲水,但磨磨蹭蹭地迟疑着,就是没有动手。
黎敏没有让她失望,果真与她想像的那样挑着水桶来了,那时善淑是多么高兴,多么紧张。想到自己要说的话,善淑的心就不由自主地怦怦乱跳。如果没有黎敏的热情,善淑是怎么也没有勇气敢主动向黎敏说这些的。
蜡烛快燃尽了,火焰一闪一闪地跳着。终于,外边一阵风吹来,扑地一声熄灭了。房间里一片漆黑,只有供奉在观世音菩萨前的香火,在黑暗中一闪一闪地晃动着。
善淑动了一下,但一会儿又默默地一动不动了,她坐在窗前,出神地遥望着星空,久久没有起来。
天还没亮,黎敏就起了床。
星星还在闪眨着光芒,鸟儿还在沉睡,只有海浪在单调地发出哗哗的声响。虽然知道善淑不可能会起得那么早,但黎敏还是满怀希望地急急地赶去。
到了沙滩,黎敏意外地望见在朦胧的星光下,善淑早已等着他了。
“你来得真早。”
“你不也一样。”
黎敏仿佛想到了什么,不禁会心地笑了。
“黎敏,你理课成绩真的不好?”善淑问。
黎敏一时明白不了善淑问这话的意思,只是诧异地望着她没有吱声。
“其实我的成绩也不见得好,也许并不能给你有多少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