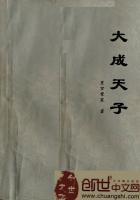陷入漫长的转弯、盘旋
生活永远是一个矛盾的智者
分不清远和近
大山依然沉默,千万年如斯
灵动的是那些梯田、野兽
昆虫和飞鸟,在雷电和风雨中
在板屋下不停出没
2006.9
云雾腾起的山谷
昨夜里什么时候下过一场雨?
地上全是湿的。那块凸起的石头上
几个被时光雕刻出的风臼,成为一个个
倒映出小片天空的水潭
我站在石头上,一只手
扶住旁边的松树,呀
许多细小的水珠
就在这时铺天盖地落下
但必须站在此地,才能更好地
俯瞰到下面的山谷
此时,山谷已经袅起了炊烟
它们一缕一缕,随晨风飘散开去
不久,从山谷那头,白雾
突然升起,开始像一层薄纱
缓缓拂过,连绵的黑瓦
和一片片反光的水田。后来
雾,越来越浓,越来越大
谷底已经完全被雾笼罩
那些低处的山头,
变成一个个海中的孤岛
很快,连岛屿也被淹没。
而浓雾,还在顺着梯田往上攀爬
感觉有风,正从山谷往上吹送
好像要将我,带离这庸俗的人间
什么时候浓雾已经裹上我的裤腿
又裹住了我的脸?凉凉的、湿湿的
只有眼前三米以内的地方,我是看见的
但我一点也不惊恐
在我身后更高处的山头上,此刻肯定有人
看浓雾怎样一点一点将我吞噬
它们刚将我带到天上
转眼又将我送回到烦恼的人间
2006.9
永红石桥
小时候,我喜欢去永红石桥
喜欢伏在它两边的青石栏上
俯身去看清澈的河水
水中也有石头,但没有
桥上的规则,也没有桥上的安分
他们似乎排着队,要赶往上游
河道并不宽,也不窄
河堤两边是一大片平整的稻田
是屋,是树,是连绵无语的青山
从任一头踏上永红石桥
都必须经过一个向上的斜坡
必须小心,细沙的溜滑
九岁,深秋在夕阳下回家
我曾经在北边的斜坡,滑倒
幼小肩上的红薯滚了一地
可我一点也不怨恨,因为冬天下雪
以后,这面斜坡
就成了我们的溜冰场
那时桥面上,挤满了
我们这些躲避炉火的孩子
一个个争先恐后,要从桥的两头滑下去
有一次是我因为太逞强,滑的太急
一不小心冲进了河里。站在河边
嘴唇冻得铁青的我在寒风中不敢回家
水中也有一座桥
但那是在夏天
有月亮的夜晚,桥南桥北的乡亲
陆陆续续坐到桥东桥西的栏杆上
俯瞰到下面的水底
也有一座桥在不停晃荡
那时摇晃的,还有桥面上的风
母亲清亮的山歌,桥下婶婶们的身子
老人的蒲扇,在月光下不停挥动
2007年夏,长沙树木岭新星小区
黄昏
太阳刚刚落山,薄暮叹息着垂下来
龙溪顿时失去了,一河的粼光
一天的捕捞,接近尾声
他开始清理鱼箕
那些深附箕缝的水草,废物
它们可能来自下游的某处水底
就要被扔在
上游的某处河滩
十月乡村的傍晚
两岸炊烟总是升起的太快
他有点失望地望着半满的鱼篓
就要朝下游赶去
要拐过十几个小弯
才能绕过那片宽阔的水田
穿过火车桥
赶往日夜轰鸣的小镇
他一个人走在狭长的路上
闹鬼的路上
他走的越来越快
天黑的越来越急
2007年夏,长沙树木岭新星小区
坐在屋前的人有点悲伤
门面又杂草丛生
母亲已不在那里
父亲坐在屋内
还是出了远门
他现在越来越寡言
从前的风已经刮过去了
雨早已停住
雪不再击打
今年新翻的瓦面
我站在草丛里
发现自己,突然变矮
母亲是从堂屋的阴影里
走出去的
墙上坐着木雕菩萨
一晃
十年
2008年早春的一个上午,社学里
凤凰一夜
楼下就是沱江
有很多人在夜色里
经过跳岩,北门城楼的灯光
在我的对面,亮的晃眼
站在水木酒吧顶楼
的露台上,风有点冷
但背后的房间一样冷
我不如俯瞰沱江
酒吧一直喧闹
有人在艳遇后迷醉
也有人在落寞中
趁着夜色离开
游船静泊
水车不分日夜旋转
那些吊脚、飞檐、门匾、木栏
在烟雨中慢慢陈旧
2008年3月30日深夜,写于水木酒吧顶楼客栈303房
小池塘
夕阳滑向山脊。透过
长堤上松柏树的间隙
半亩方塘:有些血红
有些阴暗
草鱼,这正午探出水面的张望者
石头上跳跃的土蛤蟆
渐渐安静,躲在黑处。像
提防一场突然的侵袭
垂直的壁沿上
我背手,踱步。偶尔蹲下
俯瞰。发现另一个我
正从水底仰看天幕。
岸边,塘水浇过菜地
曾经一棵高大的椿树
被父亲伐倒。三节,拧断的巨藕
浸泡在水里
数不清的小田螺,粘附在上面
三座,两栖动物的条形孤岛
随手捡起一个土块,扔去
扑嗵!有胆小的往凹面跳水
旋晕的我,扭曲着散开、消失
站起。身后
夕阳已悄悄滑落山谷
2008年夏,长沙树木岭新星小区
一场从伯父头顶落下来的雪
窗外的夜很静,但开始有雪在落下
明亮的沙沙声从远山
一直漫过灰暗的屋顶
门前干田中的,两座窑堆
已盖上一张甚白的圆桌布
没有回家的伯父,坐在窗前大凳上
突然从和我父亲的谈话中
停了下来,扭头去看窗外
正在发生的事情。眼神霎时一暗
屋子里只听见,炕桌正中的煤火上
沙罐子里甜酒的咕嘟声
我看到过,伯父的这种变化
每次来访,他只要
经过橘园北边的围墙,头总会
稍稍右侧,看着田中
亲手烧制的砖窑,停顿下来
但离家出走的妻子,和一点也不
理解父亲的,三个儿女,慢慢把他
盖建新居的愿望——压了下来
像眼前的这一场大雪
落满田畴。作死地重压
资园院子中正在摇晃的老木房
掩埋了,从三尖和禾青
回家的路。世界上所有的缝隙
孤零零的树尖,整个发出一阵
空寂、死亡的绝望
2009年12月8日半夜惊醒,写于长沙新星小区
大雪夜,围着炉火的一家
沙罐搁在煤火上,里面的甜酒
正在冒出急促的咕嘟咕嘟声
母亲突然放下,手中的木鞋夹
扭身去从门后——暗红色的筷筒中
抽出两根筷子,伸手去搅拌
沙罐里越来越满的泡沫
不时溢出的水滴,溅起一小撮
黄色的火苗。有扑哧的声音
还有淬起的灰,很快升起,又落到
油腻的杉树桌面。撕咬着
甘蔗的妹妹,一直很小心,生怕割破了
手指和嘴角。头一偏,躲过煤灰的呛鼻
罐中的水汽,还在令人生厌地
袅起。让哥哥的寒假作业簿
超出桌面的部分,有些湿卷。
只在年终,这个寄居外婆家的
龙坪小学的学生,他才回来
面对陌生的父亲,有一丁点儿畏惧。
现在,我的父亲,一个还有点帅的
壮年男人,正在尽可能靠近
楼枕上吊下来的灯,不时翻动
手中一九八六年版的《红楼梦》
母亲从橱柜中——端出
瓷碗碰撞的脆响,凳脚
擦动地面的尖叫
将我从凝神窗外的降雪中
扳过身来。看见
这个年轻力壮的矮农妇
她正熟练地:一只手用毛巾
包住沙罐炙热的弧柄
一只手用筷子搅动底部的酒糟
看着滚烫的酒水,冲卷起
碗底的鲜鸡蛋,香味顿时腾满了
整间屋子
2009年12月8日半夜惊醒,写于长沙新星小区。
其时,从老家来看我的妻子和女儿,睡的正甜。
他们一起来到了河边
走在最前面的是扁谷子
随后是马记,再后面
是四亚禾和天平仔几个人
他们沿着稻田中的水渠
走了过来。七月,正午
他们赤脚踩在发光的青石板上
似乎一点也没有感到滚烫
我早已来到河边。正蹲在
浅水湾的一块巨石上
不时用左手舀上清水
洒在脚下的石头上
右手伸出一根细长的竹枝
眺望着平缓的河面
他们突然一齐站在河堤上
叫我。我回头,要仰视
才能看见他们黝黑的脸庞
怎么不叫上我呢?有人问
猪肠子一样弯曲的老街
一个少年放下饭碗
持竿去往河边的消息
传的好快
我用食指轻抵嘴唇
又指向麦杆浮荡的河心
他们立刻变得安静。
一个个蹲到
我下游不远处的草滩
齐刷刷伸出了手中的竹竿
时光开始进入下午
但太阳,依旧很炙热
空旷的河堤上,两边都只有
偶尔吹过的微风
在打碗碗花狗尾巴等杂草的簇拥下
间或闻到一点牛屎的气味
没有一个女孩敢在夜晚
独自去往幽暗的河边
但下午三点,显然可以
当小兰提着篮子
出现在对面的石头上
我们一齐试了试手中的钓竿
想突然提起一尾蹦跳的惊喜
让小兰的呼叫
打破这个下午的沉寂
但小兰的呼叫
一直没有打破这个下午的沉寂
因为河水的流动,我们的脸
无一例外地偏向了下游
2010.9.2凌晨1点写于师大上游村
雨一直下到天亮
雨下了一整夜,天已经亮了
女人沉迷于,古老的催眠
阳台蓬顶,狂乱地抖颤。像一面
乡村的牛皮鼓,埋怨塑料的桶箱
植物很疯狂:迪士高,或者拉丁舞
平整的地面,砸落无数的鼓槌
金属防护窗,偶尔被击中
短暂的吟哦。看见下面的福特
玻璃的天窗顶,有着很好的弧线
适于雨水细微的下滑
有人突然从对面出门
垂直的雨水中,一把黑伞在移动
腰间的钥匙
响着清脆的咣当声
2010.12.3,清晨
墙上的一幅画
我坐在医院过道的铁床上
望着对面墙上的一幅画
有一条小溪,从下面的木框
往上流入一个巨大的湖泊
小溪流过的滩涂,覆满白雪
溪水很蓝,湖面也很蓝。在湖边
有一个肩上扛着暮色的人
正呆望着眼前的湖面
一些渔船,已经亮起了灯火
另一艘船,搁弃在岸边的乱石上
浓重的阴云下面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物
这不是一个废弃的码头
那个人也许只是错过了
最后一班渡船,来不及
回到另一个湖边的小镇
他一定是一个
经常这样晚回家的人。他的背后
会有一个临时收留他的村庄
已经退出画框以外
再往后退,就会退到
我此刻站立的医院过道上
过道上有一张床。床头写着:
加11床,易建东,男,38岁,耳鼻喉患者。
他也是一个,从另一艘正在行驶的船上
掉下来的人。此刻,他正冷冷地
看着画面,似乎要等着湖边的那个人
什么时候突然转过身来
2012.4.21下午4:10分写于湘雅附三医院外科楼13层24
病室22床的窗台上
一个伏在窗台上喝粥、读诗的男人
一个两天前刚被摘除了扁桃体的人
一个同时被施行鼻中隔矫正术和鼻窦开放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