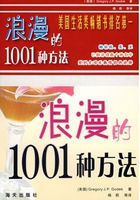明朝张岱谈到他老屋倾圮后,建了一间大书屋名为“梅花书屋”,前后有空地,砌石台,种牡丹、梅、竹、秋海棠……现代人要拥有那样一片地就得远离人文荟萃的都市,也就是远离剧院、博物馆、音乐厅、图书馆、名园、名建筑……远离艺术与文明是何等的一种损失,内心宁静,梧高三丈翠樾千重,就在方寸之间。
古时在华山筑石室修道的人,幻想炼得金丹就可以驾着白鹤升腾上天,骑在青凤上成仙去!事实证明没有长生不老的妙方,但不论修道或参禅,到了一定时辰,悟彻人的生存只是幻影虚相,人的生存空间逃不出这座自营自筑的迷宫,进而遁入空境,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对禅学大师来说,万古长空,只不过一夕风月。
牛郎织女星隔银河相望,一年一度鹊桥会,但据天文学家估计,死星与太阳相会更是长远,要隔二千六百万年才能相会一次,这样的相会是玉石俱毁悲剧性的,会引起众多流星在空中飞闯,形成地球的灾难。
流星的灰飞烟灭也是另一种空境,鲍照操笔写《芜城赋》何尝不是空境,那古代帝王特为猎鸟设的“弋林”,为垂钓设的“钓渚”,歌亭舞榭,玉池里的碧树,吴蔡齐秦的音乐都像焚一炷香似烟消火灭,洛阳妃姬,南国佳丽,都是蕙心纨质,玉貌绛唇,现在已埋葬在土石堆里。
汉朝长安的金马门俗称“金闺”,据说有才学的名士都在这儿等候求见帝王。而汉朝宫中设有研讨学术典籍的地方称为“兰台”,当年金闺的诸贤,兰台的精英也已销声匿迹。
就是诗仙李白仍然有过衔玉求售的心情,他说他流落荆州,十五岁爱上剑术,三十岁学会作文章,身长虽不达七尺,依然有万丈雄心……他写了洋洋洒洒《与韩荆州书》,希望受到器重,但属于龙蟠凤仪之士的李白终究以诗酒、以浪迹天涯为终,繁华世俗毕竟只是浮生一梦。
王子乔,也即周灵王太子,喜爱吹笙,经常游于伊洛之间,他人以“闻凤吹于洛浦”形容他落拓高远的胸怀,现代人也许不拔俗出尘,效法古代颜阖、郭子綦守陋巷苴布衣,对世间繁华视如云烟,心如槁木死灰的隐士,不过面对高霞明月,青松白云,一样能洗净心灵的尘埃,大自然是造物主为我们摆设华美的精神筵席。
我搭TGV火车从巴黎到苏黎世途中,窗外千峰万壑,奇峭壮丽,在冷雾蒙蒙中,五代的山水画家董源正运用他披麻皴和点子皴的妙笔,画下景物灿然,水墨渲染的山水胜景。
不是经常可以欣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高境,秋桂春萝一样是一种浪漫,衣兰衣,眠蕙帐,卷衣撩袖会有一缕芳香溢了出来也相当古典。凡尔赛有一条街种了两排山茶花,法国人将山茶种在高高的木盒子里,这一带有好几家路边咖啡座,我经常点一杯热牛奶,一份洋菇煎蛋,坐在路边咖啡座,欣赏山茶花,享用我的午餐。
秋天将逝,冬天还未来临前的一抹阳光怀着无比的固执,大地逐渐荒芜,草色已枯黄,曾经盛极一时盘旋着艳色光轮的繁花都在心力交瘁中逐渐凋谢,再迈前一步就是悲壮的死亡,而那抹阳光却永不放弃!有一种声音:风声能吹进最小的岩石罅缝中,嘎札嘎札形成乐音,风又将晚霞映照的海浪,吹成波涛起伏的琥珀色……
今年早来的雁已在蕾梦湖畔散布着焦灼的声音,几乎如鹤唳似的哀鸣……一只雏鸟也是造物主的一份礼物,那细胞,那卵衣都用蛋壳密封起来,是来自母体生命的一部分,就等待创造另一个独立的生命。
早春山仍在沉睡中,在软绵绵茸毛似的积雪覆盖下,大山也有甜酣的梦,只有几朵灰云忧郁地飘过乡关的界限……
就这么开始,我仔细审视世间的万事万物,我在等待大自然结束缄默,以美的语言,以智慧的语言向我说话。
清秋四僧:八大,石涛,髡残和弘仁,他们都是明朝金枝玉叶老遗民,内心充满了身世漂泊之感,抑郁、失落,反映在艺术上是苍凉悲壮的意境,泪痕与墨痕交织,譬如八大山人的《秋林亭子图》《林谷山村图》都是心境上的旧江山。
石涛老人又称苦瓜和尚,他也像徐霞客,云游四方,但他不写苦瓜和尚游记,他和髡残都擅长描绘内心的山水,想象力丰富不受拘羁,笔墨纵横,意境飘洒。
八大、石涛、髡残、弘仁终于悟透人世飘零如梦,披上袈裟,遁入空门,却孜孜不倦,经营艺术这片天地。
空间不是空境,反而是艺术上最辉煌时期。
(2003年11月)
衣上酒痕诗里字
古玩铺
那也像狄更斯(CharlesDickens)笔下的《古玩铺》,只是读者不要期待有一出扣人心弦的故事即将启幕……
阳光折射在一片玻璃窗上,古玩铺的老人就藏身在阴影的角落里,但有几朵彩光落在那儿,在他衣上、书桌上、老旧窗幔的边缘闪闪发光……
那些老旧的版本躺在灰尘中,路易时代一把翻新的椅子标出惊人的价格;一位早期法国演员留下一顶旧帽子,上头还挂着铃铛;两只大驴耳似的御寒帽,是来自布列塔尼早期妇女的手艺;一个旧木偶似乎还流连在戏台子上,一颦一笑,依然神韵十足……
那一诺千金的旧书笺,依然留在人间,执笔的人却早将秘密带进坟墓了,那旧木琴、旧镜框、珠宝玉石都不知源自何方,没有典故可以查证。
我喜爱在古玩铺流连,是怀着哀感的心情,想想自己有一天也像一堆老旧的古玩,被这纷纷扰扰的尘世所遗忘,那么洒脱,又那么绝情。这时我就会想起弗朗兹·卡夫卡,他是黑夜的一位更夫,当人类蜷卧在自己屋檐下、自己房间、自己床上安睡时,他是清醒的……
这位更夫看到他们枕着胳臂,挤在荒凉的野地,在露天下寒冻彻骨……这位曾获法学博士的奥地利作家,后因肺疾在疗养院疗养,他写作不断,一九二四年在维也纳基尔灵逝世,年仅四十一岁。临终前写下遗嘱要他至友布罗德,将他所有作品烧焚,关于他已发表的作品不要再版,幸好布罗德没依照他的遗愿,我们今天才能读到这些动人的文字。
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犹太家庭,他的作品几乎都是跳跃过时空的寓言,那种民族离散的失落感,经常流露在字里行间,对卡夫卡来说,人生不过是一场宿命的流亡,他是擅长叙述低调的高手。
“凡尔赛住着一些旧贵族的后代,他们喜欢逛古玩铺,每回我卖出一件古物,就像送走一位老朋友,它们年纪都比我大。在法国丧葬费无比昂贵,那墓碑,是有时间性的,到了期限,后代子孙,付不起钱,墓志铭与碑石就不存在了。人的形骸比古物短暂,我玩赏于古玩间,忘了自己的年岁,仿佛自己也可以跨越春秋……”古玩铺的老人说,他原是退休的语言老师,经营古玩铺纯粹是消磨时间,淡然忘我,像中国人进入“庄周化蝶”的境界。
但我依然沉醉在卡夫卡的冥想中,他悲悯地看到人类枕着胳臂,挤在荒凉的野地,在露天下寒冻彻骨……
也许那种星垂平野、月涌大江的壮阔襟怀已随流逝的年月消失。
我徘徊在古玩铺里,如走在古茂苍苍、大荒沉沉的土地上,像蔡文姬流落在乌珠部落间,面对婆罗沙尘一般的感受。
围 炉
当寒冬凡尔赛皇宫的雕像忧郁地裹在塑胶的纸包里,寂寞地站在旧日雉堞的边缘地带,我来到布列塔尼,海风飘着慈母眼泪的咸味,游子几番理却没有归意,只是将自己放逐得更远了……
黎明,在寂静中我听到鸟歌,探头看屋檐下那窝蛋,每一个封闭的蛋壳都会孵出一个独立的生命。不要对初生的幼鸟说:它们将跨足一个寒冷、饥饿、危机重重监牢似的世界……
虽然所有树还继续冬天的长梦,
冰冻的土地离春耕时节尚远,
茫茫的原野满天飞絮的霜花传递依旧是北风的讯息……
夜晚我们围在炉边,浅酌轻饮布列塔尼的红酒,尝各类法国的乳酪,有一种乳酪以核桃为佐料,入口溢出核桃香,特别可口……
在这样的夜晚,似乎就是美国作家哈阿顿所说丹麦人称为“白夜”的夜晚,夏天多么短暂,太阳远远地离开地平线,天空闪烁神秘的光,月光照亮了巉岩峭壁,月光的波纹在海面上流动……
“我们不要像丹麦人在白夜里怀着时间的压迫感,应该悠游在安徒生童话的三度空间里,想想那些鹳鸟会说埃及话,仙子们披着月光和雾气织成的披风跳舞……”佛洛方丝首先开了腔。
“就像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特洛伊战争中的大将尤利西斯回家途中森林的一夜,他穿过一片灯心草铺地的岸边,长年的争战、漂泊、痛苦忧伤,使尤利西斯的体力已不如从前,他没法在露天过夜,想起旅途中刺骨的寒风,寒天霜冻,他心力交瘁,那铺满了厚厚干燥落叶的床,飘着叶的馨香,四周密封似的灌木林挡住呼啸的北风,他睡在堆起落叶的床上,竟是温暖舒适的。到一个遥远的国度去漂泊,是年轻孩子的梦,历经艰辛,品尝人生羁泊之苦的中年人,又梦想回到最初的起点站———家园。”伊莲说。
一直沉默寡言的鹂,独自撩拨炭火,她的眼盈盈闪着泪光,她的双颊在炭火映照下如盛夏的玫瑰花……
“我的预感一定是在那次音乐会前夕,庄严的宫殿,阴翳的回廊飘过晚星的芒彩,皱褶树的阴影在风中浮动,像老烫不平的衣衫……塞纳河突然成了静止的画面,船只不再泊岸或漂流……纵然那只是一个爱情的梦,也让我回忆起最初发生的情节,最初的梦痕,天鹅滑水似的惊艳,幻象实影交织滥觞,内心半明不灭的灯盏……”鹂呢喃自语,一滴滴晶莹的泪滴进盛满红酒的水晶杯里,发出像玉碎似的微响……
回到房中,我一再思索鹂的独白,爱情是人间奥妙的谜题,是缪塞《五月之夜》里的绝句,法国一出名为《世纪孩子》的戏写的就是缪塞和小说家乔治桑的一段情,这位电影编剧一定对缪塞的作品经过一番研究,因为缪塞一八三六年写了自传小说《一位世纪孩子的忏悔》。
缪塞终究失去乔治桑,但因为经历这段爱情,他的诗作更为丰富,他的诗是不朽的,像他所描写威尼斯圣马可教堂比阿萨大广场耸立十五世纪的狮像,青铜脚趾伸展在地平线上……
福 地
我不知我们这些异乡人,是否将来就埋葬在异域的尘土中,没有一块碑,铭用自己母国的文字标明自己的名字。当我站在帝王陵墓前,或伦敦西敏寺,看到那些碑石将死者光荣的事迹引证给世人,是多么令人自豪的事,纵然埋在尘土里只是一堆干瘪枯槁的骨骸。
奥地利作家斯·茨威格一九二八年曾经到俄国旅行,他见到托尔斯泰的墓,认为是世间最美的坟墓不是拿破仑大理石的陵墓与魏玛公侯并列歌德的墓,也不是西敏寺莎士比亚的石棺……
茨威格沿着羊肠小道,穿过树林间的空地和灌木林,托尔斯泰的孙女告诉他:树荫下一堆长方形的土堆就是祖父的墓。茨威格黯然震惊,秋风萧飒,那些大树挺拔在风中都是托尔斯泰手栽的。据俄国古老年代村妇的传说,亲手植树的地方会变成福地,因而托尔斯泰就决定埋骨在他手植的树下,他的墓正如拉丁文所说“没有十字架和墓碑”。
春雪会覆盖这堆黄土,严寒季节一过,野花就缤纷了这块土地。
我也曾是托尔斯泰的痴心读者,一大本一大本的译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我都一字不缺耐心地读完,少女时梦想,像娜塔莎出现在贵族的宴会上,为安娜·卡列妮娜的情事震撼,每晚抱着那些巨著同枕共眠。
呼啸的风舒卷起满天阴郁的云,一忽儿即下起滂沱大雨,我撑着伞立在瓦诗河上欧悲小城凡·高的墓前。不像雪莱的墓:
这里躺着的人,他的名字是水写的。
(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is writein Water)
凡·高的名字是缤纷的色彩写成的,尽管没有人在他墓前栽种“色彩”,不种“鸢尾花”“向日葵”,没有《麦田鸦阵》一望无际的金黄……只有一位不知名的女士随手将一束温室里培养的待风花———风信子,留在他墓前。
凡·高短短一生中并没有多少缤纷的故事,缤纷是他不朽的画幅。
生命的竖琴已不再弹唱,它高高悬挂在墙头,但人间陌生的知音,会一再去解生命的谜题,就像一七六二年间欧洲文坛为《奥辛诗集》所掀起的痴迷,那震撼人心的诗句是由苏格兰Gaelic语翻译成英语的散文诗,叙述着古往已逝的轶事,那诗音好似由一位善琴的女子十指纤纤,湍流击石般弹出的清韵……“奥辛”只是化名,所有灵感是作者自苏格兰古语断简残篇中的获得的,奥辛的诗篇华美绝伦。
当生命的竖琴不再弹唱,它高高悬挂在墙头,那竖琴的主人莎士比亚、托尔斯奈、雪莱、凡·高……不论躺在华贵的石棺中,或只是黄土一堆,那都是福地。
(2000年6月)
暮雪纷纷
飞 雪
飘雪的夜晚像千株万株的霞草花,在无星无月的夜晚燃亮了窗外的世界。
多年生活在欧洲,逢到大寒,时时感到纵然穿上狐裘也不暖和,锦衾更是单薄,百丈的冰雪囤积在异乡旅人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