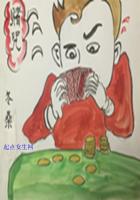戏园子在二份子的西南角,尽管这个小镇没多大,但当两人一路小跑赶到戏园子时,还是气喘吁吁、满头是汗。今天的戏是免费的,以前只有买了票才能通过的那道低矮的木门,此刻却慷慨地敞开着,无人把守,随便出入,两个姑娘心里好不痛快。
戏园子是露天的,一人多高的土墙,围成一个可容纳一千多人的圆圈,地面没有处理过,仍然是土地,也没有任何可坐的设施,只是一片空地,观众都是自带凳子。最北端是戏台,朝南,有顶棚,戏台后面是简单的化妆间。一年也唱不了几回戏,平时戏园子是闲置的,门不锁,孩子们有时候会进来玩,台上台下来回跑,也经常会跑到戏台后面的化妆间看看,在孩子们心中,那是一个有些神秘的地方。
张栓女和刘粉花进入戏园子的时候,人已经不少了。前面的观众,都坐着小凳子,有些小孩干脆靠着戏台站立着,胳膊支在戏台上,两只手掌将下巴托着,眼巴巴瞅着剧务人员忙前忙后,急切等待着大戏开演。中间地带的观众,坐着大板凳,也有高级点的,坐着椅子,再往后,是没带凳子的观众,只能站着看。
张栓女和刘粉花在人群侧面稍靠后的位置找了个空地站了下来,侧面虽然不是太好的位置,但好处是不会被太多站立的人遮挡视线。站定之后,两人喘了口气,定了定神,掏出手绢擦了擦汗,将头发理了理,等着大戏开场。在内蒙古中部地区,民间只上演两个戏种:二人台和晋剧。据说今天演的是晋剧《狸猫换太子》,这也是当地常唱的一出戏,张栓女看过不止一回了。其实每回唱戏,也基本上就是那么一些经典曲目,老百姓都看过好多回,但是没有关系,即使看过一百回,都不会减弱大家前来看戏的热情,甚至不惜步行几个小时。不少戏迷们台上演员唱,台下她们唱,一个字不落一个音不错,且字正腔圆,摇头晃脑,完全沉醉其中。
“看戏的人真不少哇。”刘粉花环顾了一下人群。
“一年到头也看不了两回戏,而且这又是不要买票的戏,还不赶紧来看,人不多才怪。”张栓女正整理着衣服,褂子上一个桃疙瘩(大襟袄的纽扣)松了,她赶忙重新扣紧。
“不过我还是喜欢看二人台。二人台总是逗得我哈哈笑,很开心。晋剧拿腔拿调的,而且太慢了,演员在上面扭好久也不唱一个字,就算唱了,一个字唱半天,你睡一觉醒来,她都唱不完一句。”
张栓女被逗乐了:“哈哈,有这么夸张吗?真该带个褥子来,你睡着看。”
“去你的,你才睡着看。”刘粉花嗔怪地白了张栓女一眼。
“哈哈哈,人家关心你,让你舒舒服服地看,你还不领情。”
“就不领情。”刘粉花显得有点心不在焉。
“粉花,咋啦?惦记你的来喜哥呢?”
被张栓女说中,刘粉花明显有些不好意思,她慌忙回了一句:“才没有呢!”
“和我还不说实话,我也不是看不出来。咱们找找看。”说着,张栓女就向人群中张望了起来。刘粉花也跟着开始搜寻。
两个姑娘的目光把整个戏园子都扫了一遍,只可惜宋来喜的身影并没有出现在她们的视线中。刘粉花显然非常失望,她自言自语道:“他也许压根儿就没来二份子赶交流,更别说来看戏了。”
“不要这么早就泄气,哪有那么巧,咱们一寻就马上能寻见。说不准他还在街上逛呢。”
“说的是呢。”
“那天我在村里碰见他,他说他会来的。”
“真的?”刘粉花眼里闪现出了光亮。
“是啊,他说他妈让他买些东西。”
刘粉花高兴了起来,又变回了她原本活泼的样子。倒是张栓女不自在了起来,她总觉得人群中似乎有一束目光总是停留在她身上,但她又不能确定,以为是错觉,可又分明感觉真是有一个人总看着她,这让她很是疑惑。
“铿锵、铿锵、铿铿锵、铿锵锵锵——”,嘈杂的人群顿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投向了戏台,张栓女感觉她身上的那束目光移走了。一定是有这么个人的,不是错觉,此刻她确定了。不管怎样,这束目光此刻没有放在她身上,她又踏实了,能够专心看戏。在晋剧特有的曲乐声中,大幕徐徐拉开,露出了早已摆设好的布景,六七个着汉服的漂亮女戏子踩着小碎步,甩着长长的水袖,从后台翩然飘出,就象仙女下凡一般。对这一幕,张栓女是熟悉的,这是《狸猫换太子》第一幕《审寇珠》的开场。
张栓女看过这出戏好多回,以前都是母亲带她出来看的,她的母亲是晋剧迷,不仅喜欢看,也喜欢唱,并且记性也好。村里每年正月十五闹元宵,非常隆重,也异常热闹,是孩子们的节日,也是大人们展示才艺的舞台。过完年,基本上是从初六开始,村里人就开始为元宵节的晚上做准备了。民间艺术家可真是多啊,大家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正月十五那天,晚饭后,在一块开阔的空地上,通常是在村里秋天收拾麦子的场院里,摆上大鼓。天全黑之后,“罄罄嚓!罄罄嚓!罄罄罄罄罄罄嚓!咚咚咚!咚咚咚!咚不隆咚咚咚咚!”锣鼓铙这三种汉族民间乐器,被稍有点音乐细胞的村民有节奏地敲响。用木柴或煤炭堆起来的旺火也被点燃,孩子们早早围住熊熊燃烧的旺火,发出阵阵欢呼。大鼓的“咚咚”声仿佛敲到了人的心里,人们的心房也和鼓声产生了共鸣。大人们也匆匆赶完家务,陆续走了出来,人越聚越多。突然,鼓声更大了,锣声更响了,铙声更亮了,大家都激动了起来,知道好戏即将上演!首先出场的,通常是秧歌队,由二三十名村里的妇女组成,头戴红花,脸擦胭脂,身上穿着颜色鲜艳的演出服,手里拿着扇子,脚下似有一个无形的“十”字,每个人都踩着这个“十”字两条线段的四个顶点,和着锣鼓的节奏,扭动着往前走。然后是高跷队,踩在一米多高的高跷上的小伙子们,同样是用心装扮了一番,个个精气神十足,他们昂着头,甩着胳膊,扭动着身体,往前走两步,再退后一步,和着鼓点,真是神气极了,羡慕煞了仰头目不转睛盯着看的孩子们。随后是跑船灯,用竹条编成船的框架,再用彩纸糊出形状,真是高手在民间,这船灯的大小和真实的小木船差不多,并且非常美观,船头点着几根蜡烛,用玻璃罩子罩住,船中间是空的,没有船底,又很轻,人可以装扮成任何角色,然后站进去,拎着船帮就把船拎起来了,同样合着节奏跟着队伍扭动表演。乡亲们别出心裁,和跑船灯类似的,可以做出好多花样,如猪八戒背媳妇、吕洞宾倒骑毛驴等等。表演完毕,就是唱歌了,村里的歌者,这个时候是展示才艺的绝佳时机,张栓女的母亲——臧丑女,这个时候是明星——张二牛败光家业以后,她没了这份心情——
“想亲亲想得我手腕腕软,
拿起个筷子我端不起个碗;
想亲亲想得我心花花儿乱,
煮饺子下了一锅山药蛋......”
臧丑女长相靓丽,嗓音嘹亮圆润,一曲民歌《想亲亲》,唱得婉转动人,博得阵阵喝彩。《想亲亲》是一曲山西民歌,内蒙古中部的风俗,融合了部分山西的民俗,在内蒙古,有大量祖籍山西的汉人,这是由“走西口”这一人口大迁徙造成的。
当然,武川县也有自己独特的民歌——爬山调:
“听见哥哥的说话声,圪蹭蹭打断个头号针。
看见哥哥朝南来,热胸脯爬在个冷窗台。
只要哥哥炕上坐,觉不见天长觉不见饿。
泪蛋蛋和泥盖了座庙,想你不想你天知道。”
一曲表达少女思念情人的歌曲,情真意切,语言直白,婉转动人地从臧丑女嘴里袅袅飘出,浸润着大家的心田,那些感同身受的少女,竟然背过脸去,悄悄擦拭着眼睛。
“闷悠悠冷坐西宫院,懒看中秋月儿圆。心内焦急苦计算,李妃产期在我前。倘若她把龙子产,我作偏妃心不安。”戏台上,刘妃正盘算着一场毒计,观众不禁为李妃捏一把汗。可张栓女却一句唱词都没有听进去,她正心疼着独自守在家中的母亲。
那束目光又重新回到了张栓女身上,她有点恼火,决定找出这个人,她的目光大胆地向人群扫了一遍,但是一无所获,这在她的意料之中。是啊,一个人如果不想被发现他在关注你,他躲避你的眼神再容易不过。
“嗨!粉花!你在这儿!”一个欢快的声音。
张栓女和刘粉花一齐回头。
“来喜哥!”刘粉花惊喜地叫出了声,但她马上意识到了失态,吐了吐舌头,赶紧用手捂住了嘴。
“来喜哥,你才来,粉花寻你寻得着急死了!”张栓女瞅着刘粉花,笑着说。
宋来喜转向刘粉花,他目光温柔地看着她的眼睛,柔声说:“对不起,我没想到你会寻我。”他搓着手,略显羞涩。
张栓女看着宋来喜的样子,一颗少女的心,敏锐地察觉出他对刘粉花的感情,心里暗暗为粉花高兴:“来喜哥,粉花可惦记你呢,你可要明白啊。”
“嗯。”来喜摸着后脑勺,嘿嘿笑着答应。粉花则羞红了脸,瞅了一眼来喜,低下了头。
“你俩说会儿话,我看会儿戏。”张栓女退到一边。她又感觉到了那个目光,此时这目光,更加灼热起来,张栓女有点无所适从。她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人群,这一次,她终于抓住了这束目光!可当她顺着这目光看到那双眼睛的时候,她心里不禁一惊:一直暗中关注自己的原来是杜家三少爷!这一次,三少爷没有再躲开他的目光,他朝栓女微微点了点头,笑了笑,便起身离开椅子,走出了人群,消失在张栓女的视线中。栓女一阵慌乱,又惊又喜,胸腔里似有一只兔子在到处乱撞,三少爷的离开,她松了口气,同时又非常失落。她重新寻找那个身影,可是,却再也看不到了。她恨自己,为何一定要戳穿他,让他难为情,这下可好,吓跑了他。正在她惋惜的时候,感觉身边有人轻轻碰了碰她,她回头一看,差点惊得叫出声来,正是杜家三少爷!
刘粉花和宋来喜也着实吃了一惊,他们不知道这个儒雅的富家少爷有何贵干。
“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杜少爷朝张栓女微笑着,说:“这个是你的吗?我在街上捡到的。”说着,少爷摊开手,在他的手心里,是一个樱桃大小的粉红色绒线小球。栓女连忙低头看去,只见自己左脚上,原本两个小球,现在只剩一个了。她顿时不知所措起来,她红着脸,低声说:“是我的,什么时候......走得太快了......我以为......谢谢你。”
栓女想不起来去拿回小球,少爷的手就这么一直摊着,但他一点也不恼,温柔地看着栓女,脸上洋溢着笑意。
“你不要了吗?”少爷又问。
“不要了!不要了!送给你了!”粉花插了一嘴:“她回家再做一个就是了。”
“真的?”少爷眼睛一亮,看着张栓女。
“栓女,你说话呀。”粉花催促道。
“栓女——你叫栓女?”少爷问道。
“是的,张栓女。”栓女回答。
“张栓女——”少爷重复了一遍,又问:“哪个村的?”
“五份子。”
“哦。我是北梁的,我叫杜家祥。不打扰了,继续看戏吧。”说完,他看了栓女一眼,又向粉花和来喜点了点头,离开了。
那天,那出戏后来唱了些什么,如何唱完,栓女都不知道了,她只知道,那束目光,一直陪伴她到大戏散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