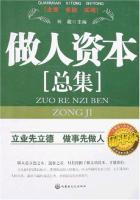关青山喝完一坛酒,平躺身体,呆呆望着房顶。张士强正要上前说话,他却突然大哭起来,呜呜道:“雁鸣,小叔不该让你和博星朗一起出去啊!”张士强吃了一惊,静静看着他。
关青山又道:“博星朗乃破军之星,天赐煞气,本性之中视六亲为仇寇,处骨肉无仁义。若是救得果拉还好,若是果拉遭了不测,只怕…只怕这天下再无人能抑住他,他的煞性也将破茧而出,你与他在一起着实危险。小叔时日不多了,还能再见到你么?”正哭着,突然四肢痉挛,缩成一团,凄厉嚎叫,在榻上打起滚来,口中尚断断续续骂道:“孔帮主呐,庄掌门呐,救我呀,太上老君,观音菩萨,如来佛祖,你们在哪儿呢?老天啊,上帝啊,我入你先人板板…”张士强看得毛骨悚然,心想还是等明天一早他清醒的时候再来为妙。当下回到翠香楼上,跟温翠香又说会儿话,温翠香叫了个姑娘来陪他吃饭睡觉。
次日一早,关青山尚未起床,张士强已到他门口等待。一会儿,两个外国人也来了,直接推门进去。关青山迷迷糊糊道:“他娘的,这么早就来了。”掀开被子,下床来穿衣服。螺蛳“啊”一声转过头去,张士强也吃了一惊。关青山赤条条立在床头,连条底裤也没穿,笑道:“没见过光屁股睡觉么?此乃人生另一境界也。哈哈哈,此法同样适用游泳、骑马、读书、吃饭等等。你们回去若敢试上一试,必得干中者大矣。但不可生搬硬套,以免弄巧成拙,须牢记运用之妙,在于变通。”
张士强瞠目结舌,威尔逊哭笑不得,只道:“原来彼国追求自由之风更甚我国。”关青山一手穿衣服,一手拿起个碗倒上酒,迫不及待先喝几口,又叹道:“奇哉怪也,我这一辈子所穿衣物,不是大就是小,竟没有过一件真正合身的。一辈子所作所为也与此类似,却不知何时才能做天性所归的事情。”
正说着话,一个士兵跑进来门来,见关青山正在穿衣服,喜道:“幸亏关先生刚起床,大王有要事请问先生。”关青山道:“放。”士兵道:“阿都派人送信来,说我们上次给他的三百匹马羸弱不堪,只与岭安盘打了四五仗就累死大半,致使他战事不利,总共死伤五百多兵马,又说现在人马紧张,请大王重新拨给五百匹马。作为回报,他愿意发一千骑兵来帮助我们打阿露。否则的话,他将收兵回山,不再打阿都了。大王犹豫不决,请先生拿个主意,到底该不该给他。”
关青山来回踱步,骂道:“这个蛮**,想的倒美。你叫叟帅回封信,先说岭安盘是头牛,最痛恨的是老挠他痒痒的蚊子,而不是狠揍他的人。要是放他出来,他一定先打死身边的蚊子;之后再说,叟帅大王已经视察了马场,马儿果然都很羸弱,正在究查养马官之罪过,等查清楚了一定给他个交待;然后说,阿露想跟我们讲和,但是叟帅大王平生最重信义,坚决不肯做对不住朋友的事情;最后请他快些派兵马过来,这边已经派人上路迎接了。”
士兵大喜,一一记录下来。关青山想想又道:“蛮**一定不会派兵来的,等过一天再给他写封信,说现在阿露退居牦牛道险要关口,不宜强攻,叟帅大王正好趁此机会休养兵马,秋后再战,骑兵不必远道而来;马儿的事情也已经查清,是由于养马官长期给马儿吃露水草造成的,大王已处罚渎职人等。”
士兵得计而去,关青山又拿起酒要喝,威尔逊止住他,道:“关先生,给你看样好东西。”关青山道:“又是什么奇*巧计的小玩意,快拿出来玩一玩。”
威尔逊拿出一个木盒打开,里面铺着块洁白的棉布,上面放着几把二三寸长的小刀、小叉、镊子及小钳等等,精巧别致,亮光闪闪。关青山“哦”一声,拿起一把小刀仔细看,朝刀刃吹口气,点头道:“果然锋利,不亚于剃头刀。是你们英格兰铸造的么?嗯,不错,只是炼得过火了,太过刚硬,少股韧性。我能铸出来更好的来。”
螺蛳笑望着他,说道:“这是我们找小满罐师傅专门为你造的。”原来这位小满罐已经成为名誉全镇的名匠。关青山又拿起一把小钳,玩弄几下,却猜不出有何用途,听得此言,奇道:“为我造的?我要它何用?”威尔逊正色道:“关先生,近来你的背部常有钻心的刺痛,对不对?不止背部,还有胸部、颈肩、面部等处,多有半身麻木、发凉、多汗之症,甚至猝倒、头部发木、眼胀、张口困难,四肢肌肉萎缩,腿脚已有瘫痪之兆,对也不对?”
关青山微微变色,道:“你所言不差,先前我一时大意,坠马摔裂旧伤,自知脊柱破裂,背心的铁钉伤及骨髓,故有此症状。我已自撰良方每日一服,当能保二三载寿命。”威尔逊面有惊异,问道:“你用的是什么药方?”
关青山凝视他片刻,哈哈笑道:“说与你听也无妨。以蜈蚣、穿山甲、马钱子、细辛、乌头、血竭、冰片、樟脑等药材熬成浓汤是也。”威尔逊长叹一口气,道:“关先生虽是国之圣手,却也只能保住短暂光阴,不知二三载之后又该如何是好?”关青山不语,拿过烟枪,躺上床开始点火,红光明灭之中,他的脸色变得沉重严峻。
威尔逊续道:“这等痛楚每日不间断发作起来,任何人也抵挡不住,故而你不停的吃烟喝酒,以麻痹身体,减少痛觉,对不对?”关青山口吐浓烟,黯然不语。
威尔逊道:“别人只当你发了疯,却无人知你正忍受何等的苦痛。可你最大的苦痛尚不在身体,而在内心。我们一直死皮赖脸来找你,你当我们真想自取其辱么?你学问大,在我们眼中充满神秘,我们不愿你就此死去。希望能够凭借万能的上帝,解释你内心的疑惑,祛除你内心的苦痛,赐予你人世间的快乐。”
关青山突然双手握紧烟枪,不住发抖,脸上的肌肉开始收缩扭曲,显是正抑止着极大的苦痛。螺蛳走过去,扶他坐起来,轻柔抚摸他的额头脸颊,道:“我们老闻你的烟味,也快上瘾了,你不要再吃了好么?来,给我吧。”说着,轻轻拿住烟管。关青山颤抖的双手慢慢松开,闭上双目,咬紧牙关,汗水涔涔而下。螺蛳把烟枪递给威尔逊,取下胸前挂着的十字条长链,轻轻挂到关青山脖子上,低声道:“上帝会保佑你的,阿门。”同时手在胸前比划几下。
威尔逊面有喜色,关注着他。螺蛳握住关青山发抖的手,道:“不要怀疑我们,让我们为你做手术吧,这是你唯一的希望,也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一起为你祈祷。”
关青山徐徐睁开双眼,目光渐变得宁静,道:“盖吾一生对上苍无所畏惧,所以命运坎坷也。直至今日,方知‘敬’、‘恕’二字之贵。就按你们的意思办吧,若是上苍垂怜,赐我关长水再生,我必应当日之诺,随你们去英格兰。”
威尔逊和螺蛳大喜,相顾而笑,扶他起身。张士强见关青山恢复神志,上前行礼,道:“关先生,有人托在下给您送来一封书信。”随即拿出关雁鸣所托之信。关青山一愣,眼中陡然精光四射,忙接过信来撕开,读罢仰天大笑,道:“雁鸣没事,雁鸣没事,哈哈哈…”笑罢,又道:“雁鸣长大了,稳重了,知道不轻易诉苦抱怨了。”又问张士强道:“雁鸣没有和博星朗在一起么?”张士强摇头道:“在下只认识关少爷,没见过这位博星朗。”关青山拉张士强坐下,琐细皆问,张士强旦有所知,一一道来。
待问的没话了,关青山已摸清关雁鸣在西安的大致情形,精神显得十分充裕,但想到博星朗不知下落,忍不住又生些担忧。片刻,再展开信,反复阅读关雁鸣的寥寥数语。读一会儿,突然“啊呀”一声,道:“总共才十余字,怎生挤的如此拘谨,笔划当中毛边参差,僵硬而强劲,料来他近日心灰意懒,不求上进,虚火冲顶以致脾性孤僻急躁。嗯,该喝点茶祛火了。”对张士强道:“劳烦小哥替我捎回去两样东西。”打开抽屉,拿出一把纸扇和一包茶叶递给他,又道:“不知如何称呼你?”张士强道:“在下**堂张士强。”关青山拱手谢了,道:“你走之前,凭手中纸扇先去天健楼,找叟帅要副金鞍,权当酬谢。”张士强辞谢出来,直奔天健楼,果真领得一副表面涂着黑漆的金鞍,欢天喜地离开安宁镇。
关雁鸣听张士强讲完,虽依旧担忧,但总算不那么惶恐了。董震的脸色却不太自然,独自喝几口闷酒。关雁鸣随即想到当日阿露本已打好金鞍准备与他交换马儿,不料马儿却被叟帅半道劫走,交易未果。想必阿露的金鞍后来又被小叔用兵夺来,此番小叔叫张士强带一副回来,也是故意要让董震重温旧梦,郁闷一下。想明白此节,关雁鸣哈哈大笑,转开他的心思,道:“师哥,这回你算是帮了小弟大忙,来,小弟敬你。”董震推辞道:“小事小事。”勉强与他对饮一口。
关雁鸣又敬张士强,敬完了放下酒坛,道:“师哥,小弟还不知胭脂姑娘为何会死心塌地去董悦师哥那儿?你当真已经抓了她哥哥的朋友么?”
董震干笑几声,瞅着关雁鸣,神色古怪,道:“不错,原本我也不知此人是他哥哥的朋友,只是猜想他们都是同乡,偏生突然都教我在西安遇上了,多半是有些不寻常的关系。没想到果真如此,潘美人一见此人,惊得花容惨淡,又看他腿脚都断了,进出全靠别人来抬,只当定是我干的,于是什么都答应我,只求我放了他。”
关雁鸣心头暗骂他卑鄙,但听得“只当定是我干的”这一句,有些奇怪,问道:“莫非不是你打断这人的腿,好来威胁她么?”董震一抬头,干笑几声,道:“是我打断的,是我打断的。不吓唬美人一下,美人怎肯轻易答应呢。”关雁鸣观他神色有异,料想此言半虚半实,隐隐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却又浑然不着头脑。一转念又想反正潘美人已去青龙堂,也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