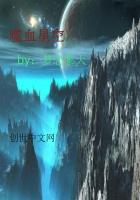我终于得到了一次出去透气的机会,L城一家阔少结婚,大摆筵席,让我去凑热闹。我来者不拒,就当给自己冲个喜了。
与我同行的司机是个新人,刚刚拿到驾驶证,我有幸成为第一个做他车的记者。
一个准新人,一个彻头彻尾的新人,我们俩的话语很投机,相谈甚欢。我变得很能说,或许是这些天被憋坏了。
众所周知我是一个‘大嘴巴’。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一处十字路口。这是一个不甚繁华的地儿,也不是交通要道,理应很通畅,结果却堵车堵得严重。
我们被堵在数十辆车后面,司机怎么按喇叭前面的车辆都没有回声。
这点有些奇怪,平常对方通常会按喇叭回声。
我摇下玻璃,探出头,顺着车与车的间隙向前看,看到距离我们几十米的地方围了满满的一片人,似乎在观光。
这不是观光的地,定是出了什么事。
出于好奇,我下车去看个究竟,司机留下看车。
这时,我听到了前面叫嚣声。前面发生的不是好事。
穿过前面的那些车,才发现车内空无一人,感情都去凑热闹了。
来到人群前,叫嚣声更显响亮。我挤过人群,直到可以看到叫嚣声发出地,才停下了脚步。
一场车祸。
有人死了,是男是女,看不清楚,已经成了一团血肉。很明显,死者是被车碾过后又倒过来碾了第二遍,目的就是让人死。
真残忍。
打架的是四个男人,三人打一人。
叫嚣声具体说是三个打人的男人发出,被打的人已经躺在地下呻吟了。
做出这种的事的人,就是被活活打死也是顺民意,或许这就是无人去过问的原因。
“这世界没王法了,自己的亲人死的这么惨,还要遭到了如此的毒打,这些高官子弟比以前的地主豪绅有什么区别?”我耳边响起了一个很轻微的话语。
“和谐社会?和个屁!”有一个轻微的声音发了出来。
这两人在交谈。
我被吸引了,瞥眼看向他们。
他们回看了一眼,摇了摇头,停止了谈话,又摇了摇头,转身走了。
我明白了。
这群天杀的,害死了人,还如此嚣张。
我快速向前挤过几个人,冲了过去。
我身后稀稀落落的传来了言语声。
“怎么了,又来了一个打手,有权有势的人就是可以随便撒野。”
“当然可以随便撒野了,因为开的是越野车啊。”
“又一个挨打的来了,死方的这个亲友来的真不是时候,早几分钟过来,两人反抗三人,还有折腾的机会,现在一个趴下了,恐怕也只有做第二个趴下的人。”
“我看不像亲友,倒像是‘徐洪刚’。”
“就是‘成龙’也照打啊。”
“我要是死方的亲人,我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冲进来,而是打电话叫警察。”
“警察来了有个屁用,现在官官相护的网比蜘蛛网还更胜一筹。”???????
这些话反映了什么呢?真让人寒心。
“住手!”我大声喊道。
三人停下了手,齐刷刷的看着我。他们不是听取了我的话,而是被我这个不速之客短暂的震住了。反应过来后,发现我只是一个小人物,一人抬脚又朝躺在地下的那人踢了一脚,以示对我的不屑。
我掏出手机,拨打了110。
他们没有阻止我,似乎真的天不怕地不怕。
不写他们的特征名字,是因为我不屑写上,我只能勉强的视他们比普通动物高了那么一点点罢了。
“你们可知如此做是可耻的?”我质问道。
“我只知道你马上就要****了。”第一动物说。
“还有王法吗?”我质问。
“老子就是王法。”第二动物说。
“你们还有人性吗?”我质问。
“人性就是狗屁。”第三动物说。
“我是L城快报的记者。”我亮名了身份,咱不是用此吓他们,我知道这吓不倒他们,我只是想用记者的身份跟他们说话。
“记者也是屁。”第二动物因为我是屁而高兴的乐了。
“他们需要施救,不管已经死了的还是活着的。”我说。
“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走到他们身边了。”第一动物说。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变成了一个侠客。
“您甭客气,因为您只有挨打的份。”第三动物说。
一瞬间,拳来脚往战在一处。
这三个动物,平日里有的活动,身手还有的说。要不是我乃打架高手,招架不住是注定的了。
这次警察来的速度挺快。眼前情景让他们很吃惊,露出了人性应有的道德。制止了群殴,铐住了三人。开始时三人动作言语上有些反抗,后来动作越来越大,言语越来越横。警察们也来了拗劲,硬是铐住了三人,将三人像个肉丸子一样的丢进了警车内。
我一切配合,被铐住‘请’了另一辆警车内。隔着警车的玻璃,我看到司机一脸迷茫的看着警车,他为什么迷茫呢?我揣测不到。
进了警局我被关进了一间狭小的屋子里。
我心情昂奋的等待着警察对我的审问,左等右等,始终不见人的影子。我看不到外面的天空,估量不出具体的时间,但在一段很漫长的时间里都没有看到警察的影子。
我明白逝去时间的久远,对我对于这件事越不利。
我身心疲惫的睡着了,睡梦中迷迷糊糊的听到了从远处走向这里的脚步声。我灵敏的睁开眼睛,坐了起来。
传来了开铁门咣当哗啦的声音。
一片光洒进来,接着一双黑色皮鞋展现在了我的视线里。
囚室里突然明亮了,我本能的捂住了眼睛。在黑暗中突然看到阳光真不是一件多么好的事。
这里原来有个白炽灯,只是开关在外面。
我慢慢的移开手,眼睛适应了亮度,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主编在朝我笑,皮笑肉不笑。
我知道我没有见到警察,却见到了他,事情可能已经不再正义与光明。
“几点了?”我问。我纠正了自己的坐姿,让自己坐的高昂一些。
“上午十点。”他说。
“已经是第二天了。”我说。
“是的。”他说。
“我为没有完成您交代的任务而向您道歉。”我想起了那场令我得到解锢的婚礼。
“这没什么,小事一件。”他说。
“我现在身在此处,算是大事了吧!”我说。
“天下的事都是这样,大事小事,就凭一张嘴说的算。”他说。
“您的意思?”我说。
“肇事者已经妥协了,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他说。
“怎样的责任?”我说。
“该负的都负了。”他说。
“赔偿?坐牢?”我反问。
“大错已经酿成,我们应该有颗宽容的心。”他说。
“我们对死者的同情心呢?”我反问。
“死者安息。”他说。
“您的意思,这件事由始至终都没有我这么个人。”我说。
“聪明人就是聪明人,肇事者是个军校的大学生,如果此事曝光了,会影响到他的一生。”他说。
“死者的家属会因为失去了亲人而痛苦一生。”我说。
“他们的后台很硬,得罪了他们,谁都不好过。”他的表情不像是在吓我。
“莫非他爸是市长。”我说。
“副市长。”他将这三个字咬的很硬吐了出来。
我失去了言语的功能,我没有多少话要说了,也不想说了。
总编临走时,轻轻拍拍我的肩膀,示意我掂量掂量。
我闭上了眼睛,没有看他。
我蔑视他,甚至蔑视所有有势力的人,他们还不如黑社会的王二???????
半个月后,我出来了。
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我已经不是那个我了。
那个案子已经结案,移花接木出现了而另一个肇事者,然后是金钱的交易,再者是肇事者蹲两年的牢子。
死者家人不在上诉,厚厚的一沓钞票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安慰。老实的农民知道上诉的结果,他们怕,怕权高势重,深知民不跟官斗。
我去找过他们,开始他们避而不见,后来见到了一个老者,他代表整个家族,恳求我别再跟他们添麻烦了,他们已经很悲伤了,让时间平静的抹去悲伤,别再搅和了。
我没有再去报社上班,报社的人也没有在打扰我。
我不再属于他们,他们也不再属于我。
我只属于我的那个小社会。
清闲的几天中,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我一生不配做有约束的活儿,因为我不是一个定性的人。
这些日子里,我与朋友的距离被拉开了,这倒是件严重的事,于是乎,我报以修复关系的心情邀众友相聚。电话通知了十来个,却呼啦来了三十多个,我们喝了一夜的酒,吹了一夜的牛。
这种生活才是属于我的生活。
唯独少了于霁。我没有问,朋友们也没有谈及她。
我想接下来,我要做些我个人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