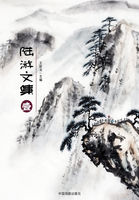昏暗暗的路灯,被齐头的枫树掩了,天上没了月光儿,透着的全是乌云,一条黑糊糊的水泥路,像谜一样深不可测,七穿八拐地往着漆夜深处溜去。
枫树的边侧,是一道残破的围墙,早已寿终正寝,像一具慢慢腐烂的尸体,它在一点点消失,白惨惨地骨架还残留着些,布满着荒草,看不清它面目。
世界静得恐怖,连心跳声都缺乏善意的刺激着双耳。
看来,这个夜,不会像往日那般平常,一定会发生点什么。
我叫于洋,是南海报社的一名记者。
报社这季度的业务还算不错,但随之工作量也增加了不少,经常没日没夜的加班早成了家常便饭。
就如今天,又奋斗到了凌晨,我晃了晃有些晕沉沉的脑袋,沿着狭促的水泥小道往黑夜深处走去,行了有几百米,前处一家排档铺子还打着灯,肚子这时也不争气地咕噜了起来,便快步往那奔去。
进门扫了几眼,铺子并不大,品种也就那几样,不过眼下要想找些别的什么夜点来吃,怕是也没那般轻巧。心想,将就着吃吧,要了份热干面,老板娘便忙活去了。
我捶了捶有些酸胀的脖子,找了个临近风扇的位置坐下,掏出手机查看起了时下的热点新闻,网上最近蔓延的一款名为‘逃出潘多拉’的手游被传得神乎其神,占据了各大搜索热榜。
我大致浏览了几下,网友对此贬褒不一,有人说它残辣血腥,荼毒社会。也有人大唱反调,说它神秘诡测,值得深究。
云云众说,各有道理。
手机突地滴了一声,我划开一看,是李思发来的。说,有一款相当刺激的手游分享给我,另外还把我拽进了一个陌生群,我一看,是一个叫‘元婴会‘的游戏群,群里信息铺天盖地,口水无非就是游戏话题,滔滔滚滚。
叮叮,一个验证声音响起,我倒有些意外,一看,是一个叫元婴君的陌生人,发来一条信息:你终将望见自己,而我将在天堂注视你。
我冷不丁被这条信息膈应得紧,暗骂了句,神经病。
不过,我隐约觉着这神经病似乎和这个叫‘元婴会’的游戏群有莫许瓜葛,于是我仔细翻阅了几下成员录,不料,这货竟是群主。我一阵无语,都些什么七八乱糟的。
老板,来碗云吞。
一个低沉的声音打来,冷邦邦的,整个铺子突地寒气袭人。
我抬眼望去,是个干瘦的男生,20几岁,背着一个黑青色单肩包,纯白T恤搭着一条浅蓝牛仔裤,看着倒挺干净,不过面色却惨寡得如白纸,毫无血色,宛似被抽干了一样。
他抖了抖肩上的背包,找了个离我不远的角落坐下。
我好奇地瞥了他一眼,他脸色真惨白得恐怖,叫人看着心慌,正专心致志地玩弄着手里的手机。
我顺着他如藤条般的手指往手机屏幕望去,悠扬温馨的音乐下,一男一女在唯美梦幻般的小岛上欢度他们的蜜月时光,甜蜜与浪漫伴随了他们一个又一个日出与日落。
怪异的是,画面中的男主人公却长得跟这位白纸男生神似貌同。
接着,画面一转,一个突如其来的老翁掳走了女孩,并讲道,要想救回女友,就必须前往传送点,依次完成游戏并通关。
不一会,老板娘满脸堆笑地上来,招呼着趁热吃,我早饿得不堪,抓起筷子就狼吞虎咽了起来。
白纸男生却冷静得出奇,他怪怪地盯着手机,惨寡的面色依旧可怖瘆人,绿褐色瞳孔却泛起离奇的炯然诡异。
我身上不禁爬满疙瘩,竟连食欲也乏了,此时的他,倒是动起了勺子,他右手点着屏幕,左手生硬机械地舀起云吞送至鼻前嗅了嗅,却并不去吃,诡异的目光不曾挪离手机一秒。
我忍没住又偷瞄了他一眼,频幕这时转出另一画面,惊悚动魄的音调下,男生手握一把利刃,他快步冲上,面不改色,对着路边的一名孕妇就是扎去,鲜血染了一地。孕妇惨哼一声,挣扎不起,边处的两名男子吓得尖声呼嚎。叫声惊动了不远处的执勤民警,民警掏出配枪朝天鸣了一枪...最终将凶徒制服。
画面显示,GAME-OVER。
白纸男生顿时脸黑如铁,他哼了声,从兜里掏出钱来往桌上一扔,起身便往门口挪去。
我一阵愕然,如今的手游怎么设计得这般血腥残暴?冷不丁却无意间瞥到了桌上的钱,哪里是人民币,明端端一张冥纸,上刻天地银行。
我顿时惊得一跳,疾忙抬眼再看他,他依旧只顾低着头,甚至连思维和体重都不曾落在脚下分厘,如风一样飘逸。
老板,钱我放桌上了。
出于职业原因,我抓起文件包就追了上去,等我追到门口,他已穿过了枫林小道上了马路,一阵清风打来,将他浸在了风里,似乎顷刻就要随风而去。
转角处,一束幽黄的灯光折打过来,七穿八拐的溜弯,甚至分不清灯光具体是从哪个方位传来。
忽地,风越来越大,吹得枝叶嘎嘎响作,砸在人心头咚咚的,慌得紧。
昏晦的路灯愈发若隐若现,视野也跟着时出时没,冷不丁一辆大挂车从黑色里直扑出来,带着洪兽般的凶厉。
当心,车子!
我尖嚎了声,但车速远快于我的音速。
只听一道急促的刹车声划破气流,车轮摩擦地面发出阵阵剐皮般的剧烈惨啸,似能刺穿人的耳膜。
我惊得周身一颤,暗呼,完了,也晚了,那白纸男生肯定死了。
司机探出来个肥臃的脑袋,他四下细探了几眼,又望了望几个车轮子,这才掷出了手里的烟头,叫骂道,娘希匹的,老子还以为撞鬼了!脚下油门一踩,一溜烟的蹿远了。
车子开走了,眼前却空荡荡一片,甚至连血迹都见不得一丝。我不禁心头咯噔一下,只觉后背阴风阵阵,难不成真撞鬼了?
朋友,你忘了手机。
一只冰透透的手蓦地搭在了我肩上,我疾转过身子,吓得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眼前的面孔,正是那张被抽干了的面孔,寡如白纸。